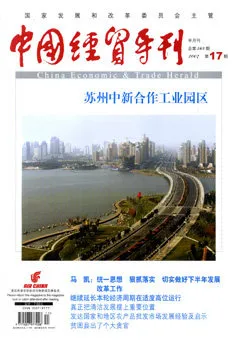继续延长本轮经济周期在适度高位运行
一、本轮经济周期的新特点
从2000年开始的我国本轮经济周期,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新特点:在我国以往历次经济周期中,上升阶段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而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到现在(2007年上半年)一直持续了7年半。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新的波动形态,或者说出现了良性大变形,即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2006年,GDP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个周期。在前9个周期中,上升阶段一般只有一二年。这9个周期是:(1)1953—1957年,上升阶段2年,最高经济增长率是1956年的15.0%;(2)1958—1962年,上升阶段1年,最高经济增长率是1958年的21.3%;(3)1963—1968年,上升阶段2年,最高经济增长率是1964年的18.3%;(4)1969—1972年,上升阶段2年,最高经济增长率是1970年的19.4%;(5)1973—1976年,上升阶段2年,最高经济增长率是1975年的8.7%;(6)1977—1981年,上升阶段2年,最高经济增长率是1978年的11.7%;(7)1982—1986年,上升阶段3年,最高经济增长率是1984年的15.2%;(8)1987—1990年,上升阶段1年,最高经济增长率是1987年的11.6%;(9)1991—1999年,上升阶段2年,最高经济增长率是1992年的14.2%。本轮经济周期,即第10轮周期从2000年开始到2006年,7年中GDP增长率分别为:8.4%、8.3%、9.1%、10%、10.1%、10.4%和11.1%。2007年上半年为11.5%。
如果我们把经济周期波动由上升通道转向下降通道拐点的来临比喻为“狼”来了,那么,近3年来,不论国际还是国内不断有人预测:中国经济的拐点来了。但实际表明“狼”没有来。
二、原因分析
为什么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一直在延续,而下降拐点一直没有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出现良性大变形,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供求分析框架出发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供给面分析:体制因素
首先,国民经济供给面的活力和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新变化。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是需求主导型经济周期。经济上升的驱动力常常是需求膨胀(包括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而供给严重制约。每当经济过热时,主要的瓶颈制约是煤、电、油、运、材(重要原材料,如钢铁、水泥等)的供给短缺。在供给面的严重短缺下,不得不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大幅度的向下调整。而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供给主导型经济周期。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的供给面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严重短缺状况基本改变,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新变化,原有的“煤、电、油、运、材”的瓶颈制约已不同程度地逐步缓解,有的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相对过剩。这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支撑经济在适度高位的持续运行。
其次,就业结构的新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就业结构,包括就业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2006年与1978年相比:一是城镇就业比重由23.7%上升到37.1%,上升了13.4个百分点;乡村就业比重由76.3%下降到62.9%,下降了13.4个百分点。二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42.6%,下降了27.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7.3%上升到25.2%,上升了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2.2%上升到32.2%,上升了20个百分点。三是在城镇中,国有单位就业比重由78.3%下降到22.7%,下降了55.6个百分点;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由21.7%上升到77.3%,上升了55.6个百分点。以上就业结构的变化,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以不变价计算的每个城乡就业人员的GDP产出率,1978年为903元,2006年上升到6304元,提高了6倍。这一方面使经济的供给面大大改善和提高;另一方面农民工以及城镇中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等劳动力成本很低,使城镇中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其购买力较低。这样,一般商品供大于求,使物价保持着低稳水平。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本轮经济周期中的“高增长、低通胀”现象。
(二)需求面分析:发展因素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加速阶段,从整体上说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我国人均GDP水平突破8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2006年我国人均GDP水平达2001美元。这推动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建设以及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城镇中,除高收入者外,一部分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也在不断积蓄,其购买力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我国本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重要推动力。
(三)政策面分析:宏观调控因素
过去,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经常是“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从1953—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共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有3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峰位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经历了5个周期。其中,在已有的4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峰位都在11—15%:1978年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为11.6%,1992年为14.2%。以往的宏观调控都是在“大起”之后,即经济全面过热之后再来进行调控。
在本轮经济周期中,汲取了历史上多次“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宏观调控表现出新特点。一是及时调控。在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及时地进行宏观调控,防止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由局部性问题转为全局性问题。二是不断调控。在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不断和多次性地进行微调,控制经济波动的峰位,使经济波动不“冒顶”,即不突破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从我国目前国情看,大体为11%左右)。这有利于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延长。
三、政策建议
(一)宏观调控: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
2006年,我国GDP增长率修订为11.1%。2007年上半年,又略有上升,为11.5%。根据历史经验,经济增长已处于或稍微越过了我国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边缘。因此,要紧密跟踪经济形势的变化,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其主要倾向是防止经济运行由偏快转为过热。这里要强调的是: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以延长经济周期继续在适度高位的平稳运行。
本轮经济周期由上升通道转向下降通道的拐点一直还没有来。按照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拐点或者说调整,总会来的。但拐点有两种:一是大拐点,二是小拐点。大拐点是指经济周期由上升通道向下降通道剧烈和大幅度的转折。这种转折往往要付出较大的调整代价。小拐点则是指经济周期由上升通道向下降通道平缓和小幅度的转折。有人建议把经济增长的大拐点叫做“狼点”,以区分于小拐点。不断地进行宏观调控,就是要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以防范“狼点”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周期平滑化的趋势。美国学者称其为经济波动的“大缓和”。我国经济周期也出现了平滑化的良性大变形。其中的原因各国有所不同,但都与其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宏观调控的改善有关。所谓经济周期的平滑化趋势,是指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缩小的波动轨迹转变。这样,在以10年左右为期的“中程”周期来考察时,其中可能包含两三个小的“短程”周期,也就是说,其中可能包含两三个小的上拐点(峰顶)。这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在适度高位的平稳运行。
为延长经济周期的适度高位运行,在一轮周期中针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多次进行微调,并不意味着前一次微调没有起作用,不意味着这次微调之后不再需要进行新的微调。当然,不断和多次性地进行微调,也并不意味着过于频繁的调控,而要给每次调控以一定的消化、吸收过程。
在化大调整为不断的小调整过程中,还需要强调的是密切关注宏观总体稳定下的局部波动问题,例如,总体稳定下不同产业的波动问题,总体稳定下的价格(如物价、房价)以及股市波动问题等。这里要“防止”两种倾向:一要防止经济运行由偏快转为过热;二要防止局部问题的冲击,防止有些局部问题转化为全局问题。
(二)把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以“长”抓不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依然任重而道远。节能减排以及把住土地闸门等,本属于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我们常说把住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信贷闸门属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而土地闸门属政府的微观规制问题,而很多人就将其视为“宏观”问题而归入宏观调控职能中。这样一来,不利于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的贯彻执行。因为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和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冷热”变化,其方向和力度可时松时紧。但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属微观规制方面的长期任务,不能时松时紧,必须“长”抓不懈。现在,一些地方由于抓紧了节能减排和土地利用等审批工作,因此有人问什么时候宏观调控可以转松。其意为何时节能减排的审批门槛和土地闸门可以放松。所以,要把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以利于“长”抓不懈,下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解决总储蓄大于总投资的困境
目前,我国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外贸顺差持续增大。要解决这个外部不平衡问题,就需要扩大内需。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那么,要扩大哪部分内需呢?这又涉及到国内的内部不平衡问题,即当前内需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要继续扩大国内投资需求,那固定资产投资不是更要反弹和过热,投资率不是更要升高吗!要继续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那现在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一角度所表现出来的消费需求已不低,近3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均在12%以上,2007年上半年又达15.4%。要说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主要是什么不足呢?一是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消费不足;二是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消费不足;三是居民住房消费不足。现在,我国许多商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但居民住房供给仍处于短缺状况,房价上涨的压力很大。
要解决总储蓄大于总投资的问题,除了要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扩大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消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解决我国目前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当中的居民住房问题。
我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要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而居民购买住房,对居民生活使用来说,是消费;但对国际上统一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来说,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却算作投资(固定资本形成);与此同时,居民购买住房后的年度折旧,以虚拟房租的计算列入消费。在我国,住房年度折旧率很低,一般以住房50年为期,年度折旧率仅为2%,这就大大压低了消费率。加之,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基数较小,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所占比重很小,2006年仅为3.1%。而在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经常占到14%左右。因此,在我国,扩大居民住房需求,增加居民住房支出,是提高我国消费率的一个长期的、重要的途径。而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大量地盖房子,增加投资。所以,在目前我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里,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仍然会存在,但在居民住房扩大以及在统计上合理提高住房年度折旧率之后,我国消费率会提高起来。从这个角度说,为了提高消费率,眼前还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以扩大住房供给。
然而,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其供给的扩大需要珍贵的土地,需要各种原材料的大量投入,这要有一个过程。要加强规划,优化商品房供给结构,加大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房和廉租房的供给,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这既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也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发展的长远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经济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