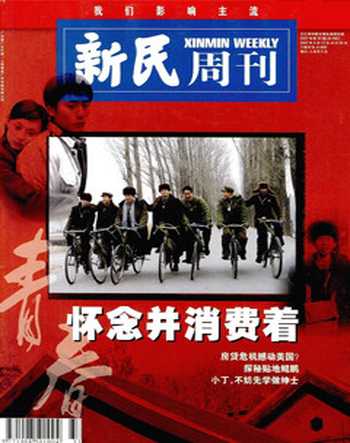伯格曼死在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董 铭

当一个传奇早已被镌刻在石碑上时,瞻仰的人群却悄然散去;直到某一天,被铭刻者真的离开了这个时代,曾经的赞叹者才又重聚在碑下,在落幕时竭力地回忆——我们并不属于他的时代。
欧洲时间7月30日,在瑞典的法罗小岛和意大利的罗马,一个电影时代就此画上了句号,很遗憾,并没有留下一个简单的入口,把我们也画进去。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拍摄时,虽然已经70年代,似乎与这里的记忆有所接触,可那并不是交汇,只是呼啸而过的火车外,庸碌的人们对车厢内的匆匆一瞥。窗外的人仅仅窥视了里面的一瞬,而车厢里的伯格曼却看到了外界的全部。
终于,他们的时代到站了,舞台静止了,上面写满了日记般、贯穿生死始终的个人信念。从《危机》到《萨拉邦德》,上帝,死神,儿子,母亲,游戏,梦境.……轮番上演着。纷繁之中,就连操纵者都自我驳斥,自我否定,他说,电影“让我有一种欺骗他人的犯罪感,用来拍电影的机器的工作原理正是基于人类的生理弱点,我用它使观众从一种感情变化到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感情:我让他们大笑,因恐惧而叫喊,微笑,相信传奇,愤怒,生气,兴奋,堕落或无聊得打呵欠……因此,我要么是一个骗子,要么是一个魔术师”。以至于他在生命的弥留时光,放弃了电影,放弃了戏剧,最后几年都沉靜在音乐里。车窗外的一切都是幻境,“金棕榈的棕榈”?对伯格曼的法罗岛来说,只不过是片普通的树叶。
备受恩泽的人们依然对着伯格曼膜拜有加。伍迪•艾伦捧着《野草莓》爱不释手,让-吕克•戈达尔毫不吝啬地把《夏日插曲》列为心中“最美最浪漫的影片”,布莱恩•德帕尔玛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影片里向《第七封印》致敬……等等这些,只不过是伯格曼留给我们五十余部杰作中的部分光芒。
他真的在接近死神,走的却是童年的小路。
假如观众们大着胆子,把幕后的伯格曼拉回台前,摆在舞台上,不再用那三位一体的位格去瞻仰他时,就会发现这位伟大的神秘主宰变得同他的作品一样,复杂、矛盾,既直接,又躲闪不定。伯格曼的个人生活,就像是他信念的镜子:那是在同一个镜头中平展着的空间。每当他(或者影片中的主人公)逃离了死亡的阴影,摆脱了早年叛逆的基本主题,伯格曼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推倒心中的围墙,沉醉在惬意的呼吸之中”。这种矛盾的转化不只一次地出现在伯格曼的中早期作品中,也预示着他在后期寻求的解脱:面具旁就是他真实的脸孔,用揭露来掩饰,用幻觉来堆砌真实,“我从未理解过艺术,我只是亲身体验它。”
隐居法罗岛的二十年来,伯格曼更像是在斟酌、修改这份体验的答案,作为遗嘱,传及子孙。
《萨拉邦德》里丽芙•于尔曼的出演,在情节上是三十多年前的感情余波,而在人物关系上,却又像是《野草莓》中的阿格达小姐和萨拉,相处多年,从爱情的漩涡中平静分离,终又重聚在一起。于尔曼与伯格曼都在努力地完成这份遗嘱,用家庭、爱情以及孤独作为原料,沉重地勾勒出伯格曼本人的情感结论。哪怕这个结论充满了反驳和自我否定(男女关系与性别对抗),都丝毫不能降低这个“镜子”举动的伟大——伯格曼用上帝的手展示了凡人的脸。
曾几何时,《呼喊与细语》如同一把锋利纤细的笔刀,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些许隐秘的伤口,丝丝阵痛,难以忘去。而《芬尼与亚历山大》中小亚历山大的“魔灯”却又是一座高耸的灯塔,用光影指引我们回到“童年时的深渊”:电影的魔力似乎无穷无尽,刹那间,深夜中的两座灯塔同时熄灭,看不到入口,何处去寻找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