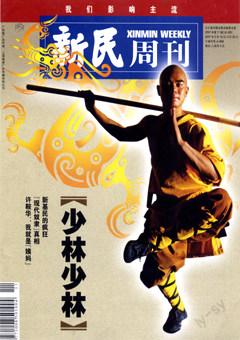许鞍华:我就是“姨妈”
王 倩
许鞍华说自己其实很“姨妈”,她想让大家了解这种怕被时代淘汰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真实。
身为“香港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许鞍华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晋身香港顶级导演行列,但3年前备受争议的电影《玉观音》让外界质疑,或许她已经才思枯竭。《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出现得正是时候,它可能会将许鞍华送上新的事业高峰。
细节决定成败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许鞍华继《玉观音》后第二次和内地电影人的合作。3年前的那部《玉观音》,内地票房不足千万,香港票房更是惨淡,影评人更是一片“差”声,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许鞍华的作品。
《玉观音》的失败对许鞍华来说绝对是痛苦的,她形容自己当时没有想清楚就接手了一个命题作文,失败在所难免。“在《玉观音》里,我想寄托一种激烈的感情。但是实验失败了,票房和评价都不好。”

许鞍华的作品大多故事性不强,但每个细节都能让人回味无穷。比如《女人四十》中在厨房铁窗前炒菜的萧芳芳,犹如被关在牢笼中的囚徒,许鞍华借此来描述一个中年女人琐碎而繁复的生活。海岩的《玉观音》偏偏就是一部唠唠叨叨的言情悲剧,许鞍华无法准确地找到细节,或者说细节太多而冗余,于是《玉观音》既没有故事,也不能给人回味。
但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我们熟悉的那个许鞍华回来了。一个义无反顾抛夫弃女的回城知青(斯琴高娃)在年华老去而又孤独无靠时,死心地回到了她曾经极其痛恨的生活中。电影照旧以细节入手,她和邻居,她和侄儿,她和乱扔垃圾的店家,她和可怜可气的“碰瓷”母亲,她和被自己抛弃的女儿,她和骗财骗色的潘知常……电影的前半段让你快乐得前仰后合,电影的后半段让你压抑得无限唏嘘,从轻快的喜剧到浓郁的悲剧,急转直下。
依旧女性中心
姨妈,一个渴望浪漫而又过了芳华的老女人,一个说着标准英式英语的退休知识分子,自恃甚高,她怕赶不上时代,于是总想做些赶时髦的事情。
这是许鞍华对姨妈的解读,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解读。《玉观音》之后,许鞍华曾经出现在纪录片《女人那话儿》中。她就叼着一根烟坐在吧椅上诉说着,为了月经到来而烦恼过,也为了自己至今没有爱而烦恼过。
“姨妈和我自己的状态特别接近,我懂这种心态,想拍出来让大家知道自己的痛苦。”在记者会上,许鞍华的腼腆和真挚一如纪录片中的那个影像。红色的针织小外套,蓝色的眼镜框,手上戴着玉手镯,左耳吊着耳坠,不停地嚼着口香糖,以此来抵抗众所周知的大烟瘾。
姨妈和许鞍华的心态并不只出现在五六十岁的人身上,也不只出现在女人身上。怕跟不上时代的人太多太多,所以现代人总是行色匆匆。许鞍华义一次给了无数人共鸣,一如当年的《女人四十》和《男人四十》,这就是流水的生活。
不变的是许鞍华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先不说以女性为中心的《客途秋恨》和《女人四十》,《半生缘》里黎明在吴倩莲和梅艳芳面前的“透明”,《男人四十》里被林嘉欣和梅艳芳抢尽了风头的张学友……许鞍华电影中的爱情大多是苦涩的,而不是完美的,男性角色的始乱终弃、懦弱和背叛倒是多次出现。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潘知常(周润发)依然如此,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姨妈内心的火焰从熊熊燃烧到奄奄一息乃至熄灭。许鞍华镜头里的男性角色释放的光芒总是不如演对手戏的女性角色那么耀眼,幸好许鞍华毫不吝啬地在电影中为我们“重温”了当年的发哥——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场景,当年是英雄,如今却是骗子。
并非上海故事
姨妈生活在现代的上海,普通里弄里的上海,而不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也不是关锦鹏镜头里的上海。说的是上海的故事,但我们熟悉的上海只出现在心已死去的姨妈离开上海的最后一瞬间——南浦大桥上,万千车灯慢慢模糊中。甚至有人说,这是一个香港导演、一个河南编剧和一个北京女演员眼中的上海,一点儿也不上海。
这是上海的故事吗?多年前的许鞍华也曾经特别想拍出当年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事实上这部电影开拍之初,就曾和许鞍华之前的《上海假期》和《半生缘》一起被认为是导演的“上海三部曲”。但如今的许鞍华已经没有了所谓的“上海情结”,在拍摄《半生缘》时,许鞍华拜访了很多上海老人,发现原来每个人眼中的上海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徒劳无功的。现在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是不是上海不太重要。姨妈只是恰好生活在这个城市,我们不是写上海这个城市的人。”编剧李樯的这番话得到了许鞍华的赞同。许说,她在拍摄时将这个城市当成了香港,“反正就是一个大城市。我没有刻意强调上海特色,没有猎奇,所以很舒服。”
姨妈的生活前喜后悲,甚至连上海和鞍山这两座城市的视觉和色调反差也是如此巨大。告别了上海的姨妈沉默着接受了一切,她嚼着冰冷的馒头,身后的收音机里传出的却是那句熟悉的京剧……
在编剧李樯的思路里,前悲后喜的情节其实很简单,乐极生悲。“常规的卖座片要么哭到极至,要么笑到极至。笑一半,哭一半,会不会更好呢?”这有点冒险,但遇到了许鞍华,李樯说自己没有担心过。“电影不能永远按照观众的惰性来进展,章回体小说就是这样完蛋的。电影在培养观众,也在挑战观众。”许鞍华的这番话值得玩味。自1979年第一部电影《疯劫》起,许鞍华就是那种既有商业能力,又不忘艺术追求的导演。
“只要拍出真诚的感觉,什么冒险都是值得的。”许鞍华讨厌重复和公式化,她一直在尝试改变,所以这么多年来她还是留在电影圈里,拍各种类型的电影,虽然有过离开,也有过失败。她对这部电影的票房的期望只是“不要亏本”,虽然很担心票房,但她依然在尝试。
许鞍华和编剧李樯最终给了姨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一如影片中分别出现在上海和鞍山的月亮。李樯将影片的最后看成是姨妈的解脱,而许鞍华的感受更加飘忽——现代社会人们一直来来往往,只有月亮一直存在,姨妈从中得到了安慰。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在香港放映时,有影评人如此理解月亮这个细节:这是只有在东北才会出现的月亮。上海,恍惚的姨妈躺在病床上,她想家了。鞍山,再次见到了月亮,她回家了。
这样的解释也很好。许鞍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