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踌躇
洪世宏
大国的痛苦往往在于难以恰当地把握自己与身外的边界。门罗主义在历史上被看作年轻的美国第一次向世界宣称自己势力范围的力举,而在当时不过是门罗总统斟酌权衡应付具体危机的小心之策。所谓门罗“主义”或“宣言”都是后人的附会,当时只是总统致国会的谘文。大国的内外边界意识并不限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疆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面上不乏疆域气魄,但是昭然于后人的,恰是背离海洋文明的一种观念狭隘。
界定自己与身外的世界,事关一个组织的安全感。产科护士会告诉妈妈,新生儿需要裹紧了睡,因为孩子在边界分明的被包中会觉得就像在母体“内”那样安全。其实她是安全的,但大人操心的是她的安全感。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所以这里谈点心理常识并不牵强。2006年,共和党控制下的美国国会和布什总统为了挽救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不利选情,通过一项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出资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上修建700英里高科技的隔离墙,以防止非法移民越境。有识之士指出,这项法案其实根本就没有安排足够的配套资金;而且即便有资金建成全部隔离墙,也不能根治非法墨西哥移民的问题。但是,布什的虚晃一枪和表面文章打点的就是广大选民的安全感。
对于西欧与北美,移民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自己与他人的界限问题。面对大量的外国移民,传统居民感觉到自己不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甚至语言等等,因而感到存在意义上的害怕与无助。于是,有些传统居民诉诸极端的反移民政见或措施。这些极端立场被称作“排外主义”。排外主义听上去是政治概念,而其英文原文 “Xenophobia”和幽闭症、恐高症等心理疾病的名称一样都有phobia(恐惧症)这个词根。排外主义无非是内心对外人之过度害怕在政治文化层面的表达。
中国没有外族移民问题,但中国也有安全与安全感问题,也有界定自身与身外的问题。2006年,这个问题再次以外资政策争议的形式浮出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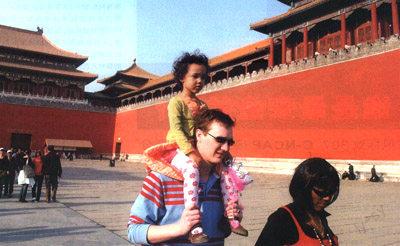
似是而非
本刊2004年10月(下)曾发表葛顺奇的文章,全面系统地驳斥外资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论调。然而,在去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即将离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以一番言辞激烈的发言再次点燃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论的不灭之火。此后,一系列社会名流跻身质疑外资的行列。另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比如商务部官员胡景岩和郭京毅,商务部的研究员王志乐和马宇则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口吻反击该论点。
一般而言,就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应该就事论事,重实质,轻形式。不过,有些所谓的公共政策问题本身子虚乌有,那么讨论其之被讨论的形式反而更加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外资—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似是而非的话语形式而生成的政策命题。
似是而非的论证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牵强附会。有些人高调批判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之后,为了言之有物,把正面的具体政策建议落到反垄断审查机制上,其它具体措施则乏善可陈。殊不知,反垄断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跟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外资企业可能是中国火腿市场的垄断者,但这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除非把火腿进一步附会成民以食为天的民生大事。如果外资真有对国家经济安全那样广泛的威胁,主要依靠反垄断机制来因应就近乎渎职了。然而,在话语层面,反垄断与并购是经常相提并论的;并购当中,跨境的外资并购往往是招人瞩目的。由此,反垄断与限制外资的并购的话语联系易如反掌。至于反垄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那就是言者有心暗示、听者也无心探明究竟,近乎蒙太奇效果的理论飞跃了。
第二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使用大量看上去热闹但完全不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某大学教授在所谓“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里用统计数据和图表显示更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独资而不是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合作,以此且仅以此证明外资意图保持垄断。这是把投资人追求对个别企业的百分之百控制(即独资)和对同行业市场的控制混为一谈,犯了常识的错误。该教授对外资企业掌握大量知识产权忧心忡忡,于是他呼吁中国政府为了抵御外资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要制定“知识产权法”。殊不知,我国早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否则连加入WTO都困难。而且,如果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以另眼看待外国人为宗旨,那我们就违背了国际条约义务。类似的,有些忧国人士因为操心国家经济安全,就大而化之地呼吁制定“国家安全法”,而国家安全的法规和机制早已有之。比如,某些类别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之一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备案;在上海,外国企业代表处必须设在经过特殊审批的写字楼,安全机制之细腻可见一斑。在战略层面上,那些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资的政策建议更大的误区在于他们不知道中国之所谓外资其实包括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而这些自家人的“外资”占我国FDI的相当高比例。这里的国家安全意义自不待言。
第三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不学不问、望文生义。为了证明以产业安全的名义限制某些外资是国际惯例,某知名大学校长称产业安全是WTO“安全例外”原则的核心。实际上,WTO体制下的“安全例外”(GATT的第21条)明确局限于国防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第四种似是而非是正话反说。对于所有谈论“产业安全”的文本,我们可以试着用WORD软件里的替换功能把“安全”换成“竞争力”。半瓶水可以说成是几乎满了,也可以说成几乎空了。说成“安全”,就有了敌我斗争的同仇敌忾。说成“竞争力”,自然就会引来追问:哪些行业因为什么原因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为什么要动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将其置于外资不能竞争的保护伞下?谁又将受益于如此保护下的“安全”?既然是市场经济,竞争就是基本法则。这个法则下就可能有个别企业的破产、或整个行业的全军覆没。个别行业的难以为继,一方面往往未必由外资竞争所致;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社会效益也未必不是好事。因此,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抽象地谈维护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遮盖了问题的实质:什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而又有基于公共利益获得额外的政策倾斜的理由?
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何以能在朝野得到这样广泛的响应?因为这样的观点听着自然顺耳。把“涉外”与“安全”联系起来不用费力,因为这样的联系本来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里;把它们在具体政策问题领域中分析、区别开来却至少要动用常识和理性。
“国家经济安全”的提法在执政党的十四大报告里还没出现,尽管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谈及“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第三段:“……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十六大报告同样在第七部分谈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时,提到“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看来,“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话语的出身就不好,从一开始就是限于外资和对外开放语境下的紧箍咒。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不是一定只有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才存在?当然不是。远者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词)显然与外资外贸无关,近者有“非典”几乎造成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与外资外贸无关。我们可以轻易罗列一系列国内环境、人口、教育、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非涉外因素直接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但是,这些都不会令朝野兴奋。攘外,只要是攘外,不论是真的还是嚷嚷的,却一定不乏“同去、同去”者。
自2002年十六大之后,外资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几乎都念叨着“国家经济安全”的诫语,有的在法规的操作性条款里,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规开头的立法宗旨部分。2006年出台的六部委“关于外资并购的规定”和稍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一五利用外资规划”里都非常突出地谈到利用外资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六部委的规定甚至苦心孤诣地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设立额外的通报与备案机制。孤立地看,这本无可厚非,但放眼横看才会看到真正的门道。自2002年末,国资主管部门颁行的法规无论是关于资本市场改革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的,还是关于国有产权评估与转让的,无论是关于产权无偿转让的还是向管理层有偿转让的,都闭口不提国家经济安全。此处无声胜有声!真正占据重点行业和垄断行业的主要是这些国有企业,而管好国有企业却被当作企业治理层面的“保值增值”问题,完全避开经济安全这样的宏大话语。相对于我国高度成熟和成功的外资政策与实践,国资改革起步晚、难度大、触及深、影响广,指导性理论几乎为中国独创,缺乏其它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如果国资体制改革不能顺利推进,会直接带来政治社会稳定性的问题,从而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如此重大的风险暴露面于不顾,只对着外资领域耳提面命地念叨经济安全,难免令人闻到一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安全感
毫无疑问,2006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对于基本顺利地走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5年过渡期的中国,2006年是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此后,中国不再有适用于过渡期的那些操作性、时间性非常强的具体开放措施的约束,而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的谈判进展缓慢,以多边机制为初衷的世贸组织的影响力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蚕食。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攀升,一方面,中国的作为与不作为皆对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实际效力构成日益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内需规模之大已经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30年任何时候更能够躲进自家成一统,管它外面春夏与秋冬。国际上,正如美国财长鲍尔森所坦率承认的,当前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甚嚣尘上,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觉得发达国家在开放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鼓吹开放,当开放伤害自己利益的时候就背信弃义,重新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所有这些国内外的利益格局和舆论环境都为中国经济重心在2006年后向内转提供了理由、原因、诱惑和便利。
2006年实际上没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安全的时候拿安全说事,还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这再一次显示安全与安全感是两回事。过去,我们不曾在政策层面反对中华老字号或驰名商标企业与外商合资;今天,却要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另设障碍。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但心理上却不难理解。今非昔比。今天我们背后的实力,给了我们在自己与外人间重新划定界限的从容。实际上或许无关重要,但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落别人手,这个感觉就足够重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重要得似乎可以支撑国家经济安全的重担。
我们曾经因为完全闭关锁国而走到了穷则思变、不开放就要面临国民经济崩溃的局面;而在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成就卓著的当前阶段,却开始了老和尚对要下山的小和尚的念叨: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为什么念叨的不是:为了真正的长治久安,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或许,这样的认识在政府的部门之间和日益分化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之间已经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共识?或许,现在是重新审视我们与自身之外的界线,重新给安全感定调的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