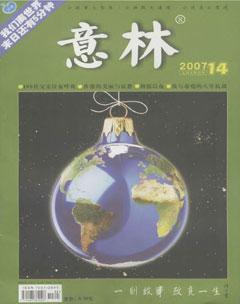法律门前
法律门前站着一名卫士。一天来了个乡下人,请求卫士放他进法律的门里去。可是卫士回答说,他现在不能允许他这样做。乡下人考虑了一下又问:他等一等是否可以进去呢?
“有可能,”卫士回答,“但现在不成。”
由于法律的大门始终都敞开着,这当儿卫士又退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弯着腰,往门里瞧。卫士发现了大笑道:“要是你很想进去,就不妨试试,把我的禁止当耳边风好了。不过得记住,我可是很厉害的。再说我还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卫士哩。从一座厅堂到另一座厅堂,每一道门前面都站着一个卫士,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就说第三座厅堂前的那位吧,连我都不敢正眼瞧他。”
乡下人没料到会碰见这么多困难,人家可是说法律之门人人都可以进,随时都可以进啊,他想。不过,当他现在仔细打量过那位穿皮大衣的卫士,看了看他那又大又尖的鼻子,又长又密又黑的鞑靼人似的胡须以后,他觉得还是等一等,到人家允许他进去时再进去好一些。卫士给他一只小矮凳,让他坐在大门旁边。他于是便坐在那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间他做过多次尝试,请求人家放他进去,搞得卫士也厌烦起来。时不时地,卫士也向他提出些简短的询问,问他的家乡和其他许多情况。不过,这些都是那类大人物提的不关痛痒的问题,临了卫士还是对他讲,他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为旅行到这儿来原本是准备了许多东西的,如今可全都花光了。为了讨好卫士,花再多也该啊。那位尽管什么都收了,却对他讲:“我收的目的,仅仅是使你别以为自己有什么礼数不周到。”
许多年来,乡下人差不多一直不停地在观察着这个卫士。他把其他卫士全给忘了。对于他来说,这第一个卫士似乎就是进入法律殿堂的惟一障碍。他诅咒自己机会碰得不巧,头一些年还骂得大声大气,毫无顾忌,到后来人老了,就只能再独自嘟嘟囔囔几句。他甚至变得孩子气起来。在对卫士的多年观察中,他发现这位老兄的大衣毛领里藏着跳蚤,于是也请跳蚤帮助他使那位卫士改变主意。终于,他老眼昏花了。但自己却闹不清楚究竟是周围真的变黑了呢,或者仅仅是眼睛在欺骗他。不过,这当儿在黑暗中,他却清清楚楚看见一道亮光,一道从法律之门中迸射出来的不灭的亮光。此刻他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在这整个过程中的经验一下子全涌进脑海,凝聚成了一个迄今他还不曾向卫士提过的问题。他向卫士招了招手,他的身体正在慢慢地僵硬,再也站不起来了。卫士不得不向他俯下身子,他俩的高矮差距已变得对他大大不利。
“事已至此,你还想知道什么?”卫士问,“你这个人真不知足。”
“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法律吗,”乡下人说,“可怎么在这许多年间,除去我以外就没见有任何人来要求进去呢?”
卫士看出乡下人已死到临头,为了让他那听力渐渐消失的耳朵能听清楚,便冲他大声吼道:“这道门任何别的人都不得进入,因为它是专为你设下的。现在我可得去把它关起来了。”
(杨松摘自《卡夫卡文集·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