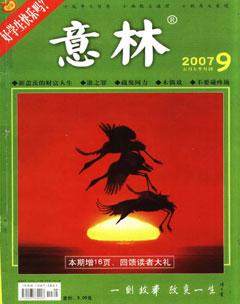得有人做出让步
李 斌
杰拉德·戴蒙德写了本书,将人类归为第三种猩猩。第一种是黑猩猩,生活在热带东非;第二种是倭黑猩猩(又称波诺波猿),分布在中非刚果。现代遗传研究发现,自视“天之骄子”的人类,其实与前两者的遗传差异只有1.6%,相同的基因则高达98.4%。或许正是这1.6%的差异,让人类拥有了动物中独一无二的素质,成为这个世界的征服者。
但在杰拉德·戴蒙德眼里,“世界的征服者”正在危及自己的生存。这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人类学家及田野生物学家,以善于写作“人类大历史”而获得过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在风靡一时的《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一书中,他试图警醒世人:“我们的前途,与另外两种黑猩猩一样黯淡。”
人类自身的两大恶习———破坏环境与互相残杀,正在将自己一步一步推向灭亡。技术的进步,更使这种破坏力达到空前的程度。杰拉德·戴蒙德担心:“人类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倒转历史,回返洪荒。”
过去的5万年里,人类把生活的范围从非洲与欧亚大陆的热带与温带区域,扩张到了全球,并进入太空。伴随这一扩张过程表现出人类的另一特征是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争夺,以及大规模屠杀同类的行为。
人类历史上的“灭族屠杀”屡屡发生。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杰拉德·戴蒙德觉得“难以捉摸”。也许,灭族屠杀最常见的动机是力量占优势的族群为了图谋弱势族群的土地和资源。或者,利益的另一种形态———权力斗争使某个族群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另一个族群。至于宗教迫害造成的大屠杀,则是一部沉重的血泪史。
“所有人类的行为特征中,直接从动物前驱衍生出来的,就是‘灭族屠杀”。它的两种常见模式,都有动物先例:不分雌雄,一律杀死———黑猩猩与狼;杀死雄的,留下雌的———大猩猩与狮子。不过,也有在动物界找不出先例的,1976年到1983年间,当时的阿根廷军政府逮捕孕妇后,会让她们一直活到生产之后,再将她们处死。
“我们与黑猩猩、大猩猩……一样,基本生活社群是队群,不容外人越界。”杰拉德·戴蒙德说,黑猩猩的行为显示,人类群居的主要理由,是防御其他人类社群的攻击。
科学家们推断,在两三百万年前有两三种人存在,但只有直立人存活了下来。一种可能性是,直立人将兄弟人类灭绝了。同样的情形,在几万年前又上演了一次。有创新天赋的克罗马侬人出现才两万年左右,原始的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杰拉德·戴蒙德认为,有可能是克罗马侬人使尼安德特人走上了绝种之路。
今天的人类是赢家的后裔,或许我们的祖先早就种下了自相残杀和破坏环境的祸根。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杀戮的原始冲动一直受到各种约束,那么现代的灭族屠杀者又是如何从伦理冲突中得以脱身的呢?研究者发现,有三种借口让这一行为变得“合理”,首先是“责怪被害人”,如认为自己是出于“自卫”;或自以为代表进步或文明;第三种借口则来自我们将动物与人类区别对待的伦理准则———将被害者当作畜生。
尽管诺贝尔奖得主、动物行为学家劳伦兹认为,动物的“侵略本能”会受到“抑制本能”的制衡,避免导致谋杀的结局。但在人类的历史上,由于武器的发明而常常使这一状态失衡。劳伦兹将此解读为“技术解放了人类的杀戮冲动”。
最近几百年间,人类发明了各种技术,能将自己送入太空,也能在一瞬间将人类抛入地狱。有很多理由,让我们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悲观,即使没有人按下核电钮,人类攫取地球资源和破坏环境的速度仍在加快,前景堪忧。
当有更多的人掌握着更强大的技术,竞争着越来越少的资源的时候,得有人做出让步。
(水木摘自《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21日)
——为被日寇屠杀的30万南京军民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