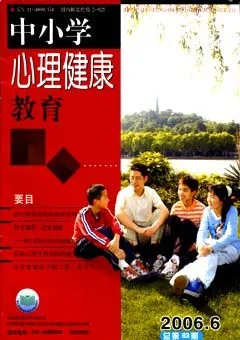心理辅导应促进来访学生积极的意义采择
学校心理辅导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个人成长,而非解决其一时的心理障碍或困惑。然而“成长”是如何发生的,却历来为心理学界所争论,并且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在诸派学说中,被称作“新皮亚杰一罗杰斯主义”创始人罗伯特·凯根提出的“结构一发展”理论对个体成长有比较深刻的见地,对学校心理辅导工作者和对青少年心理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师长很具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加以学习、吸取。
“结构一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意义采择”。一个人的自我是怎样发展的?在凯根看来,它是在一个人采择社会意义和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实现的。人是一个意义采择者。这种“意义采择”包括下面几层意思。
1.所谓的“意义”,包含相当宽泛的内涵。一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自己——他人之间关系的认识都是意义。至于一个人对自己过去经验的组织,对当前遭际的理解,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等等,也都是意义。如何采择这些意义,取决于个体在采择时所选取的角度。一个过于自我中心的人是很难把他人的意见作为积极的意义来采择的。他既有可能强化自己的意见,忽视他人的意见;也有可能张扬自己的意见,贬抑他人的意见。这种误入歧途的自我,问题出在他把自己的意见看作是惟一有“意义”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与否,都可以从其采择生活意义的方式和取舍中找到根源。
2.意义采择涉及两种显然不同的活动:静态和动态。采择意义的过程是一种动态过程,一种表现生命存在的运动,一种呼吁生活质量的运动。这种活动由自我来实施和体验,也即由个体为构成意义、拥有意义、保护意义、增强意义,或者威胁意义、失去意义的操作来表现。
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这种活动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对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或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感到平衡,也即他采择了平衡的意义,他就会按照这一意义去理解生活和处理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平静”的。
假如有一名学生,他的成绩并不优秀,其他能力也不突出,但他的父母非常爱他,从不因为孩子表现平平而感到沮丧;而这位学生对自己的状况也相当满意,并且丝亳不企图今后有出人头地的显赫或者富可敌国的钱财,那么他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安全、尊严担心,他就可以平静地、安心地过一段日子。在平衡被打破以前,这位学生采择意义的活动是相对静态的。
然而,任何静态都是相对的,因为平衡总是具有相对性。如果一个人因为新经验的介入,在思想震荡过程中,否定了自己对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或者否定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原有的认识,也就是说此刻他采择了失衡的意义,他就会按照这一与先前迥然不同的信念去理解生活和处理生活。按皮亚杰的说法,失衡是某一认知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以“新的图式”取代旧有图式的过程。失衡涉及到保护自我还是丧失自我,涉及到对自我的重新认识。这时,意义的采择活动是动态的。 譬如某个小学生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发现犯错以后撒谎能避免惩罚。渐渐地,他采择了撒谎有利于获利的意义。但是有一次因为谎话被揭穿以后,他遭到了很来历的惩罚。这个孩子开始重新考虑撒谎是否真正对自己有利。他在教训中认识到撒谎的获利是暂时的、浅近的,而说谎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惩罚。这一印象深刻的新经验让他开始重新采择生活的意义,他发现诚实比撒谎对自己更有意义。在这一认知的重大调整过程中,他处于失衡状态,他的意义采择是动态的。
3.只要—个人不停止意义采择,平衡就会走向失衡,失衡也总会导致新的平衡。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是一个人意义采择的必然过程,也是青少年自我发展的必经之路。
为什么会出现平衡一失衡这一现象?在凯根看来,关键在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文化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个体的认知水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家庭、学校、同伴团体等,也有不同的文化。对个体来说,自他来到世上的那天起,他实际上就处于文化的包围中。文化以“植入”的形式影响着个体,个体以“沉浸”的形式接受着文化。对于青少年而言,这一时期文化植入的最大危机是,难以把握好来自师长的“控制”和“放手”的尺度。即应该更多地施加来自成人的影响,还是放开手让孩子自己决定自己的文化取舍,人们常常会陷入困惑、彷徨之中。
倘若“植入”的文化与个体的认知或接受水平相匹配,双方相安无事。个体对文化所包涵的意义没有异议,则采择活动就没有冲突,个体也就处于平衡状态。这一平衡状态的时间有多长,则这一阶段也就有多长。然而,随着青少年的成长发育,他们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并且个体的生活环境各不相同,文化植入对于不同个体而言,差异往往十分明显。一旦“植入”的文化与个体的认知、接受水平不相匹配,个体对文化内涵就会有异议,采择活动出现冲突,个体也就处于失衡的状态。这种失衡意味着个体开始告别旧文化而迎接新文化。
失衡是危险的。但“危险”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危机,二是机会。一般说来,心理上的失衡总能使个体获得一种“发展”的机会,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接受新的文化,采择新的意义,向着高一阶段发展。然而失衡也有可能使个体丧失“发展”的机会,无法解决面临的危机,从而倒退到更加原始的阶段。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孩子遇到了父母离异这样一个事件,并且他自幼受到双亲的呵护,是一个缺乏独立能力的“乖孩子”。此时,他面对今后将只能与双亲中的一人生活在一起,这对小孩来说无疑是一个危机。可与此同时,他失去了原先过于温暖的家庭环境,这就迫使他更多去独立地面对新的生活,处理所遇到的问题。倘若他积极地去应付、迎接未来生活的挑战,那么对于自身独立性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反之,他会陷入痛苦、沮丧的情绪中难以自拔,导致成长受阻。
其实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由童年期的顺从或任性走向青年期真正意义上独立的过渡。用凯根的话说叫做从“唯我阶段”走向“人际关系阶段”和更高层次的“法规性阶段”。在“唯我阶段”,儿童习惯于以家庭的人际关系来理解学校和同伴的人际关系,他们时常为自尊;自卑、自大等内心活动所左右,思维与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自我中心,较少考虑他人的利益与感受。这样的自我强调的是一种“独立与分化”,而非包容与归属。因为受幼儿时期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影响,进入学龄期的儿童虽然有同伴关系,然而同伴之间的待人规则不是互惠的,而且小群体内外的界限十分明确。
在进入“人际关系阶段”后,家庭、学校和社会开始对少年输入互惠的文化。受此影响,少年人逐渐学会了以新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周边环境的舆论有意无意地在文化植入时降低个体的地位,强调人际的力量,强调个人融入群体之中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凡自尊较强、希望获得周围人们认可的少年,都会参照这样的信息,重新评价自己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进入这一阶段以后,个体就开始了“为别人而生存的历程”。
到了“法规性自我阶段”,青少年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已经逐渐减少了“迎合别人”还是“维护独立”的内心冲突,而开始学会以法律和规则作为依据来进行选择。这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一过渡时期青少年认知水平的提升往往与文化植入容易脱节,这使得他们对大量涌人的新经验在辨别与取舍时感到困难。因失衡引起的彷徨、不适应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称为“危险期”的青少年心理发展关键时期。当然,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心理失衡并不一定以剧烈的外显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并不为他人所察觉,这往往成为师长们在文化植入时方式不当的重要原因。
前面讲到,家长、学校掌握好“控制”与“放手”的尺度,使文化植入与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水平相匹配,将有助于青少年通过正确应对失衡,顺利走向,b理成熟。
对心理尚未成熟的儿童青少年,一定程度的控制是必要的。控制意味着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和行为约束。主流价值观、人际交往的正确态度、恰当的行为方式,正是在师长们的教育、管束下,“唯我阶段”、“人际关系阶段”的孩子才能够通过顺从、认同和内化,渐渐变成自觉的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但是随着心智逐渐成熟,青少年按同伴交往的准则和按法律、规则看待周围世界,采取反应方式的要求日趋强烈。外部文化植入与他们的认知水平不一致的冲突格外激烈,失衡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这一阶段,师长们对孩子适度的和协调一致的控制仍然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必要的放手则显得更为重要。师长们要敢于并且乐于让其青少年在失衡中寻求新的平衡,而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过多地去指手画脚、包办代替。因为后者对青少年心理成长关键期的飞跃将产生阻碍、延缓的作用。概括地说,这一时期,教师与家长应当尽可能减少管束,而代之以引导和放手为主,更多地让青少年自主采择生活的意义。
从心理辅导的角度看,帮助受导学生恢复平衡状态固然有利于个体的情绪稳定和生活正常;但一味强调维持稳定、平衡,必然会让对方沿袭因循,不思进取,自己否定了失衡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从而失去心理成长的宝贵机会和时间。失衡确实易导致个体情绪波动、适应不良,但与此同时,又能激发个体调动自身的积极因素,通过战胜危机达到高一阶段平衡。因此,辅导员在助人过程中最终的辅导目标应该放在帮助来访学生心理成长上,而不是简单地抚平来访学生“心灵的创伤”。
对于受导者来说是如此,对辅导员自身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在辅导学生遇到效果不如所期的时候;当我们的辅导对象不作应有配合的时候;当我们自感功底不足,无法使辅导深入甚至难以为继的时候,我们也会处于失衡状态,我们也会产生深刻的焦虑与困惑的体验。而正是这种焦虑与困惑,最能激发基本素质良好的辅导员去作认真的学习与反思,去寻求问:题的解决,一旦出现了突破,出现了转机,则辅导员本人无论在个性上,还是在业务上都得到了较之平时更有意义的成长。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