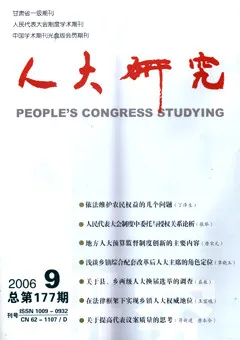我国宪法规定基层群众自治权的意义
一、帮助基层政府管理,解决基层社会问题
宪法规定基层群众自治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总结,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要求。在城市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主要是帮助城市基层政府维持城市社会秩序,这从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产生的过程和彭真当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1]。在农村实行基层群众性自治,主要是解决我国长期累积的“三农”问题。
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奉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政策,城市工业基础的建立主要依靠农业产品的积累。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2] 。城乡的二元政策,使农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与城市人群相比,已经陷入极度贫困的地步。从1980年开始,广西和其他一些地方兴起的村民委员会管理制度,完全是一种生产自救活动。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组织问题,也承担了一部分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村的社会秩序。
二、节省政府成本
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设有居委会(社区居委会)79947个,居民小组123.3万个,居委会成员45.4万人。村委会62.9万个,村民小组490.5万个,村委会成员265.7万人[3] 。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债非常严重,据有关统计资料,1999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大约在6000亿元左右,最高的乡镇、村负债大约为4000万元、500万元;到2004年乡村负债总额已达10000亿元。豫北某市村委会债务总额从1990年的0.33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0.50亿元,增长近37倍;乡镇债务从1990年的0.67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2.09亿元,债务增长了近18倍;特别是最近几年,多种原因导致债务猛增,全市乡村债务每年新增1亿元左右。湖北监利县从 1996 年开始,全县债务每年以 2 亿元人民币的速度增长[4] 。
我国当前乡村负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显示,按照我国当前的财力,国家根本无法承担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成本,基层群众自治的成本只能由基层群众自己承担。
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补充形式。基层群众性自治通过实行直接民主,使社会主义民主赋予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从基本制度和法律的规定,变为普通民众可以看得见且能够实际操作的具体方式。随着基层自治的逐步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将会有更多的人能享有和学会运用民主权利。
正如彭真在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没有民主法制思想传统,建国以后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忽视了民主政治建设,因此不论是群众,还是基层政府,民主法制意识都不强。我们党领导人民搞革命,革命成功掌握了政权,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民。建立政权后一定要支持、帮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单有人民代表大会还不够,还缺少一个重要方面。在最基层,涉及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事,要按群众的意愿由群众自己决定。在一个村子里,哪些事情可以办,哪些不可以办,哪些可以先办,哪些可以缓办,群众最了解,可以用民主的程序讨论,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他们把一个村子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有人说,群众的民主意识不强,很难实行自治。民主意识也是要在实践中培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村民委员会就是一个民主训练班。” [5]
从我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上看,基层群众性自治确实发挥了民主训练的角色,这种夹缝中的“草根民主”,现在却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四、促进政治发展
群众性基层自治激发了基层群众参与政治的欲望和热情,基层民主发展的重大突破是推动了基层人大改革,尤其是推动了基层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在一些地方还开始了“直接选举”乡镇长的试验。
关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有不同的看法,有基层民主论、党内民主论、行政体制改革、司法改革、人大制度改革等[6] 。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在高层实行宽松政策和维护群众权益特别是农民权益的号召之下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虽然不时有地方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表示了恐惧,但这种基层民主自治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在我国的政治发展路径选择中,一直有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争论,从现实上看,我国显然选择了优先发展基层民主的路径,在基层民主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必然对高层和中层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引发中层和高层的变化,推动高层和中层的政治发展。至于中国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在基层民主的影响下,下一步是先走高层还是先走中层,需要看具体情况,基层群众性自治在我国政治发展中无疑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
注释:
[1]1953年6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并呈送了《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的报告》。该报告指出, “由于我们现在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同时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即使在现代工业较发达的城市中,仍有很多不属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这种人口在有的城市中,甚至多至百分之六十以上。建立城市居委会是为了把街道居民逐步加以组织并逐渐使之就业或转业,为了减轻在区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参见《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2]参见周其明:《农民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3]民政部:《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6年5月18日。
[4]来自财政部科研所的一份报告也显示了与此大致相同的结果:2005年,全国乡村债务总体规模大致在10000亿元,占我国GDP比重的5%,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30%。
安徽省池州市乡村两级债务为4.9亿元,乡均1080万元,村均38万元;四川省通江县2002年底乡级负债5.32亿元,村级负债3.89亿元,仅村级负债就相当于该县当年一般预算收入的13倍;河南省化解乡村债务试点县温县乡村债务规模为1.6677亿元。来自豫北某地级市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该市乡级负债总额12.0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785万元;村级负债总额10.53亿元,平均每个行政村负债29.53万元。
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东津镇,目前镇级负债6800万元,村组债务还有1.1亿元,村均负债206万元。目前监利县778个村欠债在100万以上的村82个,50万到100万之间的139个。2004年9月份对山东省17个县市区所辖245个乡镇15865个村的调查统计,乡镇级负债总额47.35亿元,乡镇平均1932.7万元,债权与债务相抵后,乡镇平均净负债1359.4万元;村级负债总额35.8亿元,总债权30.69亿元,村均净负债3.23万元(青岛新闻网,2005年1月27日)。
豫北某地级市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全市乡镇中负债1000万元以上的33个,占21.43%,总额6.84亿元,占乡级总额的56.54%;2000万元以上的7个,占4.5%;负债最高的乡镇乡本级负债6858万元;绝大多数乡镇债务依存度都超过20%的警戒线。负债最高的村债务总额达到7600万元。参见焦元森、焦元玉:《乡村巨额负债考验农村税费改革》,http://www.cdnj.gov.cn/newsnsd/detail.php?id=1135476143&lb=%B5%F7%B2%E9%D3%EB%D1%D0%BE%BF&gjz=。
据湖南省益阳市统计局资料,该市128个乡镇负债额高达5.26亿元,乡镇负债面达82%,平均负债411万元,并有继续增加之势。3471个村委会负债8.89亿元,村均25.6万元。参见吴许元、吴彦:《化解乡村负债是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措施》,http://www.hntj.gov.cn/xhzj/xslt/200412160030.htm 。
据福建省农调队统计资料,该省被调查乡镇平均负债632.91万元,人均负债159元。其中,负债额在500万元及以上的乡镇占46%;负债额达1000万元及以上的乡镇占14%;被调查村平均负债21.98万元,人均70.70元。其中,负债额在50万元及以上的占16%;负债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占6%。参见林昭利、金秋江、林凯:《福建农村基层负债问题简析》,载《统计研究》2002年第1期。
[5]《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6]参见周其明:《中国法治与选举制度改革》,载《中国选举与治理》2005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