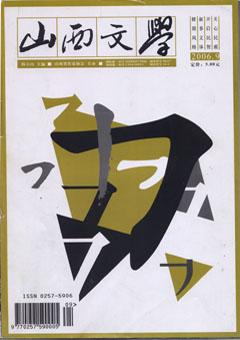1992,我们的蓝皮户口
鲁顺民
确实是1992年,这个时间是不会错的,因为那一年,儿子刚刚满一周岁,刚刚会说一两句完整的话。也确凿是这一年的春天,因为那一天早上除了能感受到空气里微微的寒意之外,还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这个早晨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早晨,因为在前一天晚上,我们那个近城的村落出奇地空寂异常,甚至显得有些沉闷。若是在平时,这个村落里某个院落的灯火一直会持续到下半夜才会熄灭,有两个嗓门特别大的女人扯开嗓子大笑,或者扯开嗓子大哭,她们的笑声或哭声会像蝙蝠一样在漆黑的夜空四下飘荡。他们都聚在一起或者谈天,和丈夫干仗,或者打扑克,情形相当壮观。但是,这个晚上忽然没有了动静,一时让人感到不大适应。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是县里要组织卖户口。这个消息没有通过广播,也没通过电视,然而这个消息却以奇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消息传播速度之快让人有些措手不及,远在八十公里之外的人都赶来了,已经在县城的旅馆里呆了整整一夜。这恐怕是中国消息传播的一种特色,消息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多多,记者参会采访,记者招待会,还有一种谁都不曾参与,然而大家又都在其中的“吹风”方式被普遍地采用,其中技巧被各级干部稔熟于胸。
所以,那一晚,村里突然沉寂下来。这一沉寂是前所未有的。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也没有过这样的情形,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这样集体性的沉寂。沉寂本身只是意味着一次直接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横陈面前,人们都在关起门来密谋、策划,但更多的则是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引起的不适应。
这可能吗?谁想买就买?这是真的?
也不是没有征兆。就在1992年的前一年,1991年,城镇户口的人,也就是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市民”们手里的购粮本作废了,公家不供粮了,他们吃粮需到市场上购得。但大家还是将信将疑。
不知道那一晚父母是怎样商量的,第二天还有课,因为查阅一个文言文引文的出处,备课到很晚才入睡。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将我叫起来,他手里拿着一张存单,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让我一早到银行将钱取出来。存单上的数字是6000元人民币。6000元人民币,应该是我那时候6年工资的总和。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县里统一卖户口的消息。一个城市户口,售价3000元人民币。父亲要将全家子弟全部转为城市户口,计四名,我两个弟弟,一个弟媳和刚刚一岁的侄女,共计120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高中教员12年工资的总和。
父亲命令我,必须在早上九点以前把款项全部取出,然后赶奔卖户口的地点——县城实验小学,如果有关系,尽量动用一切关系,把四个户口全部拿在手里。睡意像爆裂的炮仗一样被炸得粉碎,存单拿在手里,好像全家的前程都交在我手上一样神圣和庄严。
我一时心里感到太温暖了。要知道,一个农民户口糟害过我们多少农家子弟,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人,从上小学开始就受农民户口之累了,考学的时候,报志愿,有一栏就是填写你的户口属性,我们只能填“农应”或者“农往”,不能填报技工学校,技工学校是专为市民户口的同学准备的。因为是农村户口,我们没有被招工的权利,我们在学校里只配在集体劳动的时候积极一些,我们在那些市民户口的女同学不理不弄的眼光中发育严重滞后。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市民同学举手!我举起了手。因为我家住在县城边上,根本不知道“市民”“农民”的区别,以为住在城边子上便是市民无疑,不想,老师从隔着四排的教台上奔驰而下,狠狠地打落我举起的手,说:你家是个什么我不知道?你个烂农民装甚装?
我那时刚刚九岁,刚刚九岁的我便是一个“烂农民”,这种耻辱一直映在心底里,顿时感到身边的世界是如此的污浊不堪!
当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乡亲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赞扬你十年寒窗如何刻苦,纷纷说,这下好了,人家一下下就把“农皮”给剥掉了。确实,要剥农皮,途径有三,当兵,下煤窑,上大学;上大学点灯熬油相对难些,当兵、下煤窑是青年农民普遍的选择。
国家真是英明,知道一个受过“烂农民”创伤的人的痛苦,明码标价,可以花钱改变自己的身份了。要知道,弄一个市民户口是多么难啊。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敏感异常的词语在中国县级区域内流行,这个词叫做“转户”,另外一个词使劳动部门由门可罗雀变得炙手可热,这个词叫做“农转非”。前不久,我们县里呆了八年的县委书记被省里停职检查,主要罪名是给自己的司机“非法转户”,而副县长则身陷囹圄,罪名是买卖户口。
我被父亲委以这样的重任,哪里敢有半点懈怠?
我的同学是银行的副行长,取这些钱当然没有问题,可是,那一天不知道是银行的储备金不足还是手续过于繁杂,我坐在同学的办公室里,款子迟迟没有取出来,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天提款的人突然增加数十倍,早早在银行门外排起了长队。银行刚上班,先有半个小时的例会,我还在同学的办公室里等着,父亲骑着车子就赶来了,先是责怪我办事不力,后是骂我不关心弟弟们的前途,差点就把我的同学捎带进去。同学自然不怠慢,屈驾跑进柜台把手续办好,交在父亲手上。
赶到户口出卖的地方,人已经排到校门外边几十米长了。显然是来迟了。
正是早晨八九点钟,八九点钟的太阳正从树枝后面升起来。校门口一向是老干部们活动的门球场,要在平时,这地方早就被老头儿们吵得不可开交了。但是此刻,那么多人,那么长的队,大家井然有序地排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其实,里面出卖户口还没有开始,据说得九点以后。碰见几个熟人,大家看一眼,谁都不说话,这种情形让我想起1979年学校办文化补习班的情景,让我想起1987年涨价时的抢购风潮,熟人见了都不打招呼,生怕你把他的抢了去似的。
大约有3000人等候在那里,静悄悄地等候在那里,队形整齐而紧密,谁都插不进去。这种情形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一群人仿佛都走到了大漠深处,绝水断粮,谁也顾不得谁,谁要是对别人有所觊觎,那真敢刀兵相见。前面有一个同学,两个平时处得不错的朋友,打了个招呼,他们只是虚虚地应了一下,丝毫没有让插队的意思,只好排在队的末尾。谁知道,我刚排好,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回头再看,后面又排出了十几米。
据说,此次户口出卖,是基于广大群众对城市户口的急切需求而限量出卖,这里头,有已经找好工作,因为没有户口而不能转正者,有一定专长因为户口限制而不能录用者,有一定领导才能因为户口限制而不能成为国家干部者,一句话,是因为户口限制了人才的出路,而偷鸡摸狗可导致县委书记丢官,中央最高层发现这一问题,为保护干部计,于是出台了这样的政策。
既是限量,肯定抢手,既是抢手,即有竞争。我毛估了一下,眼前这近3000多排队买户口的人,以每人手里3个待买户口计,这么长的队伍最少也在万个以上。排除中途意外情况不论,就我
排队的次序而言,已经在4000之外了,限量会限在4000以内吗?
迟迟不见公安局的人来,已经有不少人越墙而入,到里面排队去了,门外的人大声呼喊要注意道德和秩序。好在,公安局的人很快就来了,他们从铁门进去,接着就来了维持秩序的武警,吆五喝六把队伍拾掇齐整了。接着,银行的人由我同学带队也开进了现场,他们携带着银灰色的储钱箱。我同学看见了我,但只看了一眼,也没有什么表示。这种情形之下,任何带有暧昧色彩的暗示都可能招致公愤。
等买户口的人持着各种证明手续以及现款缓缓进入现场,我才发现并不像想像的那么严峻。公安局户政股的人一连占用了六间教室在办理各种手续,每一个地方,户籍、银行、民政部门的人都在。一条长龙立时被一截为六,尽管如此,队伍行进还是非常缓慢,人们难免等得焦灼不安,等我排到离办事窗口还有一丈之地的时候,已是上午快十一点多了。当天的课早已误了。事后,校长并没有因此而责怪我,因为我发现他也在排队,为他一个给出去人的三姑娘,他正在设法把她办成学校的校工。前县委书记之下台,他也有一份罪责在,县委书记被处分,三姑娘也随之清退。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我同学的父亲,一位在公安局待了近三十年的老刑警在那里维持秩序。这个同学在大学低我一级,在大学的时候,这位父亲在送他儿子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招呼他的儿子,事实上,在大学三年同学期间,我至少尽到了一个兄长之责。当年,他病得眼看要休学一年,我偷偷用煤油炉子煮稀饭给他吃,拉下脸来求女同学的母亲给他在医院求医问药,这位同学便不必休学就可以顺利毕业。假期,他家里当恩人一样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这位公安老父亲对我是千恩万谢。
我跑到他跟前。但是他居然认不出我来了。
他问我:你干啥!
一副公安局的口气。
我说:大爷!
他问我:你干啥!
我报上了姓名,他仍然没有想起来。事情刚刚过去两年,他儿子毕业之后已经做了我的同事,他竟然把以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脑子像是被格式化过的磁盘一样没有任何信息。他终于发话了:排队去排队去!然后就公事公办地坐在那里。
我仍然没有走,一种屈辱和愤怒从心里升起来,我说:大爷,你不认得我了?
他看了看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说:你要干甚!
我说:大爷,我排了半天队,你能不能给通融一下,我还有课回去要上。
他说:你们家还有农民?
我说:是呀,我们家都是农民。
他说:你们家不是在城里?
我说:是,都在城里。
他说:城里也有农民?
我说:我们家,是城里的农民。
他忽然笑了:你也不用套近乎,排队去。然后,他又公事公办地跟同事聊天去了。要说这位老叔完全不近人情也不对,当我再回去排队的时候,原先的位置要插进去可想而知会引起众怒,正当我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走了过来,将我原来排队的位置用警棍隔开,对我说:你还排在这里!
完事之后,他扭头走开,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看了我好几眼,眼睛里充满疑惑。人在这时候,突然变得格外冷漠。
然而,他这种冷漠又何尝不可以理解?这一天之后,如此众多的人突然之间就要和他平等相处,成为他们“市民”行列中的一员,而且不费吹灰之力花钱就可以买得。就像一个费九牛二虎之力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才踏进大学校门的人,突然惊奇地发现过去那些不用功学习差的同学也踏着清晨的钟声同自己一样走进教室;就像一个从小干事做起的干部,突然发现有一天官员也明码标价在那里出售。这种冷漠是可以理解的,岂止应该冷漠,简直应该愤怒。
就在那一天,在庞大的买户队伍边上,有三五闲人抱着胳膊在那里窃窃私语,身份不一,有干部,有职工,有工人,就是没有农民。农民都排在队里挤着。他们闲适的脸上写满了一种叫做酸涩和鄙夷的东西。
各种手续总算是顺利地办完了。
卖户口一直持续到傍晚,仍然有许多人没有如愿,公安局的人撤摊下班,银行的人满载而归,没有买到户口的人们在昏暗夕阳的阴影里显得很麻木,就像扯开一张没有兑奖消息的彩票一样。但是很显然,人们由失望而积攒起来的情绪已经到了极限,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他们久久不肯离去。
这时候,主管公安的县长助理对着失望的人群宣布:同志们,不要失望,不要悲观,不要丧气,鉴于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户口明天还卖一天,地点改在公安局,希望同志们看好自己的钱,拿好自己的手续。
县长助理口才好,话有号召力,据说他给上级口头汇报工作时,数字可以精确至小数点后四位数。
果然,第二天,卖了一天,买者甚众,第三天又是一天,买者亦众,到第四天的时候,还有零零星星的人进公安局办理交款手续,后来大家发现,这半个月内,出卖户口的门一直敞开着,有求必应,货源充足,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限量发售。
交钱,办手续,注销农村户口,隔了一个多月,买户口的人才去派出所办理转户手续,但是,当人们去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时候,最终发现了里面的不同,一是户口本不同,城市户口本是暗红色,而他们的是天蓝色的;二是在迁移的人名下面赫然盖着一个长方形印鉴:买户。这种户口被户政部门称为蓝本。不知道是为了区别还是有其他原因,但是户政部门和县政府信誓旦旦地向蓝本持有者表示,无论蓝本还是红本,其功能是一样,待遇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尽管如此,父亲和所有蓝本持有者心里总是感到不怎么踏实,不怎么对味。
五十多岁的父亲和母亲没有为自己买户,父亲说我就是转成个市民又有谁会给我安排工作?他说得无奈,也说得心酸。在四十岁之前,父亲几乎每天在为成为一个国家正式干部奋斗着,初中毕业,想去当兵,结果祖母拿着一根绳子就要给他上吊,后来被县里抽调为“四清”干部,阴错阳差又错过了转正的机会,回到村里从民兵营长一直做到大队支书,后来犯了错误抽回公社。那时候犯个错误跟犯个罪差不多,他老人家一直对我讳莫如深,后来我查县党史资料,偶然在档案局里发现他的处分决定,叫做“瞒产私分”。好家伙!这是光荣呀!我对父亲说:你这是光荣啊!谁想,父亲的脸上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难堪,显然这个错误对他而言还是一块心病。后来有人告诉我说,1970年代的某一年,工作队要求大队上缴国家100万斤公粮,父亲跟蹲点干部发生了严重冲突,100万只完成70万,本可以成为“大寨式大队”的希望化为泡影不说,父亲也因此马失前蹄。要知道,这个100万岂止可以成为国家干部,简直立即就可以做某一个公社的书记的。但他给“瞒产私分”了。总之,他的干部梦是彻底地破灭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
1992年,邓小平南巡,南巡的讲话在县属各企业,尤其是我们那个偏远小县还没有发生应有的效应,县属各企业还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老企业无一亏损,新企业还在陆续上马,县财
政在那一年突破1000万大关,县域经济还在旧轨道上一步步滑行着。刚开始,我还以为卖户口是南巡讲话的结果,心怀感激,这个口子终于敞开了,可是近年才知道,那是国家的统一布置,那一次全国卖户口所得款项达900亿之巨。
“蓝本”持有者当然就有资格找工作了,劳动部门门庭若市。那时候,我的一个同学正好担任劳动局办公室主任,1992年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就拥有了手机,那时候还叫“大哥大”,通话的时候就跟拿着一块砖头捂在脸上一样。砖头捂在我同学的脸上,大批农民扔掉锄头拥入县属各企业中成了拿工资的工人,还有运气好的进入了县级各机关。可是毕竟僧多粥少,安排的工人还不及买户者的十分之一,全县近万农民一夜之间拥了城市户口,也在一夜之间县里突然增加了一支近万名的失业大军。户被销了,地被抽了,没地种的这些蓝本持有者顿时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国家不久又出台政策,凡持蓝本而没有就业者,土地重新补回。当然,这是后话了。
过了不到两年,县属各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化肥厂破产,塑料厂停产,化工厂承包,电石厂因电价上调利润日薄,铁厂因无技改资金一直停留在1950年代的水平,不久被黄河水淹,接着,百货公司倒闭,副食果品公司倒闭,制药厂红火了不到一年,把贷款全部花完,药品质量不过关迟迟不能注册上市,倒闭,医疗器械厂倒闭,全县惟一的国营企业水泵配件厂在不久之后也停产,厂区全部拍卖,倒闭。不到五年的时间,那些进入企业成为正式工人的人拿着蓝本的同时,又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叫做下岗工人。
1992年的户口出售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买户的人肯定不会像当年那样心高气旺希望户口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命运的变化,但对他们而言,这肯定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跟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因摸不准市场行情而投资失利,因年景不好而歉收,因娶不起媳妇铤而走险到四川买一个女人回来,打工之后被三年五载拖欠着工资一样,是农民一生中众多闪失中的一次闪失,没有带来什么,也不会带走什么,权当做了一回梦罢了。
前几天回乡,碰到一个比我高一届的高中同学,他也是“蓝户口”,同时他还是最后一个倒闭企业的职工,企业倒闭之后,媳妇跟人跑了,这个人变得有点神神道道的,拉住我说起他的媳妇:她迷窍了嘛,她脑迷了嘛,我下岗工人不假,可再下岗也是个工人呀!国家负担我哩,一个月一百块低保,一百块呢!她迷窍了嘛,后来怎样?嫁了个农民,他妈的,她嫁了一个农民!如咱?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抬起头,天上的太阳还朗照着,周围市声如潮。我说:天已经不是那个天了,你还守着残梦干什么?
他说:什么?他自言自语:咱好歹是个工人是个市民呢,一个月一百块钱,相当于过去十级工的工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