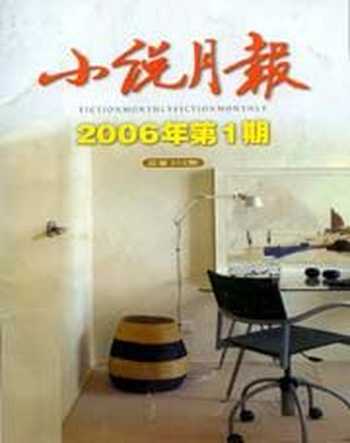狂奔
尽管他们尽量不让人们知道他们在城里做什么事,但后来该知道的人们还是知道了,尽管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住,但后来人们还是知道了他们就住在厕所里。先是,他们怕极了让老家的人们知道他们住在厕所里,所以他们从来都不让老家的人来,几年来,几乎是断绝了来往。在他们的老家,当然是乡下,人怎么能够住在厕所里边?只有猪,那还得是坑猪。但这是城里,城里的厕所里有上水和下水,墙面上还贴了亮晶晶的白瓷砖,但瓷砖再亮,也还是厕所。进了厕所那个漆了绿漆的门,往左是男厕所,往右,是女厕所,正对着一进门的地方是一间屋,这家人就住在这个小空间里,这间屋当然也有一个门,不单单是一个门,挨着门还有一个窗,窗上还另开了一个小窗口儿,刚好可以让人们把手伸进去,或里边的人把手伸出来,进厕所,要是解小手呢,就是两毛钱,要是解大手呢,就是五毛钱,五毛钱交进去,里边还会把几张软沓沓的再生纸递出来。这公厕的外墙呢,也贴了瓷砖,亦是白色的那种,给太阳一照有些晃眼,门头上,照例是两个很大的红字:公厕。公厕这两个字是居高临下,让远远的人一眼就能看到。公厕那两个大字的下边又是两个窗子,亦是漆了绿色的油漆。只是在那窗台上放着不少瓶瓶罐罐,因为是夏天,这公厕的窗下还有一个炉,那种极简单的三条腿铁皮炉,铁皮炉上安一节生了锈的铁皮烟囱,歪歪斜斜朝着公厕墙壁那边,所以那公厕的墙上有给烟熏过的痕迹。靠着这铁皮炉,是一个很大的运货的白皮木条钉的那种箱子,里边是一口炒菜的小铁锅,一口做饭的钢精锅,还有就是几个塑料盆子,红的和绿的,或者还会有几个塑料袋子,袋子里是几棵青菜,或者是两根黄瓜和几个土豆,或者是芹菜和菠菜。这就是这家厕所人家的生活,在夏天,他们的生活好像还宽展一些,要是到了冬天,这些东西就都得搬到公厕里边去,公厕里就显得更加挤挤的,碰到上边有人下来检查,他们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没人让他们住在这里,这里只是公厕和看公厕发发手纸收收如厕费的所在,谁让你一家子住在这里讨生活?而且,他们居然还有那么大一个儿子,人们都注意到他们的那个儿子了,个子很高,总是趴在一进门正对着的那个小屋里写作业。这间屋呢,顶多也就是十二平方米,却放了一张大床,床靠着里边,外边的地方就刚刚只能放下一张小办公桌,放了办公桌,就没有放椅子的地方。但桌子下和床下还有墙上都放满了和挂满了各种零零碎碎的东西,因为他们要生活,床下先是两个大扁木箱子,里边放着这家人四季的换洗衣裳,还有小木箱子,里边是冬天的鞋,还有就是各种的面袋,都挂在墙上,一袋是米,一袋是面,一袋或者还是米,这回却是小米,一袋或者还是面,这回却是玉米面,还有更小的袋子,是豆子,这家人爱吃豆粥,豆子又是好几种,就又有好几个小小的袋子,这就让这里多少有了一些乡村的气息,让人们想起他们原是从乡下来的,但他们一定有背景,别看是看厕所,也不是人人都能找到这份差事的。还有就是一束罂粟莲蓬头,猛看上去像是一束干枯了的莲蓬头,却是罂粟的种子,这家人原想找块地种种他们的罂粟,他们也只是喜欢那花的美丽,但公厕旁边哪有什么地可种?那罂粟种子就一直给挂在那里。屋子本来小,这家人却又在床的前边拉了一道布帘儿,两块旧床单拼起来的,布帘儿上边的花色早已经很暗淡很模糊了,就像他们的日子一样暗淡和模糊,没一点点鲜亮的地方,这样一来这屋子就显得更小,拉口道帘儿全是为了他们的儿子,也是那做儿子的,一再地争取和抗议才给拉上去的,这样一来,那做儿子的就可以安安心心躲到帘子后边去写他的作业,不怕被别人看到。这儿子为了怕人看到他生活在公厕里,只要是在家就总是躲在帘子后边,躲在后边也没别的事,就只是看书和不停地做题,所以一来二去学习出奇的好,常常考试是全校第一。像他这样大的学生,学习好,心事就重,学习越好心事越重;心事重到后来就会向病态方面发展,一开始他是怕被人们发现他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他尽量躲在布帘子后边,像一只土拨鼠,土拨鼠的安全感就是要不被人看到。到了后来,他干脆是天没亮就早早离开家,中午那顿饭就在学校里吃了,晚上一定要等天黑了才肯回来,天不黑就不进家。从公厕,也就是他的家出来的时候,天还没亮,但他还是担心被人看到,低着头,把车子猛地往外一推,车子“哗啦哗啦”好一阵响,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担心厕所里会冷不丁走出个熟人,心总是怦怦乱跳,可是呢,既然是夏天,厕所门口的那块空地上就总是有人,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坐在那里说话,他便宁肯在不远处的小饭店门口蹲着等,等着人们走散,车子就停在那里,那里有路灯,后来他干脆就在灯下看书,所以有人总是能看到一个学生在那里看书。后来做父母的发现了儿子总是在那里不肯进家,有时候会把饭端了过去,一碗菜,上边扣两个大馒头。这做儿子的,性格和他的名字恰恰相反,他的名字叫“大气”。这家人姓刘,他就叫刘大气。只不过那个“气”字后来让老师给改动了一下,改成了“器”字,老师在课堂上说刘大气你是什么气?气只是一种看不着的东西,你这一生只想做看不到的东西吗?你今后叫“大器”好了。刘大器当时的脸有多红,但他在心里佩服极了老师,老师只给改了一个字,自己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现在是夏天,天真是热,这里有必要再说一下公厕附近的情况:公厕前边原是一片空地,往南是街道,往西是菜市场,所以人们没事就总爱围在这里,坐在这里把买来的菜择一择,或者把买来的豆荚用剪子铰了再铰,用来晒干莱,最近这一阵子,那些住在公厕附近的老太太们好像特别热衷做这件事,一个人开始这么做,便马上会有许多人跟上做,好像不这么做就是吃亏,其实首先做这件事的人是大器的母亲,她年年都要晒许多干菜在那里,白菜啦,蘿卜条儿啦,豆荚啦,茄子啦,晒干了,收在一个又一个小口袋里再挂在墙上。这种事,在城里已经好多年没人想起做了,这里有一种近乎于怀旧的东西在里边,那些上年纪的人忽然,怎么说呢,是一种触动,便都行动了起来,买来豆荚和萝L,或者就是茄子,就在公厕那块地方,一边说话一边做这件事,这一阵子,公厕的前边地上就总是晒满了各种切成块儿切成丝的东西。大器的母亲呢,是外来户,而且又是个看公厕的,人们怎么看她?在心里,是侧目而视,是种种的看不惯,而忽然,她可以与人们亲近了,那就是她可以帮着人们照看那些等着晒干的蔬菜,她的记性又好,哪张报纸上晒的是哪家的萝卜条她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夏天的风雨说来就来,她还得即时把那些等着给太阳晒干的东西收回去,等太阳出来再即时晾出来,这样一来,人们都得感谢她,都好像多多少少欠了她什么?还有,就是人们纳凉时的屁股垫子,各种各样碎布缝的屁股垫子,在不坐的时候也不再带了回去,而是都放在了她那里,下来了,要坐了,就从她那里取出来,说完话,天不早了,再由她——弯腰收回去,还把上边的土再拍拍。在这个夏天,公厕里可真是热闹,人们后来明白那热闹是因为公厕里养了两只叫蝈蝈,一只还不行,
是两只,一只挂在前边的窗上,一只挂在后边的窗上,而且呢,这两只蝈蝈特别的能叫: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一只叫得快一些,很急促,一只叫得慢一些,几乎是慢半拍,但这只叫得慢的蝈蝈声音特别的好听,就好像有人在那里抖动小铜铃。两只蝈蝈一起叫起来的时候甭提有多热闹,热闹的都有些吵,但夏天本就是这个样,一切都是吵吵的,闹闹的,让人觉着日子无端端的是那么闹闹的富足,而那蝈蝈的叫声亦是要人怀旧的,让人心里有一份若有若无的触动,只是那触动来得太轻微,仔细想它的时候又会想不真切,又会没了。夏天的晚上,人们是吃完了饭又要下来,先是,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说他们年轻他们又都不年轻了,都四十左右了,他们这个岁数既不想去舞厅花钱而又不甘寂寞的岁数。这夏日的傍晚他们又不愿在家里热着,便有人把录音机提了出来,在那里放音乐,一开始是无心,但音乐这东西是有煽动性的,这煽动就是让人们想随着它的拍子动,这几天,便有人在那里跳舞,女的和女的双双地跳,后来有男的加入了,便是男的和女的双双地跳,他们在那里跳,便有人在那里看,有技痒的,还自动过来教授舞技,是个瘦瘦矮矮的男子,在报社工作,现在退休了,在家里赋闲。那边在跳舞,这边靠近公厕呢,老头和老太太就坐得更靠南一些,好给那些跳舞的让些地方。这样的晚上,是苦了大器,他就只能把车子停在了路灯下看书,有人看到了,看到看公厕的老白,人们叫大器的母亲叫老白,人们看到老白端了一碗饭菜出去了,到街对过去了,那是一个很大的碗,有时候碗里是米饭,上边堆着菜,茄子山药还有一个咸鸡蛋,有时候是馒头,下边是菜,上边是馒头,而且,还有一个咸鸡蛋,这家人特别能吃咸鸡蛋,到了冬天,他们为了省钱,从不吃菜,就只吃咸鸡蛋。人们问老白,也就是问大器的母亲去干什么?端碗饭菜给谁?老白觉得这没啥,便说了实话,说她儿子在对过儿的路灯下看书。她没敢说大器是怕让人们看到他,因为这,大器的父亲和母亲很生气,说大器心里太虚荣。“你那心里有什么?有什么?除了虚荣我看还是虚荣!”大器的父亲说城里的厕所比村子里的好房子还好许多呢!大器的父亲上过学,怎么说,居然还上过高中。他对大器说:“我也上过学,我也年轻过,但我就不虚荣广大器不说话,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蝈”叫着,灯已经关了,这往往是睡觉前的事,因为黑着,没人能看到大器眼里有什么在闪闪的。三口人,都睡在一张床上,都脚朝外,这样起身的时候,谁也不会影响谁,大器睡靠墙那边,大器父亲睡中间,大器的母亲睡外边。大器那边的墙上挂了一个小灯泡儿,用一个绿塑料壳子罩着,大器就在这灯下看书,幻想着他美好的闪闪发光的未来。耳边是东边那条河的“哗哗”声,只有在夜深时分,那河水的声音才会清晰起来,才会“哗哗哗哗”一直响到人们的枕上。
大器十七岁,长了一张特别白皙的脸,个子也高,但就是不怎么爱说话。这么一来呢,气质就像是特别的与众不同。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众不同,往往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能引起别人注意,自然就会有朋友,大器最好的朋友是高翔宇,事情就是高翔宇引起的,说是高翔宇引起的又好像不对。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开头出了错,到后来往往会越来越难收场,这开头的错全在大器。问题就出在大器穿的那条军裤上,现在谁还穿军裤,但大器居然就穿了一条,洗得有几分旧,颜色淡了几分,却更好看,在别人,也许穿在身上不会好看,而在大器,什么衣服穿在他身上都好,这样一条军裤,下边又是一双洗得泛了白的那种两边有松紧带儿的懒汉鞋,这种鞋子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穿了,可大器偏偏穿了这么一双,效果呢,更加显得与众不同。大器的身体是那种正要往足了长,却还没有长足的那种,架子已经有了,肩宽,腰细,到了胯那地方又稍微宽一些,这种身材穿什么都好,大器又喜欢干净,他在心里明白,自己能和别人比一比的就只有干净,所以他的衣服上总是散发着一种洗衣粉的味道。因为大器穿了一条军裤,那天,和大器关系最好的高翔宇,不经意地随便问了大器一句,高翔宇问大器什么?问大器的父亲是不是在军队里做事?大器不该犹豫了一下,脸红了一下,居然,说“是”。只这一个字,一个人的生活便马上发生了变化。高翔宇再接下来问,大器的脸便更红了。高翔宇问大器的父亲在部队里做什么?是不是军官?这一回,大器摇了摇头。高翔宇说既然不是军官,最差也是个志愿兵吧?大器在心里觉得这种关于志愿兵的虚拟自己好像还能接受,便点了头。高翔宇继续问下去,问大器的父亲是不是开车的?开车的志愿兵好像可以在部队留得久一些,工资也不低。一问,大器又点头了,大器在心里觉着开车很不错,他希望自己的父亲就是个开车的,大器甚至希望自己的父亲浑身上下都是气油味儿。几乎是,所有的青年人都是喜欢虚拟的,虚拟有时候可以给人以想象的喜悦,大器这个年龄离世故还很遥远,他不知道虚拟是种种细节慢慢慢慢把一切虚假的裂痕弥合得天衣无缝,这需要更多的精心设计,在这个世上,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骗子,骗子是细节大师,可以把所有有关的细节都想到,可以编织漫长的故事而不露出一点点破绽,他们的故事甚至可以延伸到人家的祖宗八辈,他们甚至是编族谱的高手。但对于一般人,一旦说了一句假话,一旦虚拟了自己的出身,到后来总是要破绽百出。实际上,从那天开始,大器就已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了,这个虚拟的世界就是“军队”,他既然有了那样一个虚拟的在部队里当志愿兵的父亲,生活便开始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和高翔字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早上他们要在湿漉漉的操场上跑步,在跑步的时候,大器觉得自己应该有军人子弟的样子,这种想法真是奇怪,这奇怪的想法让他的跑步步法甚至都起了变化,那就是,他夸张他的步子,步子邁得又大又快,跑完了还要在原地跑一阵,也是不经意,也是有意,大器对高翔宇说新兵训练都是这样子跑。怎么说呢?假话让大器进入了一种角色,只要和高翔宇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来了,那种感觉自己就是部队子弟的感觉就来了,心里是乱的,但乱之中有一些甜美,有一些反常的激动。还有一次,大器和高翔宇去学校外边吃中午饭,学校旁边的那条东西路上正在过军车,一大溜军车,都蒙着布篷,军绿色的布篷。高翔宇看着军车,随口问了大器一句:你爸是不是也开这种军车?大器没有马上醒过神来,说:谁爸爸开车?你爸呀,还有谁?高翔宇看着大器,说你爸是不是也开这种车。大器简直是给吓了一跳,马上就从现实中回到虚拟的角色里来,摇摇头,说他爸开的是小车,不是这种大军车。高翔宇马上就又在一边问了,问大器他爸开的是什么车,是部队里什么首长坐的车?是三千?还是桑塔纳?还是奥拓?大器一时答不上来,脸就更红了,一张脸憋得通红,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但嘴里已经说了:是三千吧?高翔宇又问车是什么颜色。大器这才定下心来,说是红色的三千?高翔宇说:红色的车?部队首长很少坐红色的车吧?高翔宇这么一说,大器的脸重新红了起来,说:有时候开红色的,有
时候开黑色的?高翔宇在一旁看定了大器,说:那就是说你爸爸不是给固定的部队首长开车?高翔宇这么说的时候,大器便把话岔开了,大器说哪天有时间让他爸爸用车接了翔宇去部队玩一玩儿。玩什么呢?高翔宇问。打枪,也许就玩打枪。大器心慌意乱地说也许还可以打手枪,大器朝远处比划了一下,说打手枪最好玩儿了。“砰——砰——砰砰——”大骂嘴里发出了一声呼啸。高翔字在一旁侧着脸看着大器,心里有几分羡慕,一般男孩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喜欢上刀和枪,喜欢上部队,其实是喜欢军队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若是真要让他们吃吃部队的苦,他们往往又会马上知难而退。高翔宇看着大器,又问大器的家在哪个部队?是不是跑虎地那个部队?大器却说不是那个部队,怎么会是那个部队?是哪个部队呢,大器想起了这个城市南边的空军部队,大器说,他们的家,就在那个空军部队大院里边。这是一种明确,一种确定,从这一刻起,一切模糊的虚拟都在一点一点清晰起来,方位和地点还有飞机,不容更改,不容再发生什么变化,更不容许大器退出这个虚拟的空间。在大器他们学校,真还没有人知道大器的家在什么地方住,但到了后来,同学们都隐隐约约知道了大器的家在空军部队里,部队好像总是离城市很远,最近也应该在城市的边缘。直到出了那件事为止。那件事,或者可以说是那个事件,那个事件的发生原因真是太简单,是因为天上忽然下开了雨,是雷阵雨,下得很猛,打着雷,是炸雷,什么是炸雷?炸雷就是像爆炸一样,“咔嚓嚓——”像把什么一下子劈開了,这就是炸雷。人们都说那事件与下雨分不开,说到下雨,有多少故事都发生在避雨这件事上,在这里,有必要把大器的家,也就是那个公厕的地理位置再说一遍,那个地方,就叫河西门,是城市东边的那一带,东边临河,在城墙上,原是有个小便门方便供人们出入的,所以叫河西门。现在这个城市既然茁壮地成长了再成长,河西门一带的城墙早就给人们拆除了,只不过,留下这么个名字。离大器家的公厕不远,往南,是一家医院,那原是轻工局的医院,轻工局在早几年就不行了,所以连累了这家医院,一是设备日见陈旧,二是总是进不了好的药品,没钱,医院就这样渐渐垮了下来,垮了有那么四五年吧,偌大一个医院每天只有少得可怜的急诊病人前来打针输液,也只是救救急,等病人的病情一缓解,便会马上又去了别处。医院虽然一天比一天不景气,但医院的大楼还在那里,又加上这医院在好地段上,这几年,忽然就又起死回生好转了起来。原因是,这家医院忽然变成了这个城市第一家性病医院,门诊楼前突然多了三个牌子,一块是“卫民健康性病专治医院”,另一块是“男性专科医院”。还有一块呢,是“XXX市城区血站”,在这里,我们说医院做什么?这医院和大器又有什么关系?和我们的故事又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在这个夏天里的某一天,大器的同学高翔字来这个医院了,他怎么会到这家医院来看病?问题是,高翔宇有没有病?高翔宇没病,他的父亲在报社发行部上班,报社的发行部是最最有办法的部门,可以和各种各样的单位发生亲密而暖昧的关系。高翔宇的父亲给儿子找了个健康检查卡,卡是白来的,所以高翔宇的全家都来了,三口人都来查一查。不知出于什么想法,高翔字非要到外边去留他的尿样,他不能容忍医院的厕所里有那么多的人,取一个尿样,大家都还要排长队。高翔字已经从医院的窗里看到外边的那个公厕了,那公厕红红的两个大字召唤他去那里。其实这时候天已经开始下雨,只是星星点点,等到高翔宇从医院里出来,往西拐,再往北,到了那个公厕,雨才猛然大了起来,这么说,高翔宇其实不是到公厕来避雨,但这又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他进了男厕,解了小手,把一小部分尿液小小心心尿到那个小塑料杯里,做完了这一切,他从男厕出来,他怎么能想得到呢,他怎么能想得到在这里会一下子看到了大器。高翔宇在小便池那边取尿样的时候就听到了大器在说话,但他没想到说话的人会真是大器,他只觉得声音熟,很熟,好像是自己的熟人,是谁呢?这个熟悉的声音在应答着另一个声音,另一个声音就是大器的母亲,大器的母亲让大器快帮帮忙,快把晾在外边的豆荚啦茄子啦什么的收回来,大器虽不愿意,虽在看书,但还是一边答应着,一边跑了出来,他放下手里的作业,从布帘儿里出来了,脚上穿着拖鞋跑了出去,外边是“啪啪”落地的大雨点子,大器把地上晒的东西收起来就往回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翔宇突然从男厕那里出来了,手里拿着个白色的小塑料杯,里边是一点黄黄的尿液,先是,高翔宇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大器两只手撑了报纸。报纸里是快要晒干的豆荚。然后是,大器也一下子愣住了,他的对面,怎么会是高翔宇。两个人好像是僵住了,互相看着,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你原来是个大骗子!高翔宇突然说,他突然愤怒了,是年轻人的那种愤怒,是突然而至,是从天而降,是一种受欺骗的感觉,是一刹那间对对方的深刻瞧不起,像是一件衣服,外边是漂亮的,里子却是出人意料的破烂,这时候偏偏又给人一下子给翻了过来。大器的嘴张着,手里的报纸和豆荚掉了下去。刘大器!你个骗子!高翔宇又说。大器张着嘴,人好像已经不会说话,脸色也变了,是怕人的惨白。刘大器!高翔宇又叫了一声,他甚至想把手里的尿泼到刘大器的脸上,但他来不及泼,刘大器脸色惨白地往后退了一下,又往后退了一下,一转身,人已经从他的家里,也就是公厕里跑了出去,人已经跑到雨里去,雨是“哗哗哗哗”从天而降,只是降,而不是下,雨现在是柱子,一根一根的柱子,在厕所门前躲雨的人们都看到了大器,看到他已经跑进了雨里,正在往南跑,已经跑上了那条街,街是东西街,大器是朝东,已经跑过了那个菜市场,菜市场门前是红红绿绿的蔬菜,跑过这家菜市场就是那个“马兰拉面馆”,有人在拉面馆的门前避雨,他们也看到了狂奔的大器,跑过拉面馆,前边又是一个小超市,超市的门前亦有人在避雨。大器再跑下去,前边便是个十字路口,这时候有辆货车正穿过十字路口,狂奔的大器停了一下,然后又马上狂奔了起来,就这样,大器又穿过了那家玻璃店,玻璃店忽然发出了灿烂无比的闪光,是天上打了雷,一下子把玻璃店里的所有玻璃都照得光芒闪闪。这让大器的脑子清醒了一下,也可以说是愣了一下,但他马上又狂奔了起来,他狂奔过了这个城市最东边的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就狂奔上桥了,那桥是刚刚修好的,是水泥和钢筋的优美混合物,桥上还有两排好看的玉兰灯,下边的河水早几年就干涸了,只是为了这个城市的美丽,人们在这桥下修了前所未有的橡胶大坝,还在里边蓄了水,水居然会很深,这便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景点了,人们可以在这里划划船散散步,细心的人还会在这里发现被丢弃的白花花的安全套,但这是雨天,那些颜色艳丽的塑料壳子游船已经都停泊在了河边。大器这时已经狂奔到了桥上,桥边的收费亭里有人看见了这个狂奔的青年,一路狂奔上了桥,只用手轻轻扶了一下桥栏,身子也只那么轻轻一跃,怎么说,人已经从桥上一下子跃了下去,人跃到哪里?当然是跃到了河里。在河边,躲在游乐厅里避雨的那几个人也看到了,都吃惊地张大了嘴,一个年轻人忽然从桥上跃到了河里,为什么?他为什么?出了什么事?这时雷声又响了起来,河面上灿烂了一下,是惊雷照亮了河面,给了河面前所未有的灿烂。然后又是雨,哗哗的雨,河面上又重新是白花花的。而突然,河面上,又灿烂了一下,这又是一个雷。在河边游乐厅里避雨的人,纷纷说,怎么?你们看到没有,那年轻人可能给桥上的汽车撞飞了,被从桥上撞飞到河里了。雨下得实在是太大了,桥下的人根本看不到桥上,他们当然更看不到大器是一路狂奔而来,一路狂奔而来,扶了一下桥栏,把身子再一跃,没有什么更多的细节,简直是简洁得很,就那么,一下子跃人了水中。
雨停了,有一道彩虹,真是美丽,就挂在天边,雷声也去了天边,隐隐的。
[作者简介]王祥夫,男,辽宁抚顺人,1958年生。1984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蝴蝶》、《种子》、《生活年代》、《百姓歌谣》,中短篇小说集《永不回归的姑母》、《谁再来撞我一下》、《城南诗篇》、散文集《杂七杂八》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现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