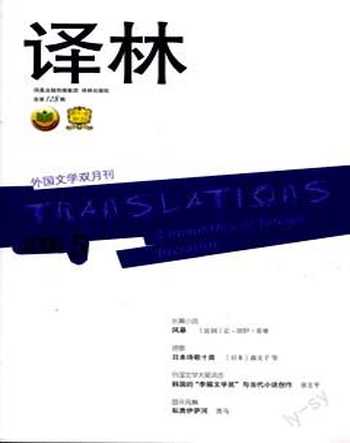吸毒的少年
阿古斯·法哈里·侯赛因
李能安/译
1 上坟
不少人为我和人类学家拉德玛纳博士结婚感到惋惜。也有好多饶舌的人说我迷上了拉德玛纳的财产。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拉德玛纳不是商人,他是地地道道的学者。他不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一点都不是,他的生活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也有人说拉德玛纳年纪大了。是的,他比我大八岁,但他还不算老。我今年刚满二十三岁,因此他也不过是三十一岁。也许有为数不少的人妒忌他的智慧,在他这样的年纪,学术上就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还有的人鄙视我,因为拉德玛纳是个鳏夫,身边带着一个快进入青春期的少年。总之,很多人为我感到┮藕丁*
但我对这些舆论不予理睬。我活在世上不是为了听他们摆布,我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拉德玛纳具备的优点比我向往的任何男人还要多。他很成熟,能虚心听取我的意见,而且他长得很帅。在他的庇护下我觉得很安全。
我弟弟顺路带我去拉德玛纳在古达帕鲁的家里时,我和他初次认识。当时我弟弟是他的学生,正在准备学士论文提纲。进到他家的第一印象是幽静。在他客厅里的墙上悬挂着几个裸体人样的画像,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类人猿”,几万年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似人似猿的家伙。
拉德玛纳和我弟弟握手,弟弟把我介绍给他,我们也握了握手。他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但很快就围绕我弟弟准备的提纲陷入热烈的讨论。他在谈话的间隙有几次以同样不可捉摸的眼光看着我。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过去了。
此后弟弟经常向我谈起他那位导师的身世,关于一年前他妻子的去世,还有其他有关他的事情。我也开始打听他的情况,阅读他的著作以及他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对这些学术问题我以往是不感兴趣的,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
然后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后来在我弟弟的毕业典礼上我又和他见面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在场,也许是他的大学派他来参加典礼的吧。他的一举一动和在家里时有点不一样,显得威严、谨慎。邦邦,我的弟弟,高兴地迎接他的导师。当他看到我时,他的表情在一瞬间有点异样,但马上又恢复常态。弟弟把他介绍给我们的父母,他们很快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
在接受拉德玛纳之前我反复考虑了很长时间。结婚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必须考虑成熟,必须权衡利弊,必须要有充分准备。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很理解我,不催我,也不问我什么时候能给他肯定的答复。
有一天他来我家,邀我陪他一起给他妻子扫墓。坦白地说我很不情愿。他向我解释说,“你应当了解我的过去,因为一个人不能轻易地和过去一刀两断。”
就这样,那天下午我们去了他妻子在郊外阐提地区的墓地。一进墓地大门,他放开了牵着我的手,我们各走各的路,东躲西闪地避开墓碑。他在东端的一座坟墓前停下,指着面前的墓碑对我说,“就在这里。”说罢,他马上蹲下。
我看了墓碑上的字,上面刻着玛尔娃蒂·拉德玛纳的名字,还有去世的日期。我一声不响地蹲在拉德玛纳的身旁。
她一年前埋葬在这里,一位贤惠、美丽、会做一手好菜的妻子,我很爱她。他说。
听到他对前妻的赞扬,我轻轻地叹息着。是的,我有点妒忌。
她是得了什么病死的?我问道。
心脏病。他简短地回答说。
我不再提问了。我见拉德玛纳低着头,口中含糊不清地在念祷文。我环顾四周,万籁俱静,除了我们俩,周围没有一个上坟的人。人就是这个命,死了,埋在土里,然后被遗忘。
我向拉德玛纳的方向瞟了一眼。看来他做完了祷告,但还低着头,手支在墓碑边上。我看看手表,太阳已经西斜,在天边洒下一片带着倦意的红光。
看到拉德玛纳还在陷入沉思,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天不早了。
“是的,”他小声回答说,一边缓缓地站起身来。他打开从家里带来的花篮,慢慢地把花瓣撒在墓前。我看到他的眼光变得毫无生气。花瓣快撒到一半时,我从他手里接过篮子,替他完成了剩下的那一半。
谢谢你,他轻声地说。
天快黑了,我说。
他点点头,怀着沉重的心情慢慢地站起身来。黄昏的阳光越来越暗淡,原来因花丛点缀而显得有些生气的墓地,如今变得令人毛骨悚然。这种气氛似乎提醒在场的人,这里就是你们将来的归宿。寂寞和阴暗。
在回家的路上,拉德玛纳一边驾驶车子,一边继续谈起在墓地里没有讲完的故事。
我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她的,她也在那里学习,但不是同一个专业。毕业后我们就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几年后我获得奖学金到荷兰完成博士学位。几年过去了,孩子慢慢长大,但她忙于她爸爸公司的业务,而我也忙于教学、参加学术研讨会、写论文。那孩子缺乏父母的关爱。
“她患心脏病好久了吗?”我问道。
“不,是突然的。”
我没打断他的话,等着他继续讲他的故事。他沉默了好长时间,眼睛直视前方那开始模糊不清的街道。
朗肯喜欢你,他突然说道。
我猛吃一惊,原以为他要继续讲他已故妻子的事,怎么话题突然转到他儿子身上呢?
那就好,我微笑着回答说。
那孩子由保姆带大。我们对他关心不够,那也是我的错。但玛尔娃蒂不该那┭……我的意思是说,她不该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公司的业务上。
“究竟怎么回事?”
“得知儿子吸毒后,她突发严重的心┰嗖!豹
“呵!”我发出短促的惊讶声。原来是这样。那孩子看起来还是好的,我说。
“表面上是好的,其实他的身心已被毒品侵蚀掉了。到现在还是这样。”
“哦。”我又叹息着。
“在接受我的求婚之前,你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我不愿看到你将来后悔,然后对孩子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在他眼里已经失去了威信。我希望你能成为他的好母亲,能帮助他摆脱毒品的阴影,恢复他正视生活和面对未来的信心。”
我沉默着掂量他的话。看来他很爱他的儿子,并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深感遗憾,似乎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
“你能做到吗?”他问道。
“让我试试。”我回答说。
“你不用现在就回答,好好想想吧。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的确,这不是简单的事,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在这个国家,后母的形象已经坏到无法改善的程度。后母已经成了残忍虐待非亲生孩子的女性的象征。而不负责任的艺术家和那些靠编故事吃饭的人,胡编乱造后母如何如何丑恶的故事,更糟蹋了后母的形象。在他们的虚构中,后母就像巫婆一样。对后母的这种偏见由来已久,一直流传到┫衷凇*
我肯定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包括上述偏见。我从未生过孩子,除了家庭我还有其他要追求的理想。作为一个现代妇女,我的理想和男人一样,要用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服务社会。我不甘心落在男人后面。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生孩子、做饭,而是为了尽其所能做点有益的事,可能的话,甚至改造世界。
过了几天,拉德玛纳又向我重复了那天提出的问题。我还是像那天一样回答他,但突然不自觉地转换话题问他,“我是不是该放弃我的职业?”我只不过是想试探他的态度。
“不,不用!”他立马回答说。“没必要那样做。只是要你妥善安排你的时间。你在银行的事业还刚刚起步,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路。”
听到他的这番话,我微笑着,心里想,那就谢天谢地了。做女人真难,为了要出去工作,结婚前要征求父亲的意见,为人妻了还要征得丈夫的同意。这是必须面对的苦涩现实,即便承认它是不合理的。有啥办法呢,有同等的机会就不错了。是的,我渴望发展我在银行的事业,至少不满足于当出纳员,要比这更高。
2朗肯
朗肯今年十二岁,上初中二年级。他长得很像他去世的妈妈,尖鼻子、尖下巴。他的个子比起同年纪的男孩要高。他不爱说话,即使说起话来也很简短。长得这么可爱的孩子,怎么会吸毒呢?这似乎难以置信。当了他的母亲后,我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证实。每星期日晚上,照例会有一大帮朋友邀他出门,其中有几个年龄比他要大得多。他们去哪儿,我不知道。但第二天早上他就已经在卧室里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的。看来他身上还存有一把家里的钥匙。不能这样下去,否则我们就无法管住他了。我一定要采取措施,让他摆脱这种坏习惯。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当我锁上前门时,我故意弄断钥匙,留半截在锁孔里。
“大哥,请你过来。”我把准备上床的拉德玛纳喊来。
“怎么啦?”他沙哑着声音问道。
“你来看,我不小心把钥匙弄断了。”我回答说,把手上另一半截钥匙拿给他看。
拉德玛纳站在那里沉思了一会,眼睛在仔细查看,然后微笑着说,“我懂你的意思,明天再换吧。”
“朗肯进不了家了。”我说。
“你会等他的,不是吗?”他半问半吩咐┑厮怠*
我轻轻地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等着朗肯来敲门。直到电视节目结束了,还没见朗肯回来。我困了,打了几次哈欠。屋前街道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开始沉寂了,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听得清清楚楚。远处传来马都拉烤肉串贩子的叫卖声。当我即将昏昏入睡的时候,突然听到摩托车停在我们家门口的声音,听起来还不止一辆。没多久又听到踩油门的声音,但很快就消失了。后来从院子里传来拖沓的脚步声,我想这一定是朗肯。我打开客厅的灯,听到他试图开门的声音。他肯定打不开,因为半截钥匙还留在锁孔里。我揭开窗帘,打开窗子。
“肯,门锁坏了,打不开。你就从窗子里进来吧!”我对他说。
朗肯显得有点惊讶,但他一声不吭,跳窗进了屋里。从他的呼气中我立即闻到一股酒精味,但他并没有喝醉。
“对不起,妈,让您等了。”他淡淡地说。
“你从哪儿来?”
“朋友家里。”
我没有再问下去,虽然肚里有很多疑问,譬如,“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等等,但我没问,下次再说吧。他已经向我道歉,这就让我高兴了。我关好窗子,拉好窗帘,然后把灯┕氐簟*
第二天我把钥匙和门锁全换了。这样朗肯手上就没有前门的钥匙了。我希望他从此不会再那么晚回家,因为家里人都睡了,他会不好意思敲门。但一星期后发生的事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彻夜不归!
次日一大清早他出现了,头发散乱,衣服皱巴巴的,径直往自己房里走去。
“你昨晚睡哪儿了?”我问道,语气尽量放温和一点。
“朋友家里。”他简短地回答说。
“怎么不回家呢?”
“太晚了,我不忍心让妈妈半夜三更起来开门。”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他的房间。
“下次如果不回来睡觉,要说一声,免得家里人为你担忧。”我又说。
他不作声,轻轻地关上房门。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吃早饭的时间到了,那孩子还在房间里不出来。他睡得很熟,看来累坏了。我壮着胆子进到他的卧室。他趴在床上,一只胳臂垂在床边。我环顾四周,在床边的墙上悬挂着一张照片,是他那去世的生母玛尔娃蒂的遗像。她戴着白色金属边框的眼镜,两眼直视前方,目光锐利,显得很美。这张照片原来是挂在客厅的,我来这个家没几天,孩子就把它搬进自己的房间里。看来他很爱他的┠盖住*
我小心翼翼地摇摇他的身子,想叫醒他。没有一点反应。我再次摇他,还是没有反应。看来他整夜没有睡觉,也不知道在哪熬夜,到这个时候还睡得像死人一样。
我查看他的书包。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我发现书包里有违禁品。我赶忙把它放回原处。我想有更好的办法劝导他。
11点钟了,朗肯还没醒来。我为他准备了早点,亲自送到他的房间,放在他的书桌上。我摇摇他的脚,这次他醒了,伸伸懒腰。
“11点钟了,”我说,“这样长时间睡懒觉可不好。”
朗肯没有回答,但他很快就起身,坐在床边。他用充满疑虑的目光盯着我。我没有提起他书包里毒品的事。
“如果你不愿三更半夜叫醒妈妈,就应该早点回家。妈把前门的钥匙给你,你就不用敲门了,”我把复制的一把钥匙交给他。我想,这样比让他整夜不归要好得多。因此,前几天算是白换钥匙了。我一定要找到另外更有效的办法。
“快去洗澡吧,妈已经给你准备好早点了。”我又说。
“以前的妈妈从没有这样做过。”他说,一边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摆在他桌上的早点。
他说的“以前的妈妈”就是他的生母。我温柔地微笑着。
“我习惯自己去找东西吃。”他补充说。
“妈妈偶尔这样做总可以吧?”我仍然微笑着说,然后离开房间。
我开始在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这个孩子呢?明显的一点是,我必须给予他更多的关心,至少要让他感受到有人关心他,把他当一回事。“以前的妈妈从没有这样做过,”这是他刚才说的话,这就是说,我不应该像他以前的妈妈。
和朗肯交流的通道已经打开,问题是如何迈过去。但愿这是一个好的开端。突然他书包里的那件东西揪住了我的心。虽然我早就料到了,但心里还是乱糟糟的。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我一定要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想,先不要让拉德玛纳知道这件事。虽然按理说应该让他知道,但男人在发怒时往往容易失去理智,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朗肯终于和我混熟了,甚至在需要用钱的时候,他会主动向我要,而不再向他爸爸伸手要了。这是我和拉德玛纳事先安排好的。现在是时候了,我应该和他谈谈毒品的事。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我反复在想如何才能让他信任我。
“爸爸平时给你多少零用钱?”有一次我这样问他。
“不一定,有时每月五万盾,有时更多。”他回答说。
“你有存款吗?”
他摇摇头。
“那么多的钱你怎么花呀?”
“买衣服、看电影、吃零嘴。”
“可你的衣服也没有几件啊!”
他咧嘴笑笑。
我意识到我的提问令他不愉快,但我没有退路了。
“肯,”我压低声调说,“你能告诉妈妈每星期天晚上你到哪儿去了?”
“到朋友家里。”我早预料到他会这样回答我。
“妈的意思是说你在那儿干什么来着?另外,他们看来好像不是你的同学,对吗?”
他没有回答,把目光移到他生母的照片上,显得很不安。
“怎么啦?”我仍很温柔地问道。“朗肯决不会做坏事的,是吧?”
他沉默不语。他用犹豫的目光望着我。我抱住他的肩膀,把他拉到我的怀里。他没有拒绝,我能感觉得到他那急促的呼吸。
“你说吧,肯,”我劝导他,“要相信妈妈会帮你的。”
他从我怀里挣脱出来,眼睛发红,还噙着泪水。
“我无法摆脱他们。”他声音沙哑地说。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了?”
“我们上瘾了。”他轻声地说。
“喝烈酒吗?”
“药丸。”
“啊?”我装着惊讶的样子。
他又沉默不语,似乎在等着我的下一句话。他低着头不敢正视我的眼睛。我故意不作声,让他继续往下说。
“我想戒了。”他低声说。
“你肯定会吗?”
“会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要是这样,下次他们来,你就不要露面,让妈妈来对付他们。”
“可我害怕。”
“为什么?”
“他们威胁我。”
我不说话,长时间在沉思。
“你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弄到毒品的吗?”
朗肯摇摇头。
“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怕。他们没有理由威胁你。让你爸爸明天和警察联系,让警察跟踪他们。你愿意告诉我们,他们在什么地方吗?”
“只是大概的地点。”
“好,那就够了。明天就打电话直接和警察联系。”我高兴地说。不过,我还是不放心。朗肯的同伙对他的威胁可不只是虚张声势。
好在警察迅速采取行动,毒品犯罪团伙的老巢连同他们的赃物一下被捣毁了。从报纸上我了解到警察正在追查毒品的来源以及毒贩们获得毒品的途径。谢天谢地!
读了报上的新闻,朗肯很害怕。无论如何他和这起案件有牵连,尽管警察在搜捕时他并不在场。我尽力安慰他说,向警察举报这一行动就足以使他从该案件中解脱出来,至少可以减轻他的罪责。
“重要的是你有了这个决心。万一受到牵连,你也要勇敢地去面对。虽然还小,你也是个男子汉,不能软弱,”我鼓励他说。
朗肯点点头,两眼炯炯有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那种眼神,显得多美、多帅。希望将来我自己的孩子也能像他那样英俊。朗肯确实走错了路,但这不是他的过错。他太年轻了,无法抗拒周围环境的诱惑,而且看来他没有得到过家长——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住—真正的关怀,他们太迷恋于各自的事业。现在朗肯身上仅存的品质是对自己做过的事勇于承担责任。如果他得到应有的爱护,他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好样的男子汉。我所希望拥有的儿子,正是这样的孩子。
3 威胁
对同伙们的威胁,朗肯的惧怕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那些人已经蹲拘留所了,而警察还忙于搜集更有力的证据。其实,真正可怕的事发生在一个星期以后,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朗肯那已被毒品蚕食的身体无法忍受戒毒的折磨,像被寒冷侵袭一样不住地颤抖,嘴唇发紫,脸色苍白,浑身冒虚汗。他挥动着双臂,好像着了魔似的。他房间里的东西都被他踢得到处都是。我抓瞎了,拉德玛纳又不在家,该咋办呢?
我按住朗肯的肩膀,他身体的抖动传到了我的手上。突然他张口死命地咬住自己的手臂,咬到渗出了血,然后用力去吮吸。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我下意识地用力往他脸上掴了一巴掌。
“不要那样做了!”我喊道。
他不作声,瘫在地板上,脸上充满恐惧。我冲出门外,叫了一辆三轮车。我领着车夫进入朗肯房间,让他帮着把朗肯扶到车上。离家前我留了一张条子给拉德玛纳,要他回来后尽快赶到医院。
到了医院大门,朗肯已不省人事。医务人员马上把他用手推病床推到急诊室准备输氧。我付了车钱,到挂号室为朗肯挂号。一切必要的手续都办好了,我就直奔诊室。我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医生,把朗肯手臂上的咬伤给他看。医生点点头,然后给朗肯打针。
“他过一会就会苏醒过来。我给他服了药,以增强体内的抵抗能力。不能突然戒毒,否则会造成严重后果。”
我点点头,虽然我不懂他话的含义。
“最好让他住院。”
我又点点头。
朗肯被转移到二等病房,这里的费用不算太贵,但也不便宜。在照料另一个病人之前,医生还抽空和我交谈了一会。
“他毒瘾大吗?”我问道。
“是的。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他反问道。
“我是他的后母。在这之前,他早就吸毒了。”我回答说。
“他生母呢?”
“去世了。”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沉默片刻,然后又说,“好吧,就这样。有一点我还要说的是,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家长的关心和爱护,没有这些,我们对他的治疗将无济于事。”
我点点头,向医生告辞,径直走进朗肯的病房。他已经醒过来了,嘴唇也红润了,脸上也恢复了生气。输氧管已从他鼻子里拔出。朗肯不敢正眼看我。我刚才的那记耳光,他一定还铭记在心。
“原谅妈妈,好吗?”我轻声地说。
他转过脸望着我,然后点点头。
“朗肯不想活了,妈妈,”他的声音很┪⑷酢*
“嘘,不要那么说。要相信自己,你肯定会把毒品戒掉的。刚才医生说了,你一定要努一把力。”
“如果朗肯死了……”
“嘘!”我马上打断他的话,“不要胡说,你会好的。”
他点点头,脸上露出异样的微笑,使我感到纳闷。
“你怎么啦?”我问道。
“朗肯很不好意思,”他回答说。
“为什么?”我又问。
“朗肯很不好意思,”他又重复着说,然后把脸转过去,避开我的目光。我也不再追问。
他长时间地避免看我,我也不打扰他。也许他觉得给我添了麻烦,很过意不去;或者认识到自己确实做错了事。唉,但愿还来得及挽救他!
“妈妈要走了,”我说。
朗肯转过身来。
“你要听医生和护士的话。妈妈明天再来看你。你还需要什么吗?”
“爸爸……”他说。
我轻轻地点头。
回到家里我发现拉德玛纳还没回来。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屋,因为留给拉德玛纳的字条算是白写了。
晚上十点拉德玛纳才回到家。他面容憔悴,显得极度劳累。我慌慌张张地迎接他,为他准备干净的衣服和洗澡的热水。他把一包厚厚的信封交给我,那是他的工资。我没打开就把信封塞进柜子里。我知道,拉德玛纳向来是分文不少地把工资全交给我,而用他自己挣的稿费作零用钱花。不久从卫生间传来洗澡的哗哗声。我调了两杯姜咖啡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他洗完澡。
拉德玛纳从卫生间出来,身上裹着浴巾,径直走进卧室穿好衣服,然后把浴巾放回卫生间。他走过来坐在我身旁,慢慢地伸过手来搭在我肩上,我轻轻地摇晃着身子。
“喝咖啡吧,大哥,”我一边说一边推开他的手臂,伸手拿起桌上的托盘,放在垫上,又坐回他的身旁。他打开杯盖,慢条斯理地吮吸着热咖啡,然后又把杯子放回原处。他的手又搭在我的肩上。
“朗肯住院了,”我轻声说。
拉德玛纳松开了抱着我的手,没有立即说话。
“上瘾了,”我又说。
他只点点头,但脸色变得很难看。
“我早就料到了,总有一天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他的声音在颤抖。
“但医生为他治疗了,他很快就会好的,”我试图安慰他。
他没回答,又端起杯子把咖啡一口喝光
“我很累,”他轻轻地说,一边站起身来,走进卧室。我关掉电视机,跟在他后面。我看见他把脸压在枕头底下。我不敢打搅他,我知道他正为儿子担忧。我默默地躺在他的身旁,很想立刻入睡。
不知睡了多久,我突然被拉德玛纳的喊叫声惊醒。我立即起身,环视四周。没有一点动静。是拉德玛纳在睡梦中惊叫。我慌忙把他叫醒。
“大哥!大哥!”我死劲摇晃他的肩膀。
拉德玛纳被惊醒了,坐将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不!不!”他叫起来,但声音不大,和刚才睡觉时喊出的梦话一样。
“大哥,醒醒!”我又摇晃着他的双肩。
他再次茫然地看着我,然后眼光慢慢地变得毫无生气。
他轻声地“哦”了一声,便低头不语。冷汗象露珠一样布满他的额头。虽然知道他一定是在做噩梦,我还是关心地问他,“你怎么啦?”
他没有回答。我很怜悯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恐惧和软弱。我抱住他的头,但他不让,把我的手推开。他的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珠子。
“怎么啦?”我又问道。
这次他声音颤抖地回答说,“我做了个梦,梦见朗肯的妈妈,她要掐死我。”
我突然感到毛骨悚然。乱七八糟的梦!我抱住拉德玛纳的肩膀,两人同时倒在床上。整个晚上我没有松开抱着他的手。我知道恐惧和不安一直在困扰着他。
第二天一大早电话铃响了。拉德玛纳正在洗澡,我赶忙拿起电话。
“请稍等一会,拉德玛纳正在洗澡,”在这种场合我习惯性地这样回答对方。电话总是打给他的,有时是办公室打来的,有时是他的学生或学术委员会的人打来的。
“对不起,夫人,”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的声音。“这是医院打来的,我们通知您,您的儿子朗肯今天早上搬进了急诊病房护理。他又休克了。等您来医院后我们再把详细情况告诉您。”
我惊呆得说不出话来。
“喂?”又是对方传来的声音。
“是,是,”我慌慌张张地回答说。“我们马上就过去。早上好!”我放下电话,听到洗澡间传来的泼水声,拉德玛纳还没洗完澡。我赶忙在洗刷槽漱洗,然后更衣,顺便为拉德玛纳准备衣服。和往常一样,他总是只用一条毛巾裹着身子走出浴室。
“医院刚打来电话,朗肯进了急诊病房,”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拉德玛纳轻声地叹了一口气,急急忙忙穿衣服。
“我们马上去看他,”我又说。
“你不先洗澡吗?”他问道。
“不了,我洗了脸。我们这就直接去医院,路上找个馆子吃早点。”
“好吧,”他说,这时他穿好了衣服。
到了医院,看病的人还不多。我们急匆匆地沿着医院走廊奔跑。白衣天使们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有推着手推车的,有帮着医生照料病人的,各忙各的事。我们在急诊病房门前停下,一个护士挡住我们不让进。我把情况告诉她,还提到刚才我接到的电话。
“医生正在里面,”那护士说,“一会就出来,夫人先在这里等吧,”她指着门前的长凳子说。
我们正要坐下,护士提到的那位医生就从病房里走出来。我马上迎上去,医生的表情看不出和平时有什么两样。
“我孩子怎样了,医生?”我急切地问道。
“已苏醒过来了。他突发心脏病,我们正在对他进行观察,”他回答说。
我松了一口气,但又放不下心。医生刚才说什么来着?突发心脏病?
“可以进去看看他吗?”拉德玛纳迫不及待地问道。
“请吧!”医生回答说。
一位护士帮我们穿上消毒衣,这是进入这间病房的规矩。朗肯脸色苍白,他没穿衣服,被单盖到肩上。几条电缆把他的身子和一台仪器连接起来,看来是心脏监测器。我深深地叹口气。那孩子的眼睛长久地盯着我,然后又转向他爸爸。我们长时间不说话,只是互相对望。
“昨天晚上妈妈来了,”朗肯突然说话了,声音非常奇特。
我惊讶地睁大眼睛。他说的“妈妈”就是他那去世的母亲。我看到拉德玛纳眨巴着眼睛,嘴唇在发颤,像是要哭的样子。对朗肯的话我们无法作出任何反应,我们也无法多说话,因为没多久护士提醒我们要马上离开病房,让病人好好休息。拉德玛纳抚摩着朗肯的头,然后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朗肯的嘴唇动了几下,好像在重复刚才爸爸的耳语。过后我亲了朗肯的面颊。看来他很想留住┪颐恰*
“妈妈,您太好了,”他对我说。
我用微笑鼓励他增强自信心,然后和拉德玛纳一起走出病房。
看来那是我们和朗肯的最后一次会面。11点钟电话铃声又响了,医院通知说朗肯离开了人间。我想起拉德玛纳昨晚的梦。是的,我没能教育好和保护好朗肯。我并不认识玛尔娃蒂,孩子的生母,但我深感对不起她。当我面对朗肯房间里玛尔娃蒂的遗像时,我仿佛看到她用责备和遗憾的目光盯着我。我低着头,避开她的目光,感到无地┳匀荨*
4 拉德玛纳
朗肯死后,拉德玛纳整天失魂落魄似的。他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发愣,屏幕上一片空白。他似乎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我能理解他,虽然我感到嫉妒。那孩子是他和已故前妻玛尔娃蒂情感联系的唯一纽带。我还记得最初他嘱咐我要引导和培养他的孩子。“你能做到吗?”当时他这样问我。我回答说,“能!”可现在孩子死了。
有好几天我不敢打搅拉德玛纳。就像昨天和前天,讲课回来后他径直走进他的工作室,打开电脑,呆呆地坐在电脑前。我可怜他那付模样,但有时不理解,一个人类学家竟如此看待和思考死亡。有时我倒觉得我比他还更理智一些。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跟他一起吃饭了。他要等到深更半夜才走到饭桌前,不用说,饭菜都凉了。这时候我就设法安慰他,重复着祖母常教导过我的关于死亡、祈祷和宽恕┑幕啊*
“对不起,”我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挽救孩子。”
“那不是你的过错,”他立刻打断我的话。
我沉默了片刻,把咖啡杯从桌上端起递给他,他用手轻轻推开。我把杯子放回原处。看来他想说些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有什么事吗?”我问道。
“我……我……”
“怎么啦?”我又问。
“我好像被玛尔娃蒂追……追……逐。”
“噢,”我低声地呻吟,把他的头抱在我怀里。他的头发被冷汗湿透,我还感觉得到他在无声地抽泣。
“好了,好了,”我安慰他。
他没有反应。
第二天拉德玛纳很晚才回家。本来这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工作忙,他早起晚归是常事。但看到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又想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开始为他担忧。他默默地走进工作室,打开电脑。他不像平时那样进卫生间洗漱。我为他准备睡衣,但他不理不睬。我像往常那样为他调好姜咖啡,放在他的桌上。
“喝点咖啡吧,”我说。
他缄默不语。我站在他的椅子后面,双手抱住他的双肩,把脸紧贴在他的面颊上。这时我隐约闻到一股酒味,这下把我给激┡了。
“你刚才上哪儿去了?”我问道,几乎在大声呵斥。
他没回答。
“你就这样逃避现实吗?你儿子因吸毒过量死了,现在你,他的老子,成了酒鬼,你不害臊吗?”
我跨步站在他面前。他仍不说话,眼睛茫然地望着电脑屏幕。
“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我提高嗓门┪实馈*
他还是没回答,突然像睡着了一样从椅子上摔下来。我不知道我还说了些什么,也许在骂他吧。我竭力喊醒他,但他毫无反应。突然我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用尽全力打了他一记耳光。他仍然纹丝不动。我抽抽搭搭,筋疲力尽。他瘫在地板上,开始打起呼噜来。
我站起身来,关闭电脑,吃力地扶着他,更准确地说拖着他进入卧室。我把他的身子猛甩在床上,两眼盯着他。人是多么脆弱啊!我心里嘟哝着。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晚,这我早就料到。
“不要……不要……”
听到他的喊叫声时,我正要去上班。我冲入卧室,看见他哆哆嗦嗦地坐在卧室一角,全身汗水淋漓。我记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兴许他又在幻觉中被玛尔娃蒂追逐。怜悯之心再次油然而生。
下班回家我看见拉德玛纳仍坐在卧室里,就在早上我看到他的那个角落。我还看到床边柜子上摆着一瓶烈酒。我怒不可遏,急匆匆地奔向车房,在汽车坐垫上又发现没打开过的几瓶烈酒。我半跑着把那几瓶酒抱进卧室,甩到床上。
“拿去,是你的,”我说。
他看着我不说话。
“喝吧,喝个够!喝醉了你儿子肯定会复活的。喝!”
我把几瓶酒的瓶盖全打开,把酒瓶递给他。他像是要笑的样子,但笑不出来,还是沉默不语。我把瓶子逐个丢到窗子外面,他仍然没有反应。瓶子在窗外打碎的声音,声声砸在我的心上。
拉德玛纳挪动身子坐在床边,久久地把脸埋在我的膝上。他终于抬起头来望着我。
“原谅我吧,”他说。
我点点头。
“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我说,“其实这些事都可以用我们的理智去处理。”
“是的,”他回答说。“对不起,”他又说。
“没关系,”我安慰他说,把身子挪近他。“我理解你的感情,但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
他不说话了,猛然从座位上摔下来。我以为他又像昨晚那样睡着了,但见他浑身┓⒍丁*
“我怕……”他说,声音很微弱。
我把他抱紧,感觉到他的身子在发烧。我让他躺在床上,他还在喃喃地说:“我┡隆…我怕……”我打电话给住在隔壁的一位医生,请他过来帮忙看看拉德玛纳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我用冷敷布敷在拉德玛纳额头上。
“他只是累了,”医生说,并为拉德玛纳开了药方。
“和我们孩子的死亡有关系吗?”
“那是正常的。这服药可以让他得到充分的休息。”
也许拉德玛纳所需要的正是休息。他把心思过于集中在儿子身上,无法解脱。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从酒精那里寻找解脱。说不定朗肯身上早就从他爸爸那里继承了吸毒和喝酒的遗传基因?但愿不是如此。
医生走后我就立即出去买药,并喂拉德玛纳服药。同时还继续为他冷敷直到退烧。
几天之后拉德玛纳的身子稍有好转。他提出要为玛尔娃蒂扫墓,顺便整修朗肯的坟墓。我只是点点头。他要求我待在家里。他一走,我就走进朗肯的房间,一眼看见玛尔娃蒂的相片。我仔细地观察着那张遗像。那位戴眼镜的美人看来样子很凶,眼光直视我的眼睛。我想转身走出去,但动弹不得。
“我让你失望了,”我轻声地说。
我似乎看到她的眼光变柔和了,向我眨眨眼,还朝我微笑。我很吃惊。不!我又重新看了那张照片。不!照片还是跟原来没什么两样,没有笑容。我用手背揉揉眼睛,照片里的她又好似向我微笑,并仿佛对我说,“不是你的过错。”我感到头晕,四周都在摇晃。我气喘吁吁地走出房间,冷汗湿透了我的脊背。我目睹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是母子之间的感情交流。也许相片里的她并没有向我微笑,但我确信我刚才经历的事是实实在在的。
晚上从墓地回来,拉德玛纳好像又恢复了活力。有关被他荒废了的工作他谈了很多。然后他要我陪着他坐在电脑旁边,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和我讲话。我不知道他这时候如何能集中精力工作,我也纳闷他怎么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难道他也看到了我今天看到的情景?我不敢问他,生怕又勾起他对亡妻的回忆。
第二天下班时,他带回了一个毛料制的小洋娃娃,塞在我的怀里。
“干吗呀?”我莫名其妙地问。
“你不想怀娃娃吗?”他反问道。
我咯咯地笑。想,怎么不想呢?我在心里回答说。我立刻猜想到拉德玛纳也一定看到了我昨天目睹的情景。一根非常坚韧、牢固,而又柔软,几乎看不见的红线系着母子俩的心。我没有问过拉德玛纳是否从玛尔娃蒂的微笑中也看到了这根红线,这个问题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相信我了?”我问道。
“相信?相信什么?”
“相信我能够教育好我们将来的孩子?”
“干吗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严肃。
“我认为生孩子容易,抚养孩子却很难。当今时代不像以前那样单纯了。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的孩子应当具有应变┠芰Α!豹
“那不是我几年前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观点吗?”
“是的,我说对了吧?”
他点点头。
“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又说,“我对我在银行的事业是有抱负、有理想、有期望的。”
“是的,我知道。”
“那么你懂得我的意思了?”
“我懂,就像我那篇文章中写的那样,孩子的家庭教育应当由我们俩共同承担,是夫妻俩的责任,不能一味地甩给妻子。”
我笑了。
“你笑什么?”他问道。
“为了表达你这个意思,还有必要借助于洋娃娃吗?”
这下轮到拉德玛纳笑了,长时间的笑。
“你现在准备好了怀自己的娃娃了吗?”他问。
“如果我反过来问你,你怎么回答?”
他又笑了。
“我是认真的问你的!”我说。
“认真什么呀?”他还在笑。
“不要笑了!我严肃地问你,你又想要孩子,你准备好了吗?”
拉德玛纳的笑声戛然停止。
“你呢?”
“我问你呢,”我毫不让步。
他沉默着,看来陷入了深思。过后便轻轻地说:“我想朗肯的事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再不会让我将来的孩子也像他那样。”
“还有你自己,”我又补充了一句。
“对,特别是我自己。”
看到他那孩子气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个不停。
“可是,”他打断我的笑声说。
“可是什么?”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准备好了,”我简短地回答说。
“现在?”他咄咄逼人地问道。
“现在,”我回答说。
拉德玛纳二话没说,一下把我揽进怀里,抱入卧室,我顿时觉得自己在空中飘啊飘啊。我还看到那个小洋娃娃孤零零地躺在桌子┑紫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