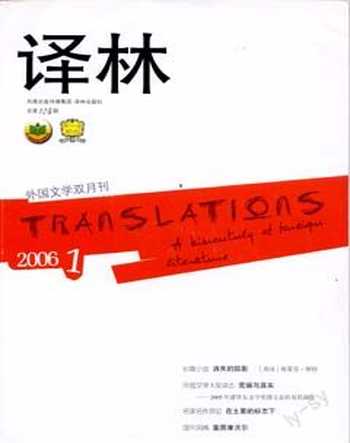马拉美
[法国]安德烈·纪德 著 徐知免 译
从十八岁起,一个年轻人就打算从事写作。在教室里听老师曾对他说,要想写得好,首先必须好好地感受,好好地思考。对此他心里完全信服。他在拉布吕耶尔拉布吕耶尔(1645—1690),法国作家。《品格论》是他的一本散文集,书中有简短格言和对当时一些人物的素描。的《品格论》中读到“写书是一种技艺”这句话,他想,这就是说,这是一个人能够而且可以学到的东西。
要做画家,就得追随著名大师在画室里学习,那么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他该走向哪里呢?
皮埃尔·路易和我,我们早年曾经是同班同学,彼此敞开心扉,畅抒情怀,几乎无话不谈。如果不说是兴趣完全相同吧,至少我俩都一样地热爱诗歌。路易比我能闯,也更大胆,而我总是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跑。
他带我去了马拉美家。
每个礼拜二晚上,马拉美总在他罗马街的寓所接待宾客。关于这些聚会的情况,人们常常谈起;若不是为了记述这位诗人的风采,阐明他的教导的某些特色,我真不想在这里对你们再次重提。他的教导,既有异于当时的一般情况,也与今天一切人们所见、所说和所做的完全不同;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其特色愈加鲜明,愈加卓越。
马拉美的内心和外表都很淳朴。他在贡多塞中学担任英语教师的工资不容许他有任何奢侈,然而他家里所有的东西无不呈现出一种优雅的趣味。他接待我们的小小餐室只容纳得下八个人,顶多也就是十个。大家环桌而坐,在平时摆饭菜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盛烟草的大罐子。大师本人站着,背靠一座棕色的陶瓷火炉。马拉美夫人早已悄悄退去。敲十点钟的时候,他女儿日内薇埃芙,面带微笑,款款地托着掺糖水的烈酒走了进来。有时,客人不多,她会停留一会儿,但很稳重,从来不加入到谈话中来。几乎常常是马拉美一个人在说话。后来他写的那本《拉杂随谈》中,有些就是他当时谈话的如实反映。我记得他说话的声调,他的微笑,那不是发自唇边,而是从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一种谨慎的、隐秘的、怯生生的笑意;在说话的同时,他常常伸出食指轻轻一掠,以表示探询和期待……啊!在罗马街的这所斗室中,我们远远离开了纷繁城市的喧嚣,离开了那么多的政治谣传、阴谋和诡计。大家跟随着马拉美进入了一种超然的境界,在这里,金钱、荣誉、掌声均已消逝,没有什么比他的那份光辉更不引人注目、更隐秘的了。今天,有教养的人都知道——
而在当时只有我们很少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是马拉美把我们的诗歌引向一个更高阶段:音韵铿锵,富于形式和内在的美,诗,显现出它从未有过的神奇魅力——我想,在艺术上,完美的东西不复旧,主要是永远向前,别出心裁。
马拉美具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在他身上闪闪发光的,正是他的圣洁。在这一方面,他完全不属于世俗,他这个人仿佛在从事某种天赋的圣职。他的言谈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他的风范激动了我们的心灵——而他,却显得十分平常,一点大师的架子都没有。可以说,对于我们,他总是以德行教导我们,而身教更多于言教。我看,确确实实,他是一位圣者。我就是这样看他。用一句简单的赞词来赞美他,我想应当强调的是他的某些品质,表面上看似乎非关文学,而实质上却是文学之所依存,却正是我们的文化所依存的东西。什么是这种德行的要素、组成成分呢?……这就是对绝对真理的信仰和信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发生任何事情,无论在马拉美周围发生什么“意外”都不动摇,怀着对真理的无限挚爱,在真理面前,一切都退避、消逝、变得无关紧要了。
不过,我看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这种对现实的轻蔑态度将会走向何方:这必然引导人们离开生活。而诗人一旦脱离现实,就有使文学堕入抽象和冷漠区域的危险。这种对客观世界的忽略,请允许我用一件轶事来加以说明,这样也许才不致因为我老是在谈论马拉美的师表风范,而使我的讲话过分严肃。
当年由于对自然主义很反感,而且也想给象征主义加上一篇小说创作(直到那时,象征主义只有诗作,而小说独缺),我写了《于里安游记》,并抽出其中第三和最后一部分另印单行本,以书名《斯匹兹堡游记》出版。我送了一本给马拉美,他接受时乍一看书名,不禁眉头微皱,他大概把这本小说当作一部真实的旅行记了。几天后,他又碰到我,他说:“啊!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还担心你真去过那里呢!”他的那份微笑简直美极了。
在这以后不久,我认为在文学和客观世界之间应该建立起直接而感性的联系。这很重要,就像我在《地上的粮食》的序言中所写的:“要让她赤脚踩在地上。”于是,我离开了马拉美,不过我仍然常常记起他的教诲:无论在文学还是在生活中,憎恶那些过于随和、讨好,或一切逢迎媚俗之举;对己对人,都要怀有一份不渝的热爱,要真诚而正直;他还要求我们坚信:体现人的价值、荣誉和自尊的东西总是胜过,而且应当胜过其余一切;其余的一切只是从属品,必要时俱可抛却。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值得注意,不知道别人是否已经给以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这种永不妥协、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出间接的后果,就像在“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出卖军事情报给德国武官,遭到逮捕,判刑,终生监禁;其后经反复申诉、辩论、调查,至1906年始获昭雪。这一事件搅动了整个法国,影响到政治、文化,以至全国各个阶层。发生时,坚定的正义事业吸引了不少热情的捍卫者走到马拉美身边,如费迪南·艾罗尔德、皮埃尔·吉雅尔、贝尔纳·拉扎尔……
因此我有理由说罗马街的谈话不仅是使我们在精神上获得教益,而且也深深地陶冶了我们整个心灵。
(徐知免: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教授,邮政编码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