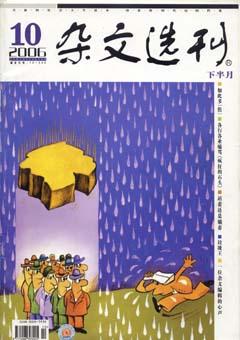垃圾王
说他垃圾王,是夸张。只是他收垃圾有很多年了,也有了些规模,也有了些产业。他在一个小学的旁边租了块空地。靠路边上砌着高高的围墙。他在围墙内搭了一个防风防雨的棚子,棚子内放着他的床。当然还有做饭的炊具。厕所在围墙外,不远,公共的,不收钱。
刚入道时,他什么垃圾都收,背着一个蛇皮袋子,到处乱走。烂布烂棉花,破铜烂铁,旧书废报纸。那时候,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城市的夹缝中盲目前行。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开了窍。
专收啤酒瓶。啤酒瓶里总有喝剩的酒。酒可以用来消毒,那酒的本身就应该没毒了。一个捡垃圾的人,本身就是与毒打交道。以毒攻毒。在这个行当干久了,自然就有了一种免疫功能。他还喜欢看书看报,这是他年轻时的一个梦。旧书废报纸,上面虽然脏一点,但上面有信息,有文化。还有征婚启事。
看废报纸上的征婚启事,是他的一大爱好。
他看了两年,从来就没发现有哪一个女人愿意找一个捡垃圾的。开口闭口就要求对方事业有成,年薪多少,还有身高,还有文化,还有素养。素养是什么东西。
他曾经养过猪。养猪怕的是瘦。瘦养,素养,怪不得这些女人嫁不出去。
他把啤酒瓶装在麻袋里,一麻袋一麻袋地堆着。靠围墙,一长溜,数数,有一百只麻袋了。啤酒瓶如果是士兵,他就是将军。谁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那啤酒瓶都想当他这样的将军了,那他干什么去呢?他在啤酒瓶面前走来走去,他模仿电视中那些领导的讲话。他伸出手去,想与啤酒瓶握手,可啤酒瓶视而不见,也有啤酒瓶流口水的,那口水有些酸臭。
他站在一堆啤酒瓶的正中间,他一字一句地喊:同志们晒黑了。他希望啤酒瓶能异口同声地回应他:领导更黑!然而,啤酒瓶依旧无动于衷。他气愤了。他从一只麻袋中抽出一只啤酒瓶,然后朝另一只啤酒瓶狠狠地砸去。两只啤酒瓶都碎了。
有点累了,他认为,不能和这些啤酒瓶一般见识,明天就去叫来一辆卡车,东风一四零的,统统把它们拖走。
拖走,一个也不剩。然后,就坐在床上,数票子。一张一张地数。从前往后数,又从后往前数。有了钱,就往乡下寄。乡下有婆娘,还有儿子,婆娘有病,儿子太小。本打算把她娘崽都接来城里住住,但又担心他们一出围墙就不认得路。
他每天都看那些废报纸,看着看着,就看出了道道。比如有好多的词语都是垃圾,而有好多的人是热爱垃圾的。就像他麻袋里的啤酒瓶一样,不断地循环,反复地使用。发酸发臭了,连洗都懒得洗。有时,某些词语不断地堆着砌着,比他的啤酒瓶堆得还高。还有好多的许诺,好多的新闻,好多的好多,都是垃圾。他找到了知音。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同路人。
围墙外的学生放学了。学生中没有他的儿子。再过两年,儿子也要上学了。放学的时候,围墙外就像一群群的麻雀,叽叽喳喳的。麻雀都飞走了。围墙外又安静了。一辆小车停在了围墙外,那是到一家小餐馆吃饭的。两个喝醉了的男人急急忙忙往厕所里跑,隔着围墙,他都闻到了酒气。
他姓甚名谁,围墙外的人谁都不知道。也没有人想着要知道。那一块空地原本是要砌房子的,却不知为何被人遗忘了。于是,街道居委会就义不容辞地管着。他每年去交一次钱,奇怪的是,他们也不问他姓甚名谁。来拖啤酒瓶子的司机,见了他就一声“喂”。他有时候气不过,半夜三更爬起来,自己喊两声自己的名字,然后自己又答应两声。然后到厕所撒一泡尿,然后再倒下去继续打鼾。
他现在应该算老板了吧,不少推三轮车的,都把啤酒瓶和旧书废报纸往他那围墙内送。他那空地是一个中转站。那些推三轮车的叫他什么呢?好像也是“喂喂喂”的。他也习惯了。他曾经对一个推三轮车的说过,他是捡垃圾的,什么名份到了他的面前,都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