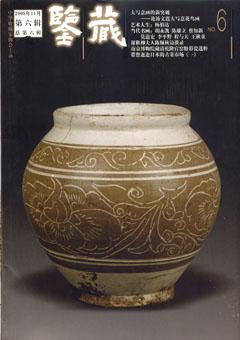与天·无极
望 野

程与天,沈阳人,满族,幼年发奋,师从皇室学校校长爱新觉罗·庆后和沈延毅,后师古文字学家于省吾,现为中国书法促进会副会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顾问、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特邀书画师、协和函授学院艺术教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海南三立画院院长、北京东方书画院副院长。
出版有《二全斋印说》、《二全斋说文解字形讹考》、《同心篇印谱》、《中国当代作家印谱》等。
20年前,我第一次见程先生与天。
和他的认识,是从一段离奇的谈话开始。我当时非常痴迷于一些清末、民国及建国初年的大学问者的掌故、佚闻。在读这些大学问者的生平故事和他们的学问成就时发现自清乾嘉以后,中国文人对古碑、拓本、版刻有难于形容的嗜好。自王懿荣、吴大、刘鹗、端方、孙诒让等诸公以降,做学问者更以对中国早期文字的理解考订为上乘。所以我也就看了一些令自己头昏脑涨的关于甲骨、钟鼎、训诂一类的图书。一翻故纸,方知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特别是文字学渊深似海。一个智者穷其一生只怕也不过北溟滴水而已。谁阅读的了解的越多,反而是一种苦闷,因为发现这些东西那个时候身边很少有人知道,更不要说交流了。直到见到他,才令我无比的雀跃欢喜。
离奇的谈话由此开始,他咏自题诗给我听,我就说自己的心得,我说了心得感受,他讲更多的问题,话随人心,逐步的就进入了他的世界——书法。他滔滔不绝,从用笔、布局、浓淡、心境性养直谈到书法的核心——文字。从六书到古籀,从金文到石鼓,从篆书到隶变,文字的形成,字形的变化,他讲的趣味以极,且信手用笔在纸上画出了一些古怪的符号,看到这些符号,我随口就一一的脱出,“水、鱼、高、眉、鼎、室、传……”接着我开口问:“这些甲骨文写进书法,会有我们常看到的真草隶篆漂亮吗?”他肯定的答到“甲骨文入书法别有一种情趣。”我接着说:“从王懿荣、铁云以后,民国间甲骨学研究以罗雪堂、王观堂、郭鼎堂、董彦堂为观,甲骨四堂贡献莫大”。他大笑道“你还知道甲骨四堂,我以为你只知道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呢!”一听此言,令我悻悻。他似乎觉察出我的不快,立刻又岔回话题,讲书法的意境和欣赏。随话语的接答,我又开始了最初的喜悦。我接着问:“习书,你以为从欧、颜、柳的正楷入手,是否为最佳?学书法是否有捷径呢?”他答道:“正常状态下练字,多认为从正楷入门为好。但我不同意,如你有心习书,我建议你直接从篆书入手,可以临写李斯的泰山刻石,从圈画中体味笔锋的变化和手腕的运动。这更有利于你以后按自己的习惯和方便书写,并且不会把字写死。这就应该是捷径!”他的观点当时听得我一惊。但我着实佩服他的理论,所以日后我的确写过好久李斯的篆书,这是后话。从书法我们又说回到诗词,他仍是多有妙论,我发现他非常注意古体诗的平仄韵脚。他认为写诗,五言、七言,平仄韵脚为最重要。而我则抬扛,新时代,写诗就应该有新气象,平仄韵脚是傻框框,只要诗的意境好,立意好,朗朗上口,没有平仄韵脚,一样是好诗。一番对答,诡争,我发现也气得他肚鼓。这使我更多了几分高兴。在言诗词时,又聊起了闲章词句,书法用印,这我才发现他对篆刻的理论,更是别有洞天,从战国私印到秦玺,从汉印到元押,他同样讲得有趣。且观点多不同于旧说。我就问他:“书法,都说是童子工,越小临习越好。那篆刻是否也是童子工,越小学越好呢?”他大声回答:“昏话,笨蛋!字是越小练越好。篆刻是越小练,越糟!”我一愣,忙问“为何?”他续答到:“小孩子,手骨是软的,一直在发育成长中。如果用印床,则手没有握感和触感,对石头的体会就完全没有了,刻多少年也是笨的刻字工。如果用手握石,则有两个问题;一、人小刀重,容易冲刀破虎口。二、手骨长期握石,姿势的细微不当,都容易日后形成畸形。”说完这些,他伸出左手,我看清他左手虎口上多有白痕。接言“当年我自学篆刻,没人在最初提醒,所以留下很多痛楚。今天如果是有心于篆刻的人,且不可小小就抄操刀。我以为小时候可以多学习认识篆法字形,多读印谱古玺,在心中冥想。等15岁以后手骨基本定型,且有一定的握力以后,再开始动刀,这会事半功倍,这比从小拿刀的童子工更强百倍。篆刻的握感走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学会用印床,则许多味道都没有了。”在日后我发现,他奏刀刊石,反文写形快而准,且从来都是用手握石,刀飞利落。这些功夫的获得,其中的辛苦,常人可能是根本无法体会的。

自从和他相识以后,我有了许多的机会看他运笔、刊石。同时也就有了更多次的谈话聊天。在后来的交流中,我开始了解他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这么多年来每每想起都还会令我激动不已。
与天,1950年生人,父亲曾就读于旧中国东北的讲武堂,在东北军中做过军官。他十岁时拜父亲的朋友,曾任过伪满皇家学校校长的老学究爱新觉罗庆后为师,研习书法。数年后他又拜入沈阳市文史馆馆长沈延毅先生门下。得庆后先生、延毅先生垂爱,加之文革间风云动荡,二位先生得有更多的时间和心血倾注入爱徒的身上。他也尽心竭力的从两位恩师身上,学到了精纯的古文、格律、书法、训诂知识。我曾经玩笑的说过,他这时期的学习,简直就是私孰专养。此类机缘,是学人百载难求的福报,他的确福泽深厚,同时他也确实不负这份福泽。1972年,沈阳市外贸局收集字画到广交会展销。在辽宁省送去的展品中,他的一幅甲骨文书法对联首先被日本客商定购。同时日本大阪的“阁云堂”中药店还特地请他题写匾额。在那个时期,这无疑是对他书法艺术的最大认同与肯定。他还写了《二泉斋印说》、《二泉斋<说文解字>形讹考》,这些著作得到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在我后来和他的交往中,细看过他早期的许多信札和函件,那厚厚的信札中穿缀着无数光耀中国学界、艺术界的名字。鸿雁之谈,难得谋面,加之书信讨论的多为纯艺术和奥涩难解的学术议题,所以当时许多和他长有书信往来的人都以为,他是位年过古稀的耄耋遗老。名贯甲骨学界的先贤容庚先生给他的复信,落款为“弟、容庚”。这些贤哲的鸿雁,成为他更广阔的学习天地,同时也不断的开阔他的视野。

1980年仲夏,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松葱柏翠的配殿内,垂挂出一幅幅格调高雅,味韵横绝的书法、篆刻。殿内人头攒动,人们无法相信这些遒劲古朴、苍老高绝的金石书法出自一位刚及而立的青年人之手。此次“与天金石书法展”,成为那年夏天北京,乃至中国艺术界的一件盛事。当时北京的艺坛名家、学界耋宿几乎都看了这次展览,可谓反响空前。作家茅盾先生看他的作品后,带病录写了自己1943年的“题白杨图”诗以示鼓励。收藏家、书法家张伯驹先生亲观展览后题词“与天依中国书法历史之发展观摩、临写,具千锤百炼之工夫,神完貌备,可嘉也。”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先生,称其书法是“阳春白雪”。《林海雪源》的作者曲波先生,赋诗赞曰“艺功奋进数经年,华骨终现今人前。文苑奇花又一朵,走刀飞笔程与天。”另臧克家、冯牧、李苦禅、启功、楚图南、张仃、严文井、沈鹏、王森然、于安澜、陈大羽、冯建吴、顿立夫、周哲文、李长路、蒋维崧等先生欣然题词祝贺。此次展览也使他步上一个新的台阶。自此以后他在学山书海中更加勤勉,他的书法和篆刻日有精进。人们喜爱他的书法,更喜爱他的篆刻,除了各国政要请其制印外,更多的同好也以用与天制印为快事。从贤朋为他的印存题签就能发现人们对他篆刻的喜爱和关注。我翻看过一本他自己非常爱惜的,充满怀念的印存,数十张题签无一相同,题签者分别是茅盾、沈延毅、张伯驹、陈书亮、于省吾、容庚、顾廷龙、张仃、李苦禅、马宗霍、俞华剑、诸乐三、柳谷子、启功、钱君、罗福颐、罗继祖、陈大羽、蒋维崧、梁燕愚、李遇春、孙其峰、霍安荣、陈公柔、林健。看着这些许多故去已经成为历史的名字,我感受到他为何那么珍爱这本印存,这印存中的名字,已经成了他对岁月和友谊最美好的回忆。此时我可以体会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书者得到如此多前辈贤哲垂爱的欣喜。这也让我想起近日读到的黄永玉先生的一句感叹“年轻人时常是错过老人的。”一个人有福分不错过老人,那他必定可以获得更多的人生乐趣和了解。与天有福,从其总角之年起就一直没有错过老人,直至今天他也已年过半百,我深信这份福运定会伴其一生。

社会越来越发达了,信息越来越通畅了,加之今天的中国已经步入全面的商品经济社会。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经济难分难解,同时随物质生活的提高,以艺术为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各式画家、书家、艺术家层出不穷,各类艺术品的价格也都以万、十万计。但有一点我总是难于释怀,以前的书家、画家和人交流,多以情谊趣味为多,而今天的则多以商业性、润格为上。有时想来我真的非常感慨和与天先生的这么多年的情谊。他的作品经数十年磨炼熔冶,无论书法、篆刻俱臻妙地,从1983年起就已经广被国际艺术品投资人推崇。香港招商局以巨金邀请其摹古篆刻创局第一枚关防,轰动香江。中国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先生亲笔题赠“万缗一印,点石成金”。而他的书法作品也早已经是一字千金了。就在与天先生的艺术作品贵比金玉之时,我仍能轻松得到他的厚赠。一个人的朋友多那人情债也就多,而我又恰恰是一个多友的人,加上我的许多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我自然成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希望透过我而能得到先生作品,那些得到作品的朋友将这些厚赠珍视有佳。与天先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为朋友的拜求,我无疑给与天先生无形中添了许多麻烦。在这里我真心的说声“谢谢”!谢谢那份情谊,谢谢那份坦荡!
有情谊的人从来不会因为小节而改变性情,与天先生长讲“此生受业,得延毅先生恩惠良多”。而在和我交流时他长称沈延毅先生为“老沈头”,最初我还觉得他如此叫法令人不舒服。后来看到他两首悼师诗,才知他的真性情。他那声“老沈头”,是心中无比亲近的呼唤!仅录与天先生两诗及跋语,一并在此怀念,山海关以北的一代宗匠——沈延毅先生。
《忆恩师沈延毅先生》
梦断侯城凭枕湿,体温渐冷抚恩师。
门房秉烛才开讲,浪子趋庭又学诗。
冬侍挥毫呵冻砚,夏携课本著长衣。
当年集腋成佳构,墨宝流传岂敢私。
一代书宗述菊翁,年华九十笔尤雄。
惊闻噩耗传琼岛,忍对遗容泣海风。
壬申春惊闻公卓夫子仙逝噩耗传来,心胆俱裂,数日竟不能成诗,今强成一绝,以寄同门,程与天泣记。
一个真性情的人,他的艺术作品中一定会保留这份性情。因而我有时想与其说我和许多人喜爱与天先生的艺术,倒不如讲,我和这些人更喜欢他的性情!这真应了和他名字相同的汉瓦吉文——与天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