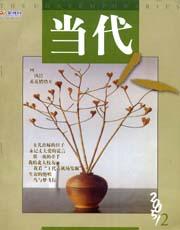谁不是陌生人?
范家塘
诗人率德最为人所知的诗歌《在地铁站》很短,拢共就两句:“这些面孔在人群中幽灵般 地显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朵朵花瓣。”这首诗的灵感据称来源于一种视觉震撼,当庞德偶 行至地铁时,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连续瞥见了几个美丽的面孔,他花了一天时间才算打到了 跟他的视觉感受相匹配的意象。从此以后,一旦提到庞德或者意象派,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 是这两句诗。
批评家们可能会醉心于这首诗的种种妙处,诸如意象的色彩对比,内涵的含蓄凝练,形象 重叠的蒙太奇效果之类,但是他们很少会去问一下,庞德何以会碰巧看到了那么多美丽的面 孔,以至于让他联想起朵朵花瓣,而我们却看不到、联想不起来?我曾经傻乎乎地键入“地 铁”的英文字到google去找图片,我能够找到的那些攒劝的脑袋,无非是一个个神色呆滞、 疲惫不堪、行色匆匆、灰头土脸,简而言之毫不美感的脸孔。这和我在上海地铁站的视觉经 验是一致的。
出入地铁的人群,不知从何而来,不知走向何处,他们近在咫尺,但是我们却视而不见; 我们的感觉器官可能抓住了他们的某些音容笑貌,但是我们的心神却飘逸在无何有之乡;他 们是一个个实体性生命,但是对我们而言他们却是一丛抽象物,一批漂浮的不负载任何所指 的能指。作为乘客,作为临时邂逅而得以呈现的在场,他们的社会学形象对于社会学家并不 陌生,只是这一意象并不具有庞德笔下的那种美学效果,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那样:“像穷 人以及各种‘内部的敌人一样,陌生人是群体内部的一个元素。作为成熟的成员,他的位 置既在群体之外,又在群体之中。”齐美尔的叙述让我们想到了波德莱尔钟爱的那些波西米 亚流浪汉,那些斜眼看人冒着酒敢的文人,他们喜欢在人群之中陶醉于形单影只的孤独感; 但是齐美尔的继承者们对陌生人的分类却显得更加没有诗意。齐美尔对陌生人公正、客观、 自由等可能特性的描述,变成了渴望被某个群体接纳但又遭到排斥的边缘人(帕克),变成了 闯入到某个社区构成其安全威胁的形迹可疑的移居者(雷文),变成了寄人篱下遭人厌烦的他 才(舒尔茨),变成了移民,贱民,乡下人,变成了永久性失去自己的家园又被新的社会系统 所拒斥的人,变成了我们看不见或漠视的那些人,他们存在着,但是他们的存在意义被剥夺 了。
当庞德用温柔的眼光抚摸着那些地铁乘客面孔的时候,他显然把自己设想成了一个无关功 利的观看者。纯粹的美学目光过滤了那些肉身的尘垢凡俗,它凝视的其实并不是那些美丽的 花瓣外观下的实体自身,而是投射于构造这些美学形象之中的诗人自己。鲍曼曾经说,我们 每个人其实都是陌生人,但是庞德的自我美学提升使自己忘记了其自身亦为地铁乘客的身份 。庞德这一美迷个案其实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有关知识分子的隐喻。当知识分子以社会代 言人自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问一下,在什么程度上,这只是忘地了 自己陌生人身份之后的一种精神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