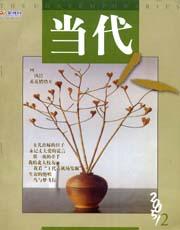秋天的飘落
朱静辉
这个秋天里我去了两次火化场,一个是送朋友,一个是老家来的堂哥,他来这个城市治病 ,就永远地留在了这个城市。
我之所以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有了说的欲望,是我在这个秋天里感到生命的无常,生死的无 界限。尽管人一生下来就逐步迈向死亡,可聪明的人是不愿想到死,他们只想到如何生活的 更美好,在其一生中如何最大的占有财富,那个美丽的花环一直在远处引诱着人们走向虚无 。
我的朋友是那么精致的一个女人,大学毕业后做广告起家,是那种吃得了辛苦又拿的起放 得下的人。她挣有上千万产业,开着“宝马”,晚礼服和宴会上永远是一袭旗袍在身的女人 。她开着车跑在每天都走的京津高速路上,这条她再熟悉不过的路,那晚她一定感到陌生, 高速路像一条黑色的带子把她带到了远方。
出事的前几天,我还见过她,那天,她穿了一件月白织锦的旗袍,一只翡翠的镯子,白色 半跟跟皮鞋,墨一样的长发在脑后挽一个圆圆的蓬松的发髻。脸有点苍白,毕竟已是快四直 的女人了,但一份成熟的优雅使她依然美丽。那天她还对我说,找个时间,我们俩去北京三 联书店,坐在二楼选个角落,要上一壶大麦茶,好好地看它半天书。我知道她是在找寻过去 的梦,找寻过去那份单纯和宁静。但这点愿望她都没有实现。
前些年,我还一直关心她的个人生活,很是给她操了一阵心,但这几年我希望她成家的念 头像风一样消失了,婚姻的列车已隆隆地开这,她莫名其妙地被遗落在站台上。虽然现在事 业有成,人生的天地宽了,生活的空间却窄了,看着那么实际的男人,我觉得能配的上她的 男人到哪里去找呢?有的男人是看上她的财,有的男人是看上她的色,有的男人财色都要, 婚姻的本质呢?这么多年在商海打拼,女友的戒备之心日甚。她逃不出女人的弱点,她曾梦 想过:有一个恩爱的丈夫,把这一切交给他打理,自己相夫教子,过一种简单的生活,纯粹 的家庭主妇的生活。说这话的时候,女友的脸部线条柔和极了,双眼漾出的温柔要把你化掉 。这对女人来说不难的生活,对她就是一种奢望。已记不清有多少次,睡眼蒙中,你被床 头的电话惊醒,那端传来女友的呼救声,我知道她又走不出去了。等你赶到时,她像只猫一 样蜷缩在那宽大的红木床上,双手冰凉。她会拿出那张身穿黑丝绒旗袍的照片,说是她死后 要把这张照片烤瓷后放在墓碑上。
女友有一句经典:“打点打点心情好重新上路。”只可惜这次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秋风把落叶一片片的摘走,抛向空中,在风中飘动的还有女友母亲的白发,刚经过了一个 夜晚,她的双眼已如枯井,单薄的身体是那样无助,仿佛一阵风就会把她吹走。
秋天是让人伤感的季节,特别是在秋天里送人到另一个世界去,就更感悲凉之雾萦身。
堂哥自到这个城市治病,就是我联系的医院,并找好的外科医生给他做的手术。只可惜胃 癌早以扩散,生命还是被死神拽走了。这是一个命运多桀的苦人,不到三十岁老婆就跟上一 个运煤的卡车司机跑了,给他留下一双小儿女,儿子还是个哑巴。为了不让他的儿女受委屈 ,他谢绝了多少媒婆,除了种一手好地,他还赶一手好毡。冬闲时,他走村串户去赶毡。愣 是把儿女养大了,女儿出嫁了,儿子还是光棍一条。他的劲一刻也没有松,入院前,还在清 凉山修复古寺,大把地吞着止痛片,挣那每天四十元的工钱。
在他生命走过的六十个春秋里,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一刻不停地旋转着,曾经充满 活力的生命,被消耗成一具空壳。如果你看到一个生命是怎样一步步飘离的,你还能对生命 无动于衷吗?那维持最低的生命体征,是那么顽强地坚持着,久久地在病房萦绕,那一刻, 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在做着死亡前的仪式。
焚烧炉在这里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投向它怀抱的人,不管他是富有的、贫穷的、高贵的、低 贱的,生命的庄严在这里得到了尊重和平衡。
堂哥的女儿执意要给他在这个城市买一块墓穴,说是他劳累了一辈子住的还是那两间上房 。
这个城市一块最好的墓地是一个文化人搞的,他原先是一位省报记者,是属于最早下海的 文化人,是那种下海后没呛水而逐步发达起来的极少数人。他是先开发房产起家,又逐步涉 猎餐饮,后来又开发了墓园,随之又把这个城市的火化场接管了过来。用他一句话说:就是 我们给活人盖完房子又给死人盖。真正做到了一条龙服务。
说实话,墓园很美,绿草如荫,花果飘香,分高、中、低档墓区,所有的墓碑都被松柏环 绕。墓区的西边是上百亩果园,北面是动物园,有孔雀和山约在高大的铁网里散步,两只肥 硕的棕熊在阳光下笨拙的挪着步子。墓园正北和东西两面是人工堆的土山,高高地俯视着这 一大片墓园。
秋天的墓园是暖色的,果树的叶子黄的耀眼红的鲜艳,连阳光都是软的甜腻。自踏入墓园 的第一步起,那低缓的哀乐就通过地下线路随我们到达墓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和我们一样 在安慰亡者的灵魂。能在这里安息,该是活着的人的一个安慰。死亡在这里被定格成一块块 墓碑,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化成一种形式。
我的脚步倘佯在碑群中,目光所到之处,有满含苍桑的老者,在活力四射的青壮年,也有 那像花一样娇嫩的笑脸。如果灵魂有知,他们是否满意这个陌生的家?
这个秋天我对落叶格外敏感,一枚不经意的飘落,也会使我的目光马上蒙上一丝忧怨,也 可能有什么正恰和我的心情,这个秋天里我的心情有点糟,所到之处看到的也是一团糟。我 为了能在这个秋天里看到纪小岚的故居、他亲手植的那棵紫藤、那有爱情记忆中的白海棠, 一大早就赶到北京,看表时光还早,正是吃早点的时候,就顺便拐进小胡同,来到一家南方 人开的小吃部,要了一屉包子,一碗小米粥吃了起来。临桌是一对母女,看来女儿已吃完, 正坐等,母亲吃的很慢,过了一会儿,女儿突然站起身走了,把还在咀嚼的母亲晾在桌边。 母亲对着那南方小老板说:我对她主这几天上火,想喝碗粥,她抬腿就走,还吃的我的退休 金。那小老板送过一碗小米粥,那母亲喝了,拄着拐棍站起来说是等明天再给拿钱下来,就 一步一颤地走了。我望着老人微弓的背影,又想起她女儿那冷漠的面孔和青春健壮的身体, 是什么让亲情如此冷漠?
我打了辆出租直奔珠市口大街,大街正拓宽,纪昀故居院里的紫藤正暴露在街上,花和叶 子上已是厚厚的尘土,面目全非的老藤独立于周围的大厦下,显得那样不堪一击。再向里走 ,正房被改造成一个大餐厅,几十张桌面上,食客如云。这里经营山西各种面食,想来是经 营者借纪昀之名,把钞票尽收囊中。
我在正房前被隔开的小天井里,找到了纪昀亲手栽的那颗海棠树,树被挤在这小天地里, 是他的主人所没有想到的。海棠树长势还算旺盛,叶子毛绿,海棠正红着半边身子,树身有 头号土碗那么粗,只是树四周的墙上挂着好几只空调的室外机,炒菜的油烟也向这方小天地 飘散,就这么长年累月的熏陶,也不知这海棠树能抵御多少载风霜雨雪?
古都博大、深厚、具有帝王之尊,它宽厚似海,可容纳百川。可它又有一种自傲时时在心 底沉渣泛起,藐视别的存在。
这个季节里,是古都最美的时候,连街上的落叶都别样丰富,可我分明感到了生命中的另 一种飘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