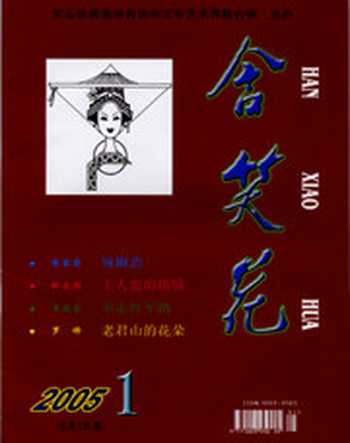故里旧居
马佳贵
池鱼思故渊
别鸟恋旧枝
客居异乡,总会使人生发“故人怀土,小草恋山”之幽情。
岁月匆匆,流光如箭。离开故乡,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悠悠往事,历历过物,别之愈深,思之愈切。琐忆往事,谈及旧物,教我魂牵故里,心念旧居。
我的故乡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村子背倚青山,面临河流,四围田畴环抱,草木相扶,远远望去,酷似一叶泊港的扁舟。村里的房舍一概坐南朝北,惟独我的旧居坐西而向东。若是把家乡绘制成一幅彩色的画卷,那么,画中点厾着粉墨色的那座院落即是我和祖上八代人居住过的地方。
我的旧居,粉墙黛瓦,一共三间房子。一间是大堂屋,另两间是耳房。大堂屋的对面矗立着一道高高的照壁,与三间房屋恰好合成一个大庭院。左右两间耳房的侧面各设有一道廊门。房屋四周,一道长长的围墙在两间耳房后面又圈出了两个小庭院,南北两面的围墙分别开着一小一大的院门,小庭院里有几棵祖上种植的大梨树。无论从南面或是北面进入大院内,都须跨过两道门槛。因此,颇有一番“庭院深深”的景致。
据说,昔时年辰荒乱,盗匪横行,这所宅院曾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式防御过盗贼的袭击。如今这座陪护着我和祖上几代人历经沧桑、忧乐相共的庭院虽已木腐墙破,斑驳零落,但其神采犹在,风韵尚存。静观她那岑寂苍凉、雄浑高古的气貌,仿佛就像欣赏到一幅古雅恬淡的图画,阅读着一部情深意切的史诗。
小时候,听父亲讲,我的曾祖父曾一度在这所房子里引笔舒卷,悄然灯前,用心苦读。后来在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中,中了“鼎”,做了官。为了解释“鼎”的意思,父亲到房楼上拿出了一个牛皮制成的圆形盒子说:“这就是装‘鼎的盒子,‘鼎就是装在里面的那顶帽子。”父亲的解释虽然不够准确,但其中的意思我们已心领神会。父亲还讲,我的曾祖父做官以后,每三个月回来探亲一次,每次回来都有五个佩刀护卫相从(前面开道的一个,牵马的一个,左右各一个,后面还跟着一个),甚是荣光。告老还乡时,便在这所房子里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私塾。
曾祖父留下来的书籍非常多,房楼上足足地堆满了一格房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破“四旧”时,有人说,我家里藏有占卦卜筮的书籍。于是,村里的人便不问青红皂白,统统拿去焚烧,从中午到黄昏,整整地烧了一个下午。万幸的是,曾祖父的书籍还是被爷爷悄悄地藏起了三箧。至今,这些书籍尽管大多断简残篇,可是家里的人仍把它视为传家之宝,精心地珍藏着。
生活在故里的那些日子,总有着道不尽的快活与欢乐,数不清的美梦和幻想。
在那里,闲花野草,百鸟千虫,无一不是开心的引子;山头河岸,田间地角,无处不存希望的寄托。清风明月,行云流水,本无心志,却怀厚意。猪鸡鸭鹅,牛羊犬马,虽为异类,情亦犹人。蛙鸣蛐吟,鸟啼蝉唱,各抒其趣,各得其乐。风翻麦浪,雨打浮萍,物物相亲,万籁祥和。
那时候,虽说家境贫寒,我却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温馨烂漫、活泼纯真的每一天。——夜晚,一灯如穗的桌旁,有弟妹伴读的身影;清晨,那几只讨人喜欢的喜鹊总会按时飞到家里的屋脊上,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催唤我们起床;白天,呼朋引伴,抓田鸡,捉黄鳝,采野果,撵蜂子……
暮春三月,碧草葳蕤,野花遍地。房后山谷里回荡的是我们骑在牛背上唱出的悠扬的牧歌。
梅雨时节,禾木青青,细雨潆潆。村前河畔上闪现的是我们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来回垂钓的瘦小的身影。
童年的稚趣,少小的欢悦,恍若一团团斑斓的影子、一帘帘醉魂的幽梦,深深地编织进我的记忆里。而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是如影随形,与我长相左右,给我慰藉,让我舒心。
旧居在我们家人的心目中是极其神圣的。父母亲建好新居的那一年,我和弟妹从喧嚣的城里赶回去一块儿过年。父亲说:“今年的春联没有买,由你们自己来写好啦。”话音刚落,我就觉着这事儿落到了我做长子的身上。
新居的对联写好贴完后,父亲又发话:“老房子的也要写,也要贴。”母亲听了,觉着有些为难我,便解围道:“不必贴了。老房子,过后就要拆了。”父亲说:“不能拆,随其自然。”
恭敬不如从命。思索了一会儿,我便挥毫写下:
破墙陋壁通风好
高楼大厦总不如
“横批呢?”父亲追问道。我笑着写下了“随其自然”四个字。父亲高兴地说:“好,好,好!‘随其自然。”
转念之间,父亲拿起上联:“‘破墙陋壁?其实呀,就像孔老夫子说的‘君子所居,何陋之有呢?”父亲这番饶有风趣的话,一下子把全家人都给逗乐了。
山传神,水写照。故乡的山,故乡的水,依旧爽朗明丽,灵光熠熠。只要融入其间,便会使人赏心乐事,悠然自得。
花溅泪,鸟惊心。旧居的恩,故里的情,毕竟海深天阔,山高水长。即使远走天涯,仍是让人刻骨铭心,感念不已。
仰望日月,低首沉思,眉间心上豁然浮漾着故里那花开花落、草枯草又长的动人景象,以及旧居那傲然凌立、高蹈遗世的潇洒情怀。这光景,这情致,不正是曾祖父书中所载述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那种境界么?
——我独自默默地领悟着其中的情感与意蕴。
故里是一首歌,让我深情咏唱。
旧居是一盏灯,在我心中永远闪亮。
——于毛泽东旧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