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静默的叶子
林 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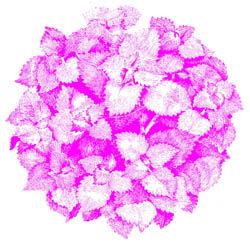
有些记忆很模糊了,有些记忆却像被风雕琢一样,所到之处,总会泛起一些涟漪,一漾一漾的,如初夏的蓓蕾绽放,每一瓣都拥挤着心房。比如年少的某个夏天,某一条街,某一个人,某一朵花……每每此时,被生活磨得起皱的心,被这样温暖的回忆浸润着,柔软无比,就像那诗句:你是我记忆的住客/你是最后一场雪。
那个夏天,我认识了一个大胡子男孩,确切地说是邻居。其实他也不是留很长的胡子,只是满腮的青碴,有一种落落的感伤,而那时又迷着三毛的书,所以也给他起了这样一个温暖的名字。
偶尔我会到他的店里喝茶,穿着自己做的黑色纯棉背心,在肩上开了两个小洞,用一根黑色的小带子系着,扎成一只黑色的蝴蝶结。我喜欢踩着单车,穿行在灿烂的阳光中,风吹来时,肩上的蝴蝶在快乐地飞舞,好像我那被阳光温暖的喜悦的心。
他会笑着招呼我,递给我一杯清茶。两人坐在白布铺的小圆桌旁,看那些茶叶在热腾腾的水里渐渐舒展,沉落。这是一个白色的世界,白的墙,白的桌,白的椅,我坐在那里,可以沉默,可以微笑,可以闭目养神,不需要任何的修饰,这让我放松和舒服。
当那些清香的茶浸润着灵魂、心以及行走的思想时,我想起了阿拉伯人喝的三道茶: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如微风。我告诉他,他笑着问:现在我们喝的是哪道茶?我笑而不答,看着他清澈透亮的眸子,不沾染一丝的尘埃。我说我们是两个相似的人,只要一言一语就能洞察彼此的心思。他答:这个世界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偶然的相似并非必然的相同,你看不见的,我看不见的,那些遮蔽和束缚我们心灵的无形的东西,正在吞噬我们纯净的世界。他说的是对的,所以至今我们仍然是两片相望的静默的叶子。
偶尔,他会来看看我。我的房间很凌乱,吉他、书、未写好的诗歌、相片、去年冬天采回来的芦苇,散落在地铺的各个角落。我们坐在地铺上,听那首忧伤的歌,歌名是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句:无话可说哦哦……无话可说哦哦……那个穿透力的声音将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串了起来。那时是盛夏,有很透亮很皎洁的月光像水一样涌进窗来。我们坐着,隔很远的距离。我给他看我写的诗,或是以前画的素描;有时他抱着那把吉他丁咚丁咚地乱弹,或给我讲宋定伯捉鬼的故事……那样的时光是缀着快乐的,似乎轻轻一摇,就会像盛夏的阳光一样,照亮了这满是尘埃的世界。
那时,一只小小的电风扇“咯吱,咯吱”地转着,清凉的风转到墙角又转回来,空气是热的,很多白蛾子扑在白炽灯上,我们就笑这种执迷不悟的飞虫。可是生命里惟有这刹那是辉煌的,又有何不肯?远处荷塘传来清脆的蛙鸣声,此起彼伏,在告诉我们,世界是存在的,只是时间飞逝,带走了很多我们无法触摸的真实的快乐!
后来,没有后来了。那年秋天他去读书了。从很远的地方给我寄来了一个木盒子,打开时仍能闻到树木的清香。盒子里有两盒诗歌录音带,是叶芝的。夜深人静的时候,盘腿而坐,听那些抒情的诗歌在优美的音乐中缓缓漫开来,心里柔软而感动。那时院子的桂花开得正盛,馥郁的芳香越过如水的月光抵达了逐渐涌起的往事。想起他欢快地在阳光下向我挥手告别,我也是欢快的。我知道,人生的际遇便是这样,在每一个转弯的路口,在每一段路的开始,这个挥手的姿势会在以后的生活中重复很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