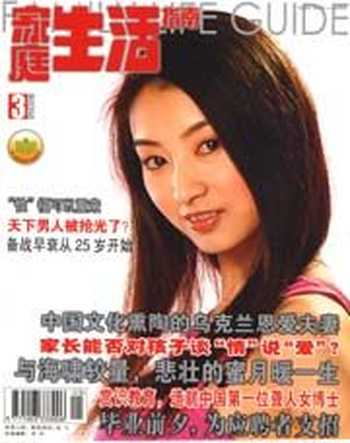中国文化熏陶的乌克兰恩爱夫妻
草原飞雪
阿拉·尤尔科夫斯卡娅是一个娇小、美丽的乌克兰女人,她温柔、文静而又充满智慧。她的丈夫伊万·斯杰潘切科高大、健壮,是一位有着12部专著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阿拉深爱她的丈夫,在离婚率极高的乌克兰,为了使自己能和伊万长相厮守,恩恩爱爱白头偕老,阿拉选择了用中国文化熏陶丈夫,并力促丈夫到中国任教。渐渐地,中国文化浸入了伊万的骨髓,他变成了一个中国式的丈夫,他爱妻子,对家庭极有责任感。2004年9月29日,阿拉和伊万的家被长春市妇联评为长春市文明家庭。
相恋在波兰
1981年,阿拉在喀什大学毕业后,进了喀什市基洛夫区教育局当了干部。1986年春天,前苏联教育部要选派一批教师到波兰首都华沙为波兰培训俄语教师,临行前,这批教师到首都莫斯科进行短期培训。作为教育局的干部,阿拉被选中作为这批教师的管理者,阿拉和伊万正巧在一个小组内。由于同是来自乌克兰,因此,阿拉和伊万相识没几天就很亲近了,到了华沙后不久,俩人就相互有了感情。伊万见自己对阿拉表示好感阿拉并不反对,就开始了对这个娇小俊美的女人的追求。那年,阿拉27岁,伊万29岁。
从波兰回国后不久,伊万就去莫斯科读副博士了。而这年秋天,应波兰一家俄语学校的邀请,阿拉要去做这所学校的校长。临行前,阿拉给远在莫斯科的伊万打电话,问他说:“伊万·我还要去波兰,你反对吗?”这时的阿拉认为她和伊万的爱情已经成熟了,她想听到伊万挽留她的话,如果伊万挽留她,舍不得她一个人走,她会辞去波兰那个校长职务留在国内的。可是,伊万却在电话里说:“是吗,又要去波兰吗?去也好,多挣点钱回来吧!”
阿拉的心有点凉,她没想到听到她要去波兰的话,伊万竟会没有表现出一点儿依依不舍。正当阿拉情绪低落地收拾行装,准备出国时,伊万却如同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在一天早晨,突然出现在阿拉面前,手捧着一大束玫瑰花向她正式求婚了。
伊万说:“阿拉,嫁给我吧!你要是答应了我的求婚,我就允许你去波兰,去那里多挣点钱,回来后,就暂时不要上班了,在家里呆着,等着做我的新娘。如果你不答应嫁给我,我就不同意你出国,我要把你留在国内,再好好追你。”阿拉流着泪,接受了伊万的求婚。
那是伊万第一次来喀什市,阿拉把伊万引见给了自己的父母,又带着伊万游览了喀什市,还带着伊万看了列宁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几天后,阿拉带着对伊万的思念去了波兰。
阿拉在波兰工作了一年,回来后,就去了哈尔科夫市,住进了伊万的家,和伊万的父母住在一起,等着远在莫斯科读副博士的伊万。
1989年秋天,伊万从莫斯科学成回来后,两人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第二天,伊万骑着摩托车驮着阿拉去了伊万的出生地日丹诺夫,在那里看了和黑海连在一起的亚速海,晒了太阳。蜜月之后,阿拉在哈尔科夫市汽车学院做了教研室主任,伊万在哈尔科夫市师范学院做了俄文系副主任。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
要像中国夫妻那样相爱
俄联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疆域,而人口却非常稀少,在这稀少的人口中,女性远远多于男性。特别是卫国战争以后,由于男人们许多都战死沙场了,女性更是远远多于男性,这种现状到现在也没有恢复过来,以至于现在的圣彼得堡等城市里男女比例竟然是一比七。
女性大比例的多于男性,再加上俄国人骨子里的浪漫,这使得许多俄国男人崇尚爱情但却并不忠诚于婚姻和家庭。在俄联邦街头,随处可以看见一个已婚的女人领着一个小孩在走路,却看不见女人身边有丈夫。和这些女人交谈时,她们都会说她们结过婚,她的孩子有父亲,但细问这孩子的父亲时,有许多问题这些女人却说不清楚。因为她们不知道她们曾经的丈夫现在正在哪个妙龄女郎的怀里。对于这种现状,她们默默地认了,她们知道自己不再有妙龄和青春,她们竞争不过那些没生过孩子的妙龄女郎。
阿拉生过孩子后,内心也非常恐慌。她非常非常爱伊万,想和伊万厮守一生,她不知道伊万会不会像别的男人那样不再爱生过孩子后的她,而和另外一个女人走。伊万高大、健壮、帅气又有学问,正是女人守猎的目标。有一段时间,阿拉感觉到了有个女人在追伊万,也感觉到了伊万的心开始在她和那个女人之间游移。
那段时间,每当伊万夹着书本走出家门后,阿拉总要隔着爬满藤蔓的窗子看着他离去。她想,也许有一天伊万会对她说他不再回这个家了,不禁默默垂泪。阿拉想起了她少女时读的中国作家巴金写的《家》,觉慧为了责任而牺牲了爱情的故事情节也曾让她流过泪。她同情觉慧,并曾对书中的觉慧说:“觉慧,你应该要你自己的爱呀!”可现在,她觉得觉慧那种责任感,对于一个家,对于一个女人太重要了。她知道觉慧是中国男人的缩影,中国男人绝大多数都是觉慧那样的,一旦结婚生子了,多数都会和妻子白头偕老。阿拉想:如果伊万是觉慧就好了。
正当阿拉为自己的婚姻担忧时,阿拉抓住了一个让伊万和中国人交朋友的机会。1991年秋天,伊万所在的师范学院来了七名中国留学生。阿拉知道后,就拼命地劝说丈夫去带中国留学生。在阿拉的一再主张下,伊万带了两个留学生。因为带中国留学生的关系,非常喜爱做学问的伊万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了。
一天,伊万回家后对阿拉说:“中国文化和俄国文化真的不同,中国人在感情上很保守,我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近一段时间在拼命躲着一个追她的金发女孩,我能看得出他很爱那个女孩子,但他却躲着,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
伊万说的那个留学生叫王民,是河北大学的讲师,32岁了。伊万讲了王民的故事后,阿拉就开始注意王民了,她总是找机会让伊万请王民来家里做客,让王民给她和伊万讲中国的故事。渐渐地,阿拉和王民熟悉了。一天,阿拉和伊万请王民在家里吃完俄餐后,阿拉问:“王民,听说有一个俄国女孩在追你,你也很爱她,你为什么躲着她呀?”王民红着脸说:“是有这回事,我也很爱那个女孩,可是我在中国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了,因此,我不能接受俄国女孩的爱。那个女孩是真爱我的,我接受了她的爱,又不能娶她,我就是伤害了她。我如果娶了她,就是伤害了我在中国的妻子和孩子。我不能伤害中国的妻子和孩子,又不能伤害俄国女孩,我只有忍着,让我自己受苦。”
王民走后,阿拉紧紧地抱住伊万,泪流满面,失声痛哭起来。阿拉的哭让伊万很惊慌,他拍打着阿拉的背,好不容易才将阿拉哄好。伊万问:“阿拉,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大哭啊?”阿拉哽咽着说:“伊万,我怕你会和其他男人一样,不要我和孩子,去和别的女人过。你要是王民就好了!中国的丈夫多好,多有责任感啊!”说着,阿拉拉着伊万坐在自己身边,拿着笔,在一张纸上一
边画着一边说:“伊万,你带了中国留学生后,我也开始研究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字真有意思。比如说‘丈夫这两个字,越研究越有深意。‘丈是三米多,‘夫是天字出头,中国女人心中的丈夫应该是不要把他看得太紧又要把他看得比天还大的意思。伊万,在我心中,你真的比天还大,我希望我们能像中国夫妻那样一生相守,我爱你,但不把你看得很紧,你可以有情人,但不能不要我和孩子,我们要白头偕老,你是我一生的依靠啊!”阿拉这番话,说得伊万眼睛也湿润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在以后的日子里,阿拉和伊万读了许多孔子、孟子、老于、韩非子的书,还读了《莱根谈》。在读这些书,感受着中国文化时,阿拉有意识地修剪掉自己身上的独立意识,她学着做一个中国式的小女人。阿拉的这种依赖,伊万挺受用。一天,伊万开玩笑地对阿拉说:“阿拉,你这样喜欢中国,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国式的小女人,中国文化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夫让妻亡妻不得不亡。如果有一天,我让你亡你可以亡吗?”阿拉说:“只要是夫君让我亡的,我就亡,为夫君而亡死也开心。”伊万放声大笑了,笑过,把阿拉揽在怀里,流出了眼泪。伊万说:“阿拉,我是和你开玩笑的,我怎么舍得你死呢?我会一生爱你,只爱你一个。”伊万伸出他粗状的手指,捺了下阿拉娇小的鼻头。
一段时间后,阿拉感觉到伊万的心全回来了。他开始一个心眼地爱家,爱阿拉,爱孩子。
取得了保卫自己婚姻的初步胜利后,阿拉又进一步想:如果能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让丈夫在中国那个国度里真切地感受中国男人的生活,丈夫对她,对家,应该更有责任感,他们的婚姻应该更加稳固了。
在中国被评为文明家庭
2000年秋天,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一个讲师来伊万任教的师范学院留学,很自然的,这个讲师也成了阿拉和伊万共同的朋友。得知阿拉和伊万非常喜爱中国文化,阿拉非常想让伊万去中国工作的情况后,这个讲师就帮伊万同母校联系了请伊万去母校做外教的事。
2001年9月,阿拉和伊万这对乌克兰夫妇坐着火车,穿过了俄联邦广的土地,沿着贝加尔湖一路前行,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来到了北国春城长春。吉林大学热情地欢迎了他们。
吉林大学让这对夫妻住进了坐落在长春市贵族区的东朝阳路外国专家公寓里,阿拉和伊万在中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们接触最多的是吉林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主任肖教授一家。
肖教授有两个儿子,都已成人,参加工作了。肖教授的夫人也是高级知识分子。肖教授家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肖教授夫妇非常恩爱,夫妻两人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爱情。肖教授虽然是一个著名学者,但却很会做家务,烧得一手好菜。肖教授对妻子爱得非常细腻,虽然他教学和学术研究很忙,每天大量的时间都扎在书本和资料堆里,但他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和妻子一起出去散步。下楼前,肖教授会帮妻子扯平衣角,正好帽子。走在路上,肖教授会挽着妻子的手臂,让妻子走在他身体的里侧,免得后面开来的车速度过快让妻子受到惊吓。
肖教授这种对妻子细致入微的爱,让阿拉非常感动,她决心让伊万跟肖教授多接触,学着做一个肖教授那样的丈夫。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国内不太热衷于交际的阿拉主动和肖教授夫妇亲热。遇有肖教授夫妇邀请他们夫妇出去逛街或是搞小型的家庭聚会时,她和伊万就会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前去参加。在肖教授家里,阿拉夫妇和肖教授夫妇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分工明确地择菜炒菜,晚餐后在一起唱歌跳舞。他们最爱唱的是四个人都会唱的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咔秋莎》等。
无数个夜晚,在肖教授家里,四个人唱着深情的俄罗斯歌曲。阿拉挽着丈夫和肖教授夫人的手臂纵情地舞蹈着,感受着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阿拉的努力没有白费,她亲眼看着伊万一天一天的变化着,先是伊万学会了做中国菜,他会做鱼香茄条儿,木须西红柿,糖醋鲤鱼等等。每做成一个菜,他都会让阿拉先尝第一口,阿拉不表扬他是绝对不行的。伊万也学会了中国男人式的缠绵,出门前,他会给阿拉系好围巾,走在马路上,他也会让阿拉走在他身体的里侧。伊万忍受不了阿拉受到一点点的焦急和惊吓,有一次为了不让阿拉着急,伊万竟在长春的大街上闹出了笑话。
那是2003年冬天,那天,阿拉和伊万去逛街,在一个商场里,阿拉走丢了。阿拉中国话说得不好,又有些辨不清方向,伊万在商场的人群中匆匆穿行着,寻找着。找了一会儿还找不到,伊万就跑着去了商场的广播室。他对播音员说他的妻子走丢了,请求播音员让他亲自广播。伊万用俄语在广播里喊阿拉的名字,一连喊了数遍,然后说自己会在商场入口外马路的正中间等阿拉。伊万说,他会站在马路最显眼的地方,阿拉只要走出商场的正门,就会看到他的。让阿拉千万别着急。
放下播音的话筒,伊万就跑出商场,跑到马路中间,站在交警指挥交通那个位置上了。正是下班高峰,一个高大、满头长发的老外站在以往交警站着指挥交通的那个位置,立即引起了行人的注意,不一会儿围观伊万的人就在马路两侧站满了。交警很快发现了伊万,前去让他离开,但伊万说在等妻子,不肯离开,后来,竟和交警发生了争吵。要不是阿拉很快找到了他,不知道伊万会和交警争执多久。
阿拉和伊万这对外教夫妻的恩爱故事,很快就被吉林大学师生和东朝阳路外国专家公寓的人们所熟知了。人们谈论着他们的恩爱。对他们投以羡慕的目光。2004年9月,长春市妇联在全市评选文明家庭,吉林大学妇女工作委员会推荐了阿拉夫妇,经考核,阿拉夫妇当选了。
2004年9月29日,在长春市妇联举行的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阿拉手捧着长春市妇联颁发给她的锃亮的文朋家庭牌匾,非常自豪。为了保卫婚姻,她自愿做小女人,处处以丈夫为主,可长春市妇联颁发给她的牌匾上写的却是“阿拉夫妇”,这个评选是以她为主的啊!一个外国女人,得到了中国妇女联合会的肯定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当她从主席台上下来,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抚摸着奖牌,她哭了。她流的是激动而幸福的泪。她对自己说:我选择让丈夫接触中国人,来中国,是对的。经过了十几年生活的风雨,我的丈夫仍然如新婚一般爱我,我的家庭是那样的牢固,还获得了中国文明家庭称号。而我的许多同学、同事,她们原来的家庭早巳不存在了!我要感谢上帝,感谢中国!
(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改编、转载、上网,违者必究。)
责编/孙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