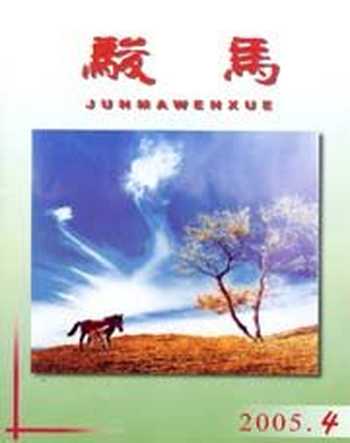市井传奇
丁 可
吹画张
柳河镇上曾出过几位奇人,“吹画张”便是其中之一。
这吹画张已年逾六旬,生得身形瘦小,发如枯草。他在8岁那年上,大病了一场,待病愈之后,竟变成了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或许受其父影响,他对书画极有悟性。但他在做画之时,行为怪异:待墨研好,他则将笔弃置一边,独守一方宣纸,思绪良久,陡然将墨汁泼洒在纸上。然后,俯下身来狂吹一通。待显出峰峦、树林、溪流的雏形之后,吹画张便毫无顾忌地吸一口浓墨在嘴里搅拌,咕咕有声,稍后,淅淅沥沥地洒在画上,再饮半杯清酒漱口,运足气力喷在画上。经他一洒一喷,再看那画,意境顿生。山水之间,宛如有松涛涌动、涧水潺潺……
吹画张没有妻室,他在父亲临终之前,给父亲吹了一幅《猛虎登山图》。曾有数人目睹过那幅奇画:只见画上的那只虎威风凛凛,迎着旭日健步而上。观者似乎都听到虎啸之声。他的父亲见画之后,哀叹一声:“儿,生不逢时呵……”便咽了气。之后,那幅奇画被吹画张焚烧在父亲的坟前。
从此,吹画张的家境日益衰败,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为了喝酒,他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家当,最后只剩下了一间土舍。凡是向他求画者,只要以酒款待,他从不拒绝。不过,谁若不明底细请其画虎,他就会怒而喷墨离去。因而,柳河镇上的人虽知道吹画张身怀画虎绝技,却极难再睹其神采。
这一年刚立春,一群鬼子兵闯进柳河镇里来,他们强迫镇子里的男人到柳河滩旁修建据点。不久,三座阴森森的炮楼在柳河镇上耸立起来。鬼子兵的头目山田少佐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尤其嗜好搜刮名人字画。他从吴保长那里得知,柳河镇上竟有这么一个奇人,顿时来了兴趣,便命令吴保长赶紧把吹画张带到据点来。
山田少佐早已令人备好了纸墨。当吴保长把吹画张带进据点里来时,他那张像猪头一样肥胖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说:“你的给我画一幅猛虎图,我的大大地赏你!”吹画张晃动着他那瘦小的脑袋,傻乎乎地笑着。山田少佐面露凶相,威胁道:“你的不画,死了死了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腰间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军刀,在吹画张的脖子上比划了两下。
吹画张吓得双腿发颤,“扑通”一下瘫坐在地上。吴保长慌忙把他搀扶起来,怂恿道:“你就给皇军大人画一幅猛虎图吧,若惹恼了皇军,咱俩的脑袋都得搬家!”
许久,吹画张才缓过神来,喃喃自语道:“酒、酒……”
吴保长在山田少佐面前低头哈腰,谄媚道:“这个疯子做画离不了酒,无酒不成画。”
山田少佐面露喜色,命手下搬来一坛清酒。待三碗清酒下肚之后,吹画张面露红润,掌心冒汗,神色也渐渐镇静下来。他急不可待地端起墨汁来,边泼边吹,眨眼工夫,一只威猛的下山老虎跃然纸上,它正迎着暮色,雄赳赳地走下山来。继而,他又噙了一口浓墨,洒在虎身之上。瞬间,画上的虎威又增添了十分,周围的人一个个都惊愕得目瞪口呆。半晌,山田少佐才回过味来,他竖起大拇指,叫道:“奇画、奇画,你的大大的良民!”
到了晚上,山田少佐為庆贺得到此画,在据点里摆下了几桌酒席。待酒酣之时,山田少佐捧出那幅奇画,欲让众人目睹一下虎姿。他小心翼翼地铺开画卷,忽然有一道寒气袭来,只见画上那只猛虎陡然跃起,狂啸着朝山田少佐扑来。他“哎呀”一声惊叫,便昏倒在地。他的那些手下们也都被惊得酒醒大半,慌忙把他扶起来。画面上那只猛虎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一滩浓墨像一团污血似地浮在宣纸上。
翌日凌晨,山田少佐一命呜呼。吴保长带着一帮鬼子兵急匆匆地去捉拿吹画张,吹画张却早已不知去向。
三炮绝
清朝光绪年间,在墨城东南有一处大杂院,每天都有一些马戏班子和杂耍艺人到此处来扎台卖艺。当然,这大杂院也并非是自由之地,凡想在此扎台的艺人,必先得到“行头”牛疤那里下“拜帖”,给他奉上一些银两,然后,经他点头应允之后,方可扎台。否则,不消半晌就得“烂摊子”。
牛疤是墨城县一大无赖,长得又黑又粗,酷似一头黑熊。他心狠手辣,会几路拳脚。他靠欺行霸市勒索来的数百两银子买通官府,坐上了大杂院的“行头”。他手下还养着七八个凶如恶狼的打手,没事儿他们整天泡在“翠红楼”里,跟那些妓女们厮混。
这一天,大杂院里来了一个叫“三炮绝”的口技艺人。他50岁上下的年纪,虽长得瘦小枯干,但双目炯炯有神。在他的身旁摆着一条油漆剥落的案子,左竖一块黄缎招牌,上书“三炮绝”几个墨字。众人倍感新鲜,他刚一扎好台,“呼啦”就围上来不少看光景的。
在大杂院里,论口技,扎台时间最长的是二里铺的“百鸟张”。他在大杂院扎台这半年多来,几乎没有空过场。一来是他嘴里有些真功夫,只要是天上飞的,像山雀、斑鸠、杜鹃啦,学啥像啥;二来是他跟牛疤还有一点亲戚关系,自然比别的台子多了一些照应。
再说那个“三炮绝”,他刚一开场,就把“百鸟张”的台给扯了。他不光能学鸟鸣、虎啸、狼嚎,只要台下的观众想听啥,他就能学啥,并且模仿得惟妙惟肖。那些听腻了“百鸟张”表演的人,自然对“三炮绝”更感兴趣。冷不丁冒出“三炮绝”这么一个冤家,“百鸟张”又妒又恨。他匆匆收拾起场子,然后找牛疤去了。
“百鸟张”在翠红楼找到牛疤时,他正跟“小翠仙”搂抱在一起闷大烟哩。牛疤见是“百鸟张”求见,甚感不悦,冷冷地道:“龟球!啥屁事也不挑个时辰!”
“百鸟张”慌忙跪下,哭丧着道:“牛爷,俺让人家给扯台了。”
牛疤一听,两条秃眉“腾”一下子竖了起来,问道:“哪个龟球,如此胆大?!”
“百鸟张”哭诉道:“今早儿,大杂院突然冒出个‘三炮绝来,他仗着那点下三烂的拙技,把俺的场子给扯了。”
牛疤搔了搔秃脑袋,沉吟了一阵儿,道:“那个三——他娘的什么绝,可从没给俺下过‘拜帖,咋钻进大杂院里来了?”
“百鸟张”故意火上浇油道:“那个‘三炮绝扎台前说了,他就不信这个邪——”
牛疤怒不可遏地起身下床,收拾整齐衣服,然后大声吩咐候在门外的小杂役道:“快去把那几个烂猪操的给爷唤来!”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小翠仙”的奶子上捏了一把。
“小翠仙”嗔怪道:“牛爷,你可快去快回。”稍后,他“嗵嗵”地走下楼来,那些打手已经候在了楼下,然后簇拥着他气势汹汹地朝大杂院奔去。他们来到“三炮绝”的台前,只见那台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不时地从里面传来一阵阵喝彩声。
众人见是牛疤来了,围观的人墙惶恐地朝两旁闪开,顿时闪出一条道来,全场鸦雀无声。牛疤大摇大摆地走到“三炮绝”的台前,一屁股坐在那条几案上,也斜着眼看着面前这个身形枯瘦的艺人,然后用不屑的口气问道:“你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
“三炮绝”慌忙抱拳,拱身施礼道:“小人有眼无珠,不识大爷为何方神圣?”
众打手怒声斥道:“瞎了你的狗眼!这就是大杂院的‘行头——牛爷!”
牛疤朝手下摆了摆手,然后慢条斯理道:“今儿碰上爷高兴,就给你留一条生路。不过,你得在这儿跟‘百鸟张比一比本事。你若赢了,爷就准你收起场子,立马走人;若是输了嘛,你就得给在场的每个人磕一个响头,然后爬出大杂院!”
无奈,“三炮绝”只得跟“百鸟张”比试一番。“百鸟张”先学了一通“乳燕脆鸣”,“三炮绝”则学了一通“杜鹃啼晓”;“百鸟张”接着学了一通“黄莺求偶”,而“三炮绝”又学了一通“布谷迎春”。俩人一直比试了百十个回合,不分高低。这可真让围观的百姓开了眼界,人们好像早已经忘了牛疤他们的存在,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
最后,“百鸟张”拿出了看家的本领“百鸟朝凤”,只见他的嘴巴在紧张地翕动着,而周围顿时有成百上千只鸟儿在欢快地鸣唱,而且鸣声各异,缠绵交错,使人怀疑纵是生着一百张嘴,也难以模仿出这么多的声音。待表演完毕,“百鸟张”的额头上已经渗满了汗珠。众人在惊叹不已之余,都替“三炮绝”捏一把冷汗。
而“三炮绝”丝毫不显畏惧,他运足力气,表演了一段“群雄鏖战”,只听人喊马嘶、冷箭飕飕、兵刃相交,仿佛有千军万马在此激战,只杀得天昏地暗,令人听了毛骨悚然。
“三炮绝”表演完毕之后脸不变色气不虚。此时,牛疤见“三炮绝”的本事的确在“百鸟张”之上,便朝手下暗使了一个眼色。他们一个个就像恶狼似的朝“三炮绝”扑了过来,周围人群顿时大乱。“三炮绝”赶紧往后一闪,纵身跃上旁边的一块石碑,朝牛疤怒声斥责道:“你为何食言?!”
牛疤冷笑道:“你牛爷说话从来就不算话,给我打!”
那些打手们从附近的那个戏摊上找来一些长竹竿,每人手持一根,将“三炮绝”团团围住。
此时,只见“三炮绝”稳稳地立在石碑之上,他气运丹田,只听“轰隆”一声震天巨响,从他的口中爆发出来,那巨响好像要将大地震裂。那些站在远处看热闹的人群,还误认为是真的大炮在响哩,都四处逃窜开去。而那几个打手也被他震得目瞪口呆,“三炮绝”又朝着牛疤连发两声,再看那牛疤“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三炮绝”如同一只轻巧的飞燕,跳下石碑,瞬间便消失在慌乱四散的人群里。那些打手慌忙把牛疤从地上扶了起来,只见他嘴歪眼斜,鼻孔出血,待苏醒过来之后,说话已辞不达言,竟变成了痴人一个。
几天之后,那个“百鸟张”也收拾起行李离开大杂院,到别处谋生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去给他捧场,人们都这么说:“听过‘三炮绝的那三声炮响,‘百鸟张玩的那算是些啥鸟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