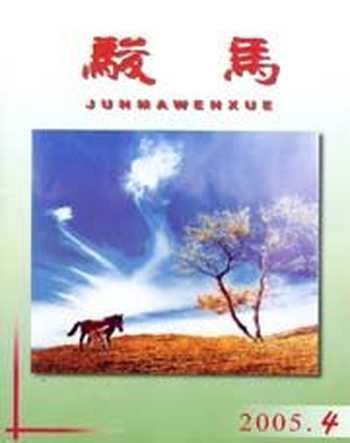小说两则
晓 立
养犬
二发在山沟里承包了百十亩地后,盖了个小土房,开始一“发”不可收了。
二发有一嗜好——养狗,养好狗,也就是说名犬。一日,他从集市上乐颠颠抱回一德国黑背狗崽儿,胖乎乎虎头虎脑甚是喜人。
“正宗的黑背,上好的狗,母的,能下崽呢!”他逢人便说,仿佛他养狗也能发财,再增加一“发”,要不怎么叫“二发”呢!他给小狗也起了一个吉利又如意的名字——发儿,叫起来“发儿发儿”,好记也好听,二发很得意。
发儿渐渐地长大,二发也不闲着地培训,他打算把发儿训练成名副其实的名犬,卖个好价钱。发儿小的时候,他就开始让它衔东西,抛出去衔回来,抛出去又衔回来,如此这般。待发儿大一点时,他就让它扑咬东西。二发在小臂上缠了许多破棉布,口中念念有词,“袭——袭!”发儿就敏捷地蹿得老高,一下咬住不放,同时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响,凶猛无比。
待发儿再大一些的时候,二发就让它进行实战了。二发的地里偶尔钻进来散放的牛羊,祸害庄稼。半大的发儿就“汪汪”直叫,牛羊也不理会,远远地闷头吃。二发干活回来,见此大怒,操起两个大土坷垃喊上发儿就冲过去。发儿心领神会,箭一般地射了出去。牛羊见有人来且气势汹汹,扭头就逃。二发大喊大叫,土坷垃便呼啸而出,命中一黑白花牛头,炸飞开去。二发又一声喊“袭——袭!”发儿咬住一只羊腿不放松,使得那只可怜的羊连滚带爬地跌进了沟里,带伤而逃。“算你命大,哼!”望着远去的畜生们,二发长长出了一口气,一种胜利感和自豪感撞击着他的心胸。
随着发儿的长大、成熟,凡有此种情况二发一般不亲自出马,只需一挥手“袭——袭!”两声,发儿就勇往直前,驱赶牛羊。羊尤其怕它,望风而逃,屁滚尿流。
二发得意,逢人便说:“你看我这狗,尿性!”
尿性的狗还能创收呢!有一天,贪嘴的羊又来占便宜。二发见发儿出去后好半天不回来,就拿起望远镜一望,竟发现发儿在吃力地往回拖—只羊,走几步歇一歇。二发乐了,这回有羊肉吃喽。他冲出门去,用自行车将奄奄一息的半大羊驮了回来。
二發用这只羊犒劳了干活的短工,伙食一下子达到了小康水平。发儿也成了功臣,下货、骨头之类自不在话下,吃得甜嘴抹舌肚子浑圆。
也怪,从此牛羊再不光顾,类似的好事二发很长时间没有幸遇了。
这一年的庄稼长得也不如意,干旱,就是他妈的不下雨,二发也没辙。上秋,有人提议让二发养点啥,让这些没长成的苞谷当青储饲料,牛羊市场挺火的,说不定也能发财呢。
二发脑袋来得快,没几天就赶回一群羊,价格便宜到家了。因为今年干旱草都没长起来,许多牧人担心牲畜越不了冬,就急急忙忙地出了手,这让二发抓住了机遇。
高兴的二发买来了酒菜,与帮忙的几个哥们儿就喝开了,一边吹着如何发“羊”财,一边还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忽然,一个从外边撒尿回来的哥们儿说:“狗把羊咬了!”待喝得差不多的二发出来时,只见一只大母羊的后屁股已被发儿掏烂了,血流了一地。
发儿自然被一顿暴打。然而,不管怎么打,发儿见羊就咬,真是死孩子掉井——没治了。再打急了,发儿竟张开血盆大口咬起二发,二发腿上的伤口流着血。后来,二发流着泪将发儿送进了镇上的狗肉馆,发儿临死也没闹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
春心
夜深了,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灯下。室内的珠光宝气和豪华的装修,也掩饰不住空气中的孤寂与落寞。电视剧无聊地演着什么感情戏,简直是自作多情。
她痛苦,痛苦得她想背叛她的丈夫。
丈夫经常下班不回家,属于那种“上了等的男人”。孩子上学要很晚才回来,现在高中抓得可是相当紧哪。
丈夫大小也是个官儿,光不回家还不算啥事,早就听说外边有点别的。他单位那个张小姐又年轻又漂亮,早被他苍蝇似地叮上了。她不但有所耳闻,有一两次还碰上了。能说什么呢?他说:“工作需要,你管得着么!再说,也不能总让我看你这张老脸吧——真是,吃饱撑的!”
其实,她长得并不难看,高挑的个儿,瓜子脸儿,白皙的面容。当然,这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变,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隐隐约约的痕迹。尽管她想尽了办法,青春还是毫不留情地渐行渐远。
解释,越描越黑。吵架,更不是办法。
更可气的是,外边还有个什么芳,跟自己岁数差不多,半老徐娘了,有什么意思呢?真掉价呀!
这不是听风就是雨,绝对是有证据的。丈夫常背着她给那个女人打电话,那手机里就有这个骚女人的号码,还有他们互发短信的黄段子。这,许多人都知道,人家就是不对她说而已。
女人的直觉更是了不得,丈夫渐渐地很少碰她,爱情开始死亡。
唉,碰上这样的男人算倒了霉了。教育?这种事是能教育得了的么?本性呵,就跟狗改不了吃屎,猫改不了吃腥一样。
她真想……唉,也都不是这岁数了,还扯啥呀。年轻的时候都挺过来了,丈夫两次在外学习,一学就是一年呵。自己带着孩子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呀。那时,因为有盼头,有希望,又有可爱的孩子在身边。同事小刘是个好人,有困难就来帮忙,偶尔有那个意思,她也假装不知道,总觉得应当忠于丈夫,绝不能整出花边新闻,那叫人多笑话呀!
现在孩子也大了,也不让人省心,好大学是没戏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也玩,我也学会潇洒。她想开了,架不住同事们劝哪。安慰说服,都是出于好心。
于是,她很快学会了跳舞,花样还不少,三步四步,恰恰伦巴。跳舞让她的身体舒展,音乐让她的思绪飞腾。舞厅里常有她的身影,当然也有男人的身影。
这个男人是她的舞友,叫宏,是跳舞时通过别人认识的。有个儿,也有模样,会好多种舞,于是成了她的老师。宏可不像有的男人见便宜就上,也不像有的男人贼眉鼠眼。他落落大方,彬彬有礼,舞姿优美。
她常找宏跳,宏也愿意找她,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她听了这话心里暗喜,白皙的脸上就荡起了青春。
流言蜚语开始生长。两天没有和宏跳舞了,她心里就痒痒得不行。宏的手机始终不开,她就几次想往宏的家打电话,说说自己心里的想法,她不能把话憋成了病。
她犹豫再三……电话的那边是女人的声音,微弱的声音,使她想起了别人告诉她的事。宏的妻子常年有病,是个贤惠而又可怜的女人。
她说:“我是宏的舞友,你好吗?也许你也听了许多闲话,对不起。也许你也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很糟。其实……说真的,我已经很痛苦了,再不想把痛苦转嫁给别人。请你放心,我的好姐姐。”电话那头说:“大妹子,其实我在家里什么也不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也相信宏,青春和幸福同样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