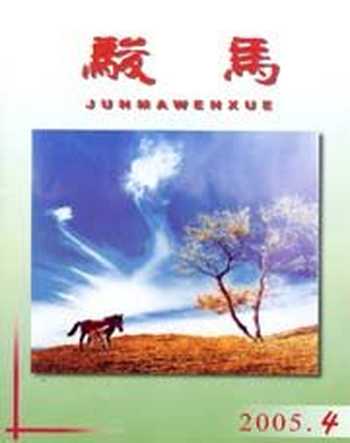蛤蟆沟春梦
杜庆文
子夜,月色朦胧,星光冷漠,乍暖还寒的蛤蟆沟沉寂得可怕。
蓦地,一个黑影从林场场部大门里幽灵般地闪了出来。他叼着烟,撇着腿,不紧不慢地向村东头走去。
突然,赖二家的黑风在柈子垛边的三角架里“汪汪”两声蹿了出來,当它发现打开栅门的是个熟悉的身影时马上安静下来,十分友好地晃着尾巴,哼唧着迎了上去。
那人摸着它的头,低声结巴道:“黑、黑风,来、来……”黑风在他腿上拱蹭着,只见那人从怀里掏出个馒头扔到一边,黑风追了过去,叼到窝里吃上了。
林场是木栅栏的世界,所有房舍统统被栅栏围住,仿佛古代的军帐,整整齐齐,错落有致,在月光下显得森严。
这是三间干打垒的泥草房,坐落在长满蒙古栎和榛棵的东山脚下。
东屋,炕上睡着赖二一家四口,大小子搂着被子拉开了风匣,小小子索性蹬翻了被子,睡成个“太”字。炕头的两口子则脸对着脸,似睡非睡地眯缝着眼。狗叫的时候,他们也没动,似乎在静待着什么。
西屋,炕头躺着位大姑娘,她确实睡着了,那十分均匀的呼吸就证明她睡得很香。她叫大曼,三天前从山东起身,海陆兼程,颠簸四五千里,来到了大兴安岭西部,投奔蛤蟆沟林场的表姨来了。表姨——赖二媳妇就是十年前自然灾害时跑盲流过来的,现在生活得不错。大曼家住鲁西南农村,好穷啊!一次,大曼读了表姨的来信,那信字虽不多,但有一点拴住了她的心:东北的大兴安岭是个神秘富有的地方,到那里能找个好对象,过上好生活。她整天地梦想着。东北有句歇后语:大姑娘要饭——死心眼儿。意思是说大姑娘到东北随便找个对象,就能混上个好生活。到东北去,到大兴安岭表姨生活的蛤蟆沟去,再也不想待在这里煎熬了。在大曼心里,似乎早就有个小伙子在林区默默地等她呢。青春的悸动火焰般整日整夜地灼烧着她。过了大年,过了端月,到了阳历四月,约摸北大荒也暖和了,大曼便征得爹爹的首肯,拿着年前信上交待的路线和地址,挟着个包裹寻到了表姨家。
这是第三宿了。旅途的疲乏虽已过去,但那火车、轮船的忽忽悠悠劲儿还没完全消失,她如在摇篮里一般。到这里她看到了满是森林的大山,领受了山沟里的寒气和林工家里的热炕头。大曼是个身材高大丰满的姑娘,苹果脸,黑黑的眼睛,厚厚的唇,除了有些憨,模样挺中看的,似乎很有福气的样子。她斜躺在被窝里,也只能这样,因为她的粗大,炕就显得窄了,头顶着炕沿,枕头几乎要掉下去。腿探出被外,圆实而又光洁。
大曼睡实了,黑风十分吝啬的两声吼叫根本没惊搅着她。
她是在一种美好的期待中睡着的。白天两耳灌满了表姨和表姨父给她选着对象的话。睡觉时她想:“表姨和姨父都是为俺好,俺一定要听话,会来点儿事儿,将来要孝敬他们,报答他们。”想着想着,表姨领进来一个小伙儿,身体棒棒的,脸蛋红红的,害羞地坐在她的身旁。表姨满面笑容,十分认真地说:“大曼,这是你小林哥,认识认识吧,俺还有事,你们谈谈,嘿嘿……”表姨出去了,就剩他们俩。稍事沉默之后,小林先说话了:“你叫大曼?”大曼忙回答:“是,俺叫李大曼,今年18虚岁。”“读过书?”“读过两年书,由于家里穷,也就不读了,虽说俺认识不了几个字,可俺能干活计。”小林乐了:“那你能上山伐树吗?”大曼说:“那有啥,俺还在山上挖过药采过石头呢。”“那咱俩上山啊?”大曼乐了:“上就上,俺这几天闲着正难受。”两个人手拉手爬山,大曼出了一身汗。突然,小林不见了,林子里静得瘆人,这时从林子里钻出一个浑身黑毛、直立走路的笨家伙朝她走来。她吓得向后退着。那黑家伙张着血盆大口,吐着长舌头,越走越近。她倒退着,一脚踩空,大叫一声滚下山去……她惊醒了,眼前黑乎乎的,不见山林,原来是一场梦。她想翻身,却动不了,这才发现身子上面爬着一个人。
“姨……救命啊!……”大曼挣扎着,叫喊着。
“你是谁?坏蛋!……”大曼拼命地撕打着,叫骂着。
那人像头熊沉重地压迫着她,又像只癞蛤蟆抓摸着她的身子,见大曼强烈地反抗,他说话了:“姑、姑娘……姑、姑奶奶,别、别叫,我、我是曲、曲……”
大曼叫骂着,听不见他说什么,当她彻底地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了,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她一下子将那家伙掀到一边。
大曼马上起身,忙用被子盖住身子蜷缩在那里,哭骂着:“你是哪来的畜生,糟蹋俺的清白,俺要告你——你这个坏种!呜——”
令人奇怪的是,那家伙在她的叫骂声中并没有仓皇逃窜,只见他慌忙穿上裤子,坐在炕稍,居然低下蛤蟆头,央求道:“哎、哎,姑、姑娘,别、别这样,有话慢、慢说,我、我——”
大曼骂道:“俺要告你这个磕巴!呜——滚出去!——”
这时,东屋的夫妻俩披着衣服慌张地进来了:“你们这是?”
那家伙忙说:“老、老赖,这是我、我走错屋了,啊啊……走、走错了。”
大曼一下子扑在表姨的怀里,哭道:“是这个磕巴欺负了俺,姨,你可要给俺做主啊!呜——俺好命苦啊……”
表姨哄着她。
赖二猛地抓住那家伙,狠狠地扇了两巴掌,骂道:“曲磕巴,你这个混账王八蛋!竟敢夜闯民宅,侮辱良家姑娘,说,该当何罪?”
曲磕巴听了“扑通”跪在炕上,双手作揖恳求道:“老、老赖二哥,不,老赖二、二爷,二祖宗,我、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说着,他自己扇着自己的嘴巴,就像打小孩屁股那样“啪啪”脆响。
表姨搂住大曼骂道:“俺的外甥女啊,你好命苦啊,刚投奔俺来两天就让人欺负了……曲磕巴,你不得好死!”
这时,表姨突然放开大曼,疯了一般地冲向曲磕巴,撕着,打着,骂着……
曲磕巴任她撕扯,直到她发泄完毕,便像鸡啄米似地磕起头来:“我不是人!你、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全、全由你们了!”
表姨索性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骂:“曲磕巴呀曲磕巴,你这个狗杂种,就是下锅油榨了你也还不回俺外甥女的清白啊!天啊,这可让俺外甥女咋出门啊?天啊!……”
大曼仍捂着被子哭着。
赖二在地上似乎急得直转磨磨:“这可咋办?这可咋办?要是说出去,这姑娘的名声?唉……”
曲磕巴这时下了地,跪在二人面前,还是打着自己:“我曲、曲磕巴是牲口,赖二爷爷赖二奶奶,我求你们啦!放、放我一马,以后就、就是让我曲、曲磕巴做、做牛做马,天天拉车拉、拉磨,我、我也情、情愿!”
赖二坐在炕沿上吸起烟来。
表姨又搂着大曼哭了起来。
黑风在院子里冲着窗户不安地狂吠着。
曲磕巴跪在地上仍是鸡啄米似地磕着头……
一晃这事儿过去五年了,大曼自然屈就于曲磕巴做了夫妻,孩子都生下三个了。
开始,曲磕巴说自己30岁,后来大曼从林工的口中得知他已53岁了,整整大她30岁,比她爹还大10岁。她好委屈啊,可生米煮成了熟饭,也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王八往水里走了。大曼哭过多次,也曾想过死。表姨安慰她说这是命,是上天安排的,也叫缘分,尽管相差悬殊,也比旧社会给人家当小老婆强呢。她认了,好在曲磕巴还是林场的老工人,当保管员兼更夫,每月能领上几十块呢。殊不知,这件事儿是大曼她表姨和表姨父赖二与曲磕巴共同策划的阴谋。
原来,赖二和大曼的表姨两个人都爱小,只要占点小便宜,就高兴得不知姓啥。这期间,作为林场仓库保管员兼更夫的老光棍曲磕巴便乘虚而入。大曼的表姨刚嫁赖二时,一次做饭由于柈子太湿,呛烟,她便跑到门口喘口气儿,揉着被呛的眼睛,正好曲磕巴路过这里,便垂涎地问:“弟、弟妹,赖二委、委屈你、你啦?”表姨看了看他:“才不是呢,烟呛的,柈子湿,不好烧。”曲磕巴听了连“啊”了两声,转头回到场部就拎回一罐柴油到了赖二家。表姨见了非常感激,认为他是好心肠的人,便留他吃饭,他也没客气,并声明有什么困难找他,保证没问题。后来表姨缺什么就去找曲磕巴。别看他磕巴,只要表姨一句话,他就一点也不“磕巴”,马上行动,麻利得很。其实,这曲磕巴当年游手好闲,吃喝嫖赌全能,只是当了林场工人,他不得不收敛一些,可一直没人给他介绍对象,再说他也不想要带孩子的寡妇。除非给他找个黄花大闺女。大家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屁,他说他就想吃天鹅屁。赖二是他的赌友,别看他长得鼠头鼠脑,可离过两次婚了,娶的都是黄花闺女,大家都说他走桃花运。大曼她表姨就是被他用钱买来的。那钱正是从曲磕巴那里赢来的,马上就派上了用场。曲磕巴那个急呀,恨呀,可干没辙,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赖二从山东老家又领回一个大闺女搂进了被窝。他在酒桌上曾对赖二说:“你小子真、真他妈的有、有福气,你、你这个媳妇应、应该有我、我一半。”赖二笑着说:“没问题,反正我都腻了,你能保证她顺从,我是情愿戴绿帽子了,不过你小子可不能白白占我老婆便宜啊!”曲磕巴说:“那当然,我、我曲磕巴是、是小器人、人吗?嘿嘿……”两个人像开玩笑似地达成了默契,便有曲磕巴常去赖二家帮忙赶串的事儿。“赶串”就是赶着饭时到人家串门混上一顿饭。其实这“传统”是旧社会挨饿留下来的,只是现今在极个别的懒汉身上还体现而已。这曲嗑巴是个老光棍儿,上赖家赶个饭时,再帮赖二媳妇干点儿零活,送点儿日用品,吃点儿饭太正常了。至于后来搞男女关系的事儿,慢慢也正常了。开始,表姨是不同意的,可听了曲磕巴给她讲了赖二的历史,一怒之下也就入港了。何况,曲磕巴第一次就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全塞进表姨兜里了呢!从此曲磕巴便成了赖家的常客,他每月的工资除该用的之外,剩下的全进了表姨的裤兜。十年过去了,为了报答曲磕巴的知遇之恩,这个表姨便和丈夫赖二合谋上演了那场罪恶的丑剧。
这种以牺牲外甥女为代价的做法也实在太卑鄙了。可大曼憨啊!她蒙受了天大的委屈,欲活羞耻,欲死不甘,她只得吞下这颗苦果。
曲磕巴年近半百娶了个18岁的山东黄花大姑娘,一时在蛤蟆沟林场产生了轰动,也让一些男人嫉妒和垂涎。大家都逗他,说一头老牛啃上了嫩草,当然更多的人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些,曲磕巴听了都不急,总是笑呵呵地回敬说:“你有、有能耐也去、去找一个。”时间长了,人们也开始逗大曼了。大曼开始见人抬不起头,等她渐渐地熟悉了这蛤蟆沟林场的环境也就入乡随俗了。
大曼能干,劈柴挑水烧火做饭,喂猪养鸡,下地种田。另外,农闲时采磨菇、木耳、猴头、蕨菜、黄花菜等等,任劳任怨。可是当她知道自己受骗而屈就于曲磕巴之后,也和表姨当初一样恨从中来,决意报复曲磕巴。怎么报复呢?离婚是不可能的,杀了他自己也完了。那只有一个招儿,就是养汉了,叫他当活王八。可这种自暴自弃又不是她的初衷,更不是她的性格,怎么办呢?
她的内心好委屈,于是她想起了他,她曾在梦中见过的那个小林。
那时时兴住公房。林场的房子有一幢房两个院子的,也有两家一个院的。由于曲磕巴是新婚,这样只能与新婚的住对门,同一个院子,共用一个厨房。按东屋的小林会计的说法,开开门是两家,关上门是一家。大曼就爱听他说这句话,何况这小林与她梦中的小林是何等的相像。都说无巧不成书,可现实生活当中也的确有那么多的巧合啊!她无限感慨,可她只能屈就于以欺骗手段霸占她青春的曲磕巴。
这两家处得很好,小林和曲磕巴上班是一个院儿,下班又是一个院儿,并且走一个大门。不同的是,小林的媳妇白静是个营林工人,大曼是个家庭妇女。两家在一起做饭也挺热闹,扯起单位的事没完没了,做好吃的都互相去送尝尝。夏天的时候,他们常在外面吃晚饭,有时高兴了就凑到一个桌上吃。曲磕巴和小林会计时常喝点酒,一老一少也不讲辈份了。可大曼年轻啊,小林25岁,白静24岁,都比大曼大。白静长得白净清瘦,是本地的农家姑娘,也很会过日子,生养了三个孩子。这两家人都朴实、热情,有事互相帮助,孩子们也成了一同嬉戏的小伙伴。
两家几乎好成一家子了,难免互相开些玩笑。一天晚饭,小林会计和曲磕巴一起喝酒,喝着喝着,小林会计说:“磕巴哥,你真有艳福,年近半百竟能娶个黄花大闺女。”曲磕巴抿了口酒说:“怎么?你、你看中你、你嫂子啦?”小林笑着说:“看中啦,你家嫂子的大脸蛋儿像只大苹果,谁见了谁不想啃一口啊?”大曼听了脸更红了,羞涩地对小林说:“去你的,俺这模样儿可不像你说的那样儿。”她虽是这样说,可内心里却是美滋滋的。白静也来劲儿了,笑着说:“小林你要是敢啃大嫂的红苹果,我就敢啃磕巴哥的抽巴梨!”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曲磕巴更不在乎这些,说:“啃、啃吧,这、这有啥,又不是谁、谁耗下的。”小林听了,放下筷子猛地探过头来趁大曼没注意亲了个正着,说:“哎呀,真是脆又甜啊!”大曼只说了一句:“鬼头,胡闹!”嗔怪地剜了小林一眼,低头吃上了。曲磕巴也骚性大发,没等白静上前,他便主动亲了白静一口,说:“真嫩!”两家人全笑了。
小林会计的确对大曼有好感。在他眼里,大曼除了憨厚朴实外,那就是她比白静丰满。自从他亲了大曼的红脸蛋之后,心里总是装着这件事。大曼也是一样,她认为小林哥哥的吻不是一般的玩笑,他们年龄相当,本该美梦成真,可命运却如此地捉弄她。她好命苦啊!为此,她常常偷偷地流泪。
有一天,白静上山栽树,曲磕巴也不在家。小林下班回来了,开开门走进厨房,他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大曼在灶台旁洗着身子,那丰满的身材很富有挑逗性。那圆实的小腿在黑短裙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白皙光滑。他痴痴地立在那里,顿时血涌全身。这时大曼也发现了他,马上停止了擦洗。此时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是多余,欲望之火就像干柈子倒上柴油,熊熊燃烧起来了。他们相拥了,亲吻着,表现得无比贪婪、紧张和忘我,彼此都在战栗中呻吟着……尤其是大曼,她像一头初次发情的母牛,让欲火烧得疯狂,冲破了旧礼教的樊篱,一任心上人的摆布……
大曼摸着小林的头含着热泪说:“以后再不能这样了,俺对不起白静,你以后心中有俺,俺就知足了。”
此后,两家人平常的欢笑不如以前了,这是小林和大曼偷情后的一种愧疚心理在作怪。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小林家三个孩,大曼生了五个。小林两口子双工资,大曼只靠磕巴一个人。再像以前那样两家同桌就餐是不可能的了。大曼家成了林场的困难户。一次,大曼的儿子打坏了小林儿子的眼睛,白静急了,骂大曼惯孩子。大曼狠狠地打了儿子一顿,可白静还是记了仇。曲磕巴和大曼一商量,决定向场部申请新房。曲磕巴跟阚场长说了几次也没动静,可大曼去找,只一次就成功了。后来大曼见阚场长好说话,一有困难就去找他,什么困难补助啦,什么救济粮啦,只要大曼出马,一切绿灯。那时的大曼被孩子累得不像个样子,家里的活也拿不上来了,屋里屋外一片狼藉,又脏又臭,谁也不愿上她家串门。她也破罐子破摔了,学会了抽烟,串门子,当然也去找阚场长,因为阚场长总是不断地“照顾”她。小林见她变得这样邋遢,不可救药,也就不理她了。她呢,也从不找小林的麻烦。
改革春风吹满地,蛤蟆沟的林场工人种上了地。由于多年的滥砍盗伐,山林损害严重,林业自然不景气了,年年发不下工资,只好让林场工人们开荒种地,暂时不收税,顶工资用。
曲磕巴本来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你让他种地那就好比让他搬山。他说:“我连老、老婆孩子都、都养活不起,还养、养地?”大曼说:“俺也种不了地,那咱们种树吧。”曲磕巴笑道:“笑话,守、守在林、林子里,种、种哪门树、树呢!”大曼说:“俺种松树苗,不省劲吗?”曲磕巴说:“你说、说咋整就、就咋整,反正我、我是没工、工夫。”大曼说:“你做豆腐还行,解决口粮不成问题。”曲磕巴说:“我起不了早。”大曼说:“俺能起早,你晚起来帮一下,然后你卖。”曲磕巴只好答应了。
他们说干就干,松树籽是自己采来的,不花钱,很快就播上了。家里支起了磨,做上了豆腐。几年之后,树苗长得尺把高,曲磕巴的豆腐也卖出了名。曲磕巴一点也不笨,不仅能做出一手好豆腐,还是一个围棋高手,他还代表林业局参加过全县比赛拿过第三名呢。
树苗可以卖了,附近城镇都争着抢着买大曼的树苗,这下他们可发了,一下赚了三万多元。当时的林场,一个万元户就吓人一愣,三万块,真让人眼红。曲磕巴家里不仅盖了房子,五个孩子也穿上了好衣服,而且都能读上书。
当然,作为林区致富典型,他们家很快就受到了宣传媒体的关注,县里记者前来采访,曲磕巴和大曼双双上了电视和报纸。
曲磕巴从此穿上了皮鞋皮夹克,吸上了香烟,走在街上经常哼上几句《沙家浜》: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总共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
多亏那阿庆嫂将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
有人打住他说:“磕巴哥,你唱得不对,你是多亏磕巴嫂种树苗使你富有了腰杆壮,是吗?”曲磕巴说:“是是,这、这个我承、承认。”说着从兜里掏出两个桔子:“给,兄、兄弟,吃、吃一个。”那人接过吃上了。曲磕巴说:“说、说实在的,我不是说光、光溜话,还是党、党的政策好、好,要不我、我还得赶、赶串去,就差、差老婆没、没离婚了!”那人点头道:“良心话,良心话啊!”有了钱的大曼打扮上了,穿戴干净整齐了,苹果脸更红了,体态仍是丰满,走在街上,不管见了谁都笑呵呵的。一天,阚场长去了苗圃,看见大曼正撅着滚圆的屁股拔大草,他便悄悄地走了过去,色迷迷地盯住她。他见四周无人,便在背后抱住了她。大曼回头一看是他,拿起蒿草向后猛抽,抽得阚场长捂着脸走开了。只听大曼在后面骂道:“姓阚的,你狗日的听着,你以为俺还是当年求你的俺呢?老娘那时是没办法才走了下道。从今以后,你再碰老娘一下,老娘就阉了你狗日的。”以后,那位爱占妇女便宜的阚场长再也不敢碰她了。那时,大曼刚过而立之年。
后来,大曼对表姨说:“俺知道俺命不济,可俺心里只有小林一个。”
曲磕巴知道了说:“不管你、你爱谁,你、你都是蛤蟆沟曲磕、磕巴的老、老婆!”
大曼听了,不禁勾起旧恨来,愤愤地骂道:“俺是你老婆?哼,俺是你姑奶奶!”
曲磕巴听了死乞白赖地说:“是是,你、你是我的亲、亲姑奶奶。”
大曼抹起泪来:“你们当初合伙设套儿欺骗俺,坑了俺一辈子啊!你这个不得好死的磕巴!呜……”
曲磕巴自知理亏,便扭过头装哑巴了。可他想不通的是,穷对付的日子,大曼也哭闹过,他能理解,可今天日子过好了,她又伤哪门子心呢?
大曼也不做饭,曲磕巴也没办法,起身溜到赖二家打麻将去了。
这一年,蛤蟆沟林场更换领导班子,小林取代了老阚当了场长。
大曼和以前一样经营着自个儿的苗圃,另外也种些庄稼,又廉价,又省力气,一年收入一两万,仍是全场首富。
有钱了,曲磕巴旧病复发——赌钱。开始几年,曲磕巴怕大曼,小打小闹玩玩,没想到越玩儿越上瘾,越玩儿越大。其实,这事儿还是赖二两口子鼓捣的。他们见曲磕巴的腰包鼓起来了,要多眼红有多眼红。再说了,以前曲磕巴领了工资是往他们赖二家送,可现在呢?他们心里很不平衡。本来赖二两口子就心术不正,这回又打上了坏主意。于是,他们勾搭曲磕巴玩麻将,带上了刚掉蛋的阚场长。和这几个饿狼一起赌,曲磕巴自然是输多赢少。他也不在乎,嘴上常说:“不就是几、几个小钱嘛,小、小意思。”曲磕巴赌上了瘾,索性豆腐也不做了,活儿几乎全交给了大曼。
开始,大曼以为他已六十开外,身子骨差了。后来发现他成天成宿地玩,也不见回收。另外,儿子大军惯得没个人样儿,家里的零花钱说没就没,拿出多少没多少,不到一年,零用钱就花了一万多。此外,她表姨赖二媳妇买四轮车和大犁,借去一万元,三年了还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大曼火了,于是拴驴卸磨,豆腐黄铺了。她疯疯火火地跑到赖二家扌周了麻将桌子,弄得赖二两口子和老阚下不来台。
大曼揪住曲磕巴骂道:“曲磕巴,你这个老混蛋,你不能挣钱,祸害人倒能耐,你以为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呢?让你上这儿来打水漂儿啊?你不得好死!”
大曼一气把曲磕巴骂个狗血喷头,翻着蛤蟆眼没有嗑了。
赖二夫妻听了明知道大曼骂人是一箭双雕,他们内心有愧,不敢声张,只有老阚上前说两句,结果让大曼一阵抢白,马上就瘪茄子了:
“好好,我也不是块好饼,我滚犊子!”老阚穿上鞋溜了。
大曼借着火气对表姨说:“你们都在这儿,俺家那一万块钱该还了吧?大军当兵马上得用钱呢!”
表姨尴尬地说:“大曼,这事儿,这么着,明年一定还!”
赖二也附和道:“明年一定还。”
大曼爱面子,只好说:“那好,明年不还,俺可要算三分利息!”
赖二夫妻忙点头:“行、行。”
从此,曲磕巴打麻将少了,可他的儿子大军又出事了。
大曼给曲磕巴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姑娘一个小子。儿子大军是第三个孩子,初中没毕业,18岁的他整天游手好闲,交些酒肉朋友,还有个乖女孩花枝招展地天天缠着他。你说这乖女孩是谁?是阚场长的四闺女,他的同学!曲磕巴以为儿子有能耐,根本不在意,后来大曼发现不是好事儿,明白那阚四闺女是冲着曲家的钱来的,时间长了儿子肯定弄个鸡飞蛋打不可。于是决定让他当兵锻炼,出息出息,回来还能分配个工作。可现在当兵不容易,必须上下打点好,否则拿不到通知书。曲磕巴开始不同意,他认为只有这一个儿子,应该留在身边。大曼说儿子是个败家子,会弄得跟他老子一个样儿,更危险。于是,儿子当兵的事儿定了下来,一万块钱由大曼亲手交到了主管人员手中。
大军当兵是个光荣的事儿,人们看到穿上军装的坏小子也变了样子,免不了称赞几句。大军心里美滋滋的,曲磕巴和大曼也很高兴,觉得儿子当兵确实能出息人。谁承想在临走前一周里,大军挎着阚四闺女在街上招摇时把挑逗四闺女的王三踢坏了。踢在哪儿?正是男人的要害处。人家要上告,被大曼拿一万块钱把事儿压住了,否则,大军的兵也当不上了。
大军走了,大曼一个人哭了好几天,她心疼那两万块钱啊!曲磕巴却不在乎,摇身一变成了军属,光荣得天天去赖家玩麻将,根本不理解大曼那颗已经苦透了的心。
这一天,曲磕巴天亮才回来,回来就睡觉。大曼忍无可忍,一把将他拎起来,打了两记响亮的耳光,哭骂道:
“曲磕巴呀曲磕巴,你这个没出息的败家鬼,八辈也看不见后脑勺啊!你们爷们儿没有一个好东西呀!俺辛辛苦苦挣的钱,都让你们爷们儿给糟蹋了!呜——俺命苦啊,俺这是在猪窝里和你们骨碌啊!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畜生,总有一天,要遭报应的!呜——”
曲磕巴自知理亏,他知道自己已是年近七旬的糟老头子,而自己要啥啥不行,还有许多坏毛病,只好忍耐,任她发泄。
大曼出了气,哭够了,出去干活了。
晚上,曲磕巴突然提出要去市里医院看看病,怀疑是腰间盘突出。大曼骂道:“活该,这是你玩麻将玩的,报应!下一步就是股骨头坏死,你等着瞧吧!”骂是骂,气是气,她还是拿出钱让他去了。
曲磕巴心想:“这回我可出去逛一逛花花世界,散散心。”
大曼心想:“走了好,最好永远别回来,俺就可以……”
大概是在曲磕巴走后的第五个中午,大曼在苗圃里独自一人开池放水浇树苗。清澈的井水在池子里流着,树苗整齐茂盛。大曼坐在松软的草地上看着。蓦地,她又想起这半年来连串发生的烦心事儿,泪水不禁又流了出来。阳光照得她浑身慵懒,她抹了一把泪水,索性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她望着蓝天,觉得天那么深邃空阔,她恨老天捉弄人,将她配给曲磕巴,她恨表姨太肮脏下流,为了自己而牺牲外甥女的青春年华,真是隔层肚皮隔层山,要是亲姨是绝对不能这么损的。她又觉得自己前世可能做了许多坏事,到了今世才受到如此的惩罚。她每天都看电视连续剧,经常被一些恋人的恩爱情节所打动。于是她心里总装着曾有一时之欢的现任场长小林。磕巴看病去了,她盼望小林来,可一连四天过去了,她失望了。
躺在草地上,一对百灵鸟在她头上自由飞翔,婉转地唱着;一会儿又有一对蝴蝶追逐着翩然而至。她羡慕极了,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着看着,于是又想起了小林,想着想着也就入睡了,脸上带着愉悦和满足。
小林真地来了。她睡意朦胧中觉得有人亲她的脸儿,咬她的唇……醒来一看果然有个男人,刚要发作,见是小林,惊喜道:“怎么真的是你?”
小林笑着说:“是我怎的,你不喜欢?”
大曼当胸捣了他两下,说:“该死的,你怎么刚来,想死俺了!”说完便猛地将小林拢在自己怀中,仰在草地上……
鸟儿的叫声远去了,蝴蝶也惊飞了,只有蓝天与白云凝滞在那里……
“今晚上到俺家,俺给你留门。”大曼命令道。
“不行,今晚我值班。”小林说。
“不行,今晚咱们一定做回真正的夫妻!”大曼生气了。
“那好,由着你。”
大曼乐了,乐得像个小孩子,泪水又流了出来。
小林给她擦眼泪:“别伤心,一切都会好的。”
“昨天我才知道磕巴去市里看病,要不我……”
大曼趴在他的肩上说:“十年了,俺觉得你该来啦,再不来,俺也该死了!呜……”
晚上,也就在这天晚上,一件出人意料事发生了,轰动了这沉寂而蛮荒的蛤蟆沟林场。
原来,那天晚上大曼和小林睡在一处,却被半夜回来的曲磕巴撞个正着。曲磕巴傻了,没等他磕巴出个一二三来,就被十分沉着的小林场长摆手打住了。小林围着被子点上了一枝烟,大有当年曲磕巴侮辱完大曼之后的沉着,说:“别惊动别人,曲大哥,事已如此,我们好说好商量。”曲磕巴看在他是场长,还是老邻居的面上,也沉静下来:“说、说吧,反正大、大哥也戴、戴上绿帽子了。”小林说:“大哥,咱们这么着,你知道我喜欢大曼,我也知道你喜欢白静。”“这又能、能咋的?”“咱们这样好不好,我和大曼已经这样了,可以说无法挽回。我看你莫不如现在就到我家去,就说是我叫你来的,这样咱们两个也就一了百了,怎么样?”曲磕巴听了,内心里马上淫荡起来,说:“这、这能行吗?”小林说:“我是她丈夫,我又是一场之长,在咱们蛤蟆沟天老大,地老二,我是老三,咋个不行?去去,白静正等着你呢!”真没想到,曲磕巴真地去了,不是他智商不够用,而是他色令智昏。因为过去他就动过此念头,可一直没敢付诸行动,今天可是天赐良机,捉了小林和大曼的奸,有了把柄,乐得他不能自持,便很顺利地进了小林的屋,摸到了睡得正香的白静的身边,脱了衣裤就钻进了被窝……没想到,白静被他扰醒翻了脸,开始以为是小林,后一闻气味不对,就大叫起来。曲磕巴一急也解释不清,忙拿起衣服,连裤子也没穿便逃了出去。白静大喊大叫,左右邻居惊醒了,马上报告了派出所。
当曲磕巴跑回自己家时,发现小林不见了,才知道自己吃了哑巴亏。
小林是让邻居们从林场场部办公室里找回来的,白静哭着诉说经过。公安人员很快将曲磕巴逮走了。
曲磕巴以强奸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有人说可以用钱保释回来,大曼说不行,这是天老爷对他的惩罚。于是,大曼提出离婚,并及时办了手续。从此,大曼不管别人说什么,总是扬眉吐气,理直气壮的样子。是啊,二十多年的委屈,人们平时的惋惜啊,嘲弄啊,总算有了收尾。
就在曲磕巴入狱的第三天,大曼闹到了赖二家,要回了那一万元欠款,并将他们的丑事抖了出来,狠狠地教训了这对狗男女,受到林场上下的一致赞成。
六月花开的一天,大曼从银行里取出仅剩的六万元存款,扛着一袋树籽,领着两个小女儿回了山东老家。临上车,她哭着向送行的邻居们说:“俺们山东老家富了,再也用不着闯关东了!这些年俺就像做了一场梦啊!”
听了她的话,蛤蟆沟的乡亲们都落了泪。
大曼走了,林场的人们好像失去了什么,特别是连续三年受灾,先旱后涝又闹虫灾,庄稼庄稼全毁,树苗树苗全淹死。人们不时地念道:“大曼在时咋不这样呢?”
可是,大曼走了,八年了,再也没有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