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人间
拓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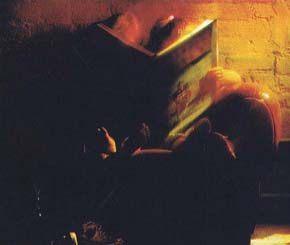
600年前,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率一支庞大的舰队,开始了七下西洋的壮举。历时多年,七次进出大海的风风雨雨,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
1994年,美国作家雷瓦西为中国人郑和撰写了一部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书中讲到作者自己的一段经历:有一次在非洲的肯尼亚,一个黑人告诉雷瓦西,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肯尼亚帕泰岛中国船难事件幸存者的后裔。1999年,《纽约时报》记者为此专门探访了肯尼亚帕泰岛,试图寻找与当年郑和船队有关的遗迹。可惜经数百年岁月风雨的冲刷,他们没能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最后推想:那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极有可能就是郑和部下的后裔。
今天,我们只能通过报刊书籍,在阅读的过程中默想,那一次次的惊涛骇浪,怎样拍打船栏。一个帝国的使者,又是怀着怎样的执着,要让足迹印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当600年后有不同肤色的人自称是中国人的子孙时,那一脉从华夏大地伸出的枝叶,早已经淡陌了故土的印痕,化作他乡的一棵棵大树,守望着相同的一片海。
因为时光匆匆,因为桑田沧海。
当我们东望大海的时候,目光总会读到日本。而日本人据说是最爱读书的。日本每年出书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亚洲其他国家。除了传统阅读,日本的年轻人近来又兴起了手机网书阅读。据《产经新闻》2003年底的调查,当时的日本,已有200万人成为手机网书的读者。
与传统书籍相比,手机网书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携带方便,比如随时随地可以阅读等等。因为可以即时掌握读者的阅读信息,网书经营商可根据读者对某一作品的兴趣,来决定该作品是否继续刊在网上。这也使得作家们常常处于紧张状态,时刻注意市场动向。
在中国,似乎通过手机阅读的现象还不是十分普遍。缺少了一份厚重,缺少了一页又一页的翻开,于传统的阅读者来说,总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如同网络间的通信往来,总是比传统的鸿雁传书少了期待和浪漫。培根说,读书之用有三,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海德格尔的说法则是:阅读,使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即便是今天,仍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阅读,从而带给人们一个奇妙而充实的世界。有报道说,恐怖小说眼下在校园学生和公司职员中十分流行。这与成长的过程渴望冒险的体验以及商品时代人们需要另类的刺激来减轻虚幻的感觉有关。
我们在阅读中试图去理解郑和和他的同伴们。在郑和时代,中国曾作为一个帝国称雄海上。而在郑和之后,110年前的那一场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胜利者正是日本人。风吹过,仿佛还听得到帝国兴亡的鼓角轰鸣。
日本人爱读书,但似乎总有人不愿意面对历史。而我们不会忘记的是: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