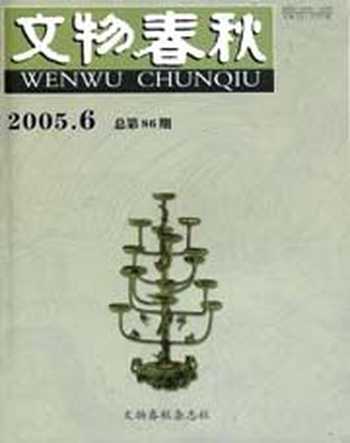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下)
卫 奇
【关键词】萨拉乌苏河;旧石器考古;旧石器时代;考古史
【摘要】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的重头戏,“河套人”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曾经以“三步曲”长期掌控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舞台。萨拉乌苏河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历经将近一个世纪,地层和古人类学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然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却进展甚微,特别是有关考古术语的畸形演化,突显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不甚严肃的科学作风。本文对这一历程的充实期和综合科学研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作了回顾性研究。
四、充实时期

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汪宇平(图四)在萨拉乌苏河曾经进行过两次考古调查,1957年发表简报[31]。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发表的一篇非常有意义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报告,它的重要性在于:(1)在萨拉乌苏河新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2)发现了2件人类化石;(3)首次用中文科学地记述了萨拉乌苏河的地貌概况。在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如果说桑志华是一个贡献卓越的开拓者,那么汪宇平无疑是一个成绩显著的继往开来的学者。据汪宇平的调查报告,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发现在大沟湾的西沟,即范家沟湾(图五),获得石制品76件,还有烧骨和哺乳动物化石,并且在萨拉乌苏河阶地中发现了1件右侧顶骨和1件左股骨远端部分的人类化石。吴汝康研究指出,新发现的顶骨和股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又“接近于一般的现代人”特征,由于“化石石化的程度很大,发现的地层可能是更新世晚期,汇集各方面证据,可以确定这些河套人类化石代表晚期的尼安德特人类型”。“从顶骨和股骨的结构较一般化的事实来判断,中国的古人(尼人)阶段的人类化石的形态可能比西欧典型的尼安德特类型的人类更为接近于现代人,也就是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自然,目前在我国发现的古人阶段的人类化石还很稀少的时候难于作出结论,但是这种推断完全是有可能性的。”[32]
1956年,中国地质学编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首先将发育在萨拉乌苏河流域的巨厚河湖相地层称之为“萨拉乌苏河组”[33],后来1959年出版的《中国地层名词汇编(草案)》也收入了“萨拉乌苏河组”这一术语。
1962年,汪宇平在萨拉乌苏河第二级阶地河流堆积层中发现一具相当完整的人类头骨,它的石化程度不高,其形态特征在现代人范围之中[34]。
1963~1964年,裴文中、张森水和汪宇平等组成科学调查队,在萨拉乌苏河地区开展第四纪全面考察,于陕西省横山县雷惠农场石马坬村发现一具成年人的头骨化石。化石发现在河流第二级阶地的全新统中,地层中含经过磨蚀的灰色陶片。人类化石呈黄褐色,骨壁较厚,石化程度大,同时出土的还有巨驼、大角羊、羚羊和鹿。报道者认为,头骨“骨质全部石化,呈黄褐色,重量较大;从石化程度来看,它与‘萨拉乌苏河系的化石相同(如巨驼标本),与附近发现的现代的或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骨骼有显然的区别。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暂时可认为它是属于‘河套人的。”[35]裴文中等经过调查和发掘,发现一批脊椎动物化石,经祁国琴研究,新增加的种类有虎和斯氏高山鼠相似种[36]。

1964年,裴文中和李有恒发表文章[37],以“萨拉乌苏河系”全面论述了陕北和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及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含旧石器的类黄土堆积,并且对于它们的地层术语、岩相、结构、分布和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裴文中等认为两地的地层复杂而多样,似乎应该用“系”来表示,不应当用建造或层、组之类的术语。过去“系”应该是现在“群”的规范术语,其“建造”规范为组。他们认为水洞沟地区和萨拉乌苏河地区地层发育的时间和背景相同,所以从地质上可以看作是同一地层,因此,水洞沟的地层是可以列入萨拉乌苏河系的。但是,从发现的动物化石和石器来看,水洞沟地区和萨拉乌苏河地区在晚更新世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差别,就石器和人类生活的环境来讲,两者可能不含有相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他们根据当时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后人研究。其文章最大的缺憾是将萨拉乌苏河的基座阶地误认为是上迭台地,从而导致图中地层结构的严重失误和对于萨拉乌苏河河谷发育过程的认识不足。因此裴文中在北京大学为1960届地貌学专业做关于萨拉乌苏河的专题讲座时说:披毛犀从高原面上下到萨拉乌苏河喝水的时候被淹死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报告,在萨拉乌苏河下部地层“为水平层理的砂层,中有胶结的薄层砂层,也夹有较薄的泥灰或粘土层,其中含化石甚多,且有完整的骨架或未解体的骨骼(带有皮毛者)。这些化石包括大骆驼、马和披毛犀等,肯定是更新世者,应属于萨拉乌苏河系,且不是由附近搬运而来,应为原生者。”笔者曾经在汪宇平指引下确认过这个盛产动物化石的地点,但是对于萨拉乌苏河岩系的地层发现化石上“带有皮毛者”实在难以理解。
1964年,刘东生等论述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问题时,用了“沙拉乌苏组”、“沙拉乌苏动物群”等术语,并且将“沙拉乌苏组”置于上更新统下部[38]。从此以后,“萨拉乌苏河”在地质学界一般简化成为“萨拉乌苏”。
1965年,安志敏在小南海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报告中,将萨拉乌苏河的石器置于水洞沟和小南海的石器之间。他认为,小南海文化和萨拉乌苏河文化相似,属于不同地区的两种文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石器比较进步,甚至于还出现类似细石器的遗存,又揭示了它们可能是中国中石器及石器文化的先驱[39]。

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察队,考察了萨拉乌苏河(图六)。汪宇平带领大家参观了他发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和人类化石地点,明确了人类顶骨和股骨化石出自萨拉乌苏河的阶地堆积层中,并且查明萨拉乌苏河的高阶地含宋代瓷片,初步判断萨拉乌苏河的发育历史很短,大约为1000年。
贾兰坡、盖培和尤玉柱根据萨拉乌苏河动物群包含中更新世常见的古菱齿象的现象,认为其年代可能早于峙峪和小南海遗址。他们认为萨拉乌苏河的旧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另称“第一地点”—峙石器属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周口店第一地峪系”),或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他们将萨拉乌苏河遗址和峙峪遗址并列在后一传统系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40]。
1977年,张森水将萨拉乌苏河发现旧石器的地点称之为“大沟湾”地点[41]。
1978年出版的《华北区域地层表(内蒙古分册)》将萨拉乌苏河一带的上更新统河湖相地层确定为“萨拉乌苏组”[42]。
贾兰坡和王建在《西侯度》研究报告中所称的萨拉乌苏文化,也归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文化系统[43]。邱中郎和李炎贤提出:“过去把水洞沟、内蒙乌审旗大沟湾以及甘肃庆阳黄土底砾层中,陕西榆林黄土中发现的石制品,合在一起称为‘河套文化,这是很不恰当的。这些地方发现的石制品并不相同,特别是水洞沟和大沟湾两地点的石器差别较大,而且这些地方发现的东西时代可能有早晚的区别。”[44]
1978年,袁宝印在《地质科学》杂志上发表《萨拉乌苏组的沉积环境及地层划分问题》,首次正式科学地揭示了萨拉乌苏河的河谷地貌,并依据地层、古脊椎动物、旧石器、孢粉以及沉积物理化性质的分析指出,萨拉乌苏河流域存在凸岸基座阶地和主岸(即凹岸)两类堆积。凸岸基座阶地的形成时代最早不过2000年。主岸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三组地层:全新世早期大沟湾组,晚更新世晚期萨拉乌苏组上部,晚更新世中期萨拉乌苏组下部。其中萨拉乌苏组与黄土区马兰黄土的时代相当,二者同期异相;而同马兰黄土底砾层相当的晚更新世早期沉积以丁村组为代表,在本区尚未出露。他认为,晚更新世早期气候干冷(相当于里斯冰期);晚更新世中期,鄂尔多斯东南部迅速下沉,气候暖湿(里斯—玉木间冰期),本区开始形成许多湖泊,至后期出现统一大湖;晚更新世晚期,气候变为干冷(玉木冰期),出现以河流堆积为主的时期,周围可能同时存在沙漠,但也有过两次短暂的雨量稍多的湖沼相沉积期;全新世早期,气候转为温和湿润(冰后期),出现统一大湖,以后因新构造抬升或气候变干的影响,湖泊很快消失,形成现在的荒漠草原景观[45]。袁宝印的研究是继桑志华和德日进之后,对萨拉乌苏河科学研究的再一次全面创新,完成了一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重大科学转折。

五、综合科学研究时期
1978~1979年,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董光荣、高尚玉和李保生等在鄂尔多斯高原探索毛乌素沙漠的形成时代和演变历史,对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了长期且广泛的第四纪地质调查和研究[46],其中将研究基点放在对该区150kaB.P.以来的上更新统—全新统的认识上。调查期间,在萨拉乌苏河发现6件人类化石,包括2件完整的额骨、1件额鳞残片、1件小孩下颌骨右侧部分、1件右侧股骨和1件左侧胫骨。除了1件额骨和1件股骨发现时已经脱层或含于次生地层外,其余4件均发现于原生地层萨拉乌苏组下部的层位里[47],从而解决了多年来河套人出土地层不清楚的问题。
1979年出版的《地质词典》,以规范科学术语的形式确定了“萨拉乌苏组”、“萨拉乌苏动物群”、“河套文化”,并且提及“河套文化”的另外别名“萨拉乌苏文化”和“大沟湾文化”。“河套文化”不包括“水洞沟文化”,而且前者比后者时代稍晚,石器制作水平稍高,具小石器文化的特征[48]。
1980年,在董光荣的策划下,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今与原冰川冻土研究所合并为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单位在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了综合考察(图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由贾兰坡挂帅,黄慰文带领卫奇和刘景芝到萨拉乌苏河调查发掘。7月30日开始发掘汪宇平发现的范家沟湾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卫奇和刘景芝执行发掘。发掘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星期,出土石制品130多件[49],其中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发掘结束后进行了人类化石地点的核查和调查,前后新发现人类化石11件,包括顶骨1件、枕骨2件、下颌骨2件、椎骨1件、肩胛骨2件、肱骨1件、股骨1件和腓骨1件。8月中旬,田野工作基本结束,考察队员开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与贾兰坡等会合,参观了水洞沟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然后返回萨拉乌苏河采集样品。在室内研究中,发现1922年桑志华采集的PA62号人类股骨远端髌面生前被磨损,这是骨关节炎病症的一种反映[50]。
1982年,董光荣和李保生提出,袁宝印定名的“萨拉乌苏组上部”是一套以风成的细砂为主的堆积,应更名为“细砂组”[51]。1983年,董光荣、李保生和高尚玉又将其改名为“城川组”,提出“萨拉乌苏组下部”才是一套以河湖相堆积为主的萨拉乌苏组[52]。
1983年,原思训、陈铁梅和高世君用铀子系法测定河套人和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指出萨拉乌苏河河湖相沉积层的时代不早于晚更新世中期,其上部距今不超过3万年,下部为距今3~5万年。根据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出土层位判断,“河套人”和“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应为距今3.7~5万年左右[53]。
1984年,黎兴国等报道,范家沟湾旧石器时代考古地点文化层的炭屑以14C测年方法测定为35?熏340±1?熏900年B.P.[54]。
1986年,董光荣和李保生综合多方面的科学资料,对萨拉乌苏河地层进行了详细划分和全面分析,提出萨拉乌苏河一带的地层层序(从下到上)为:中更新统老黄土—上更新统下部萨拉乌苏组—上更新统上部城川组(包括下、中和上三段)—全新统下部大沟湾组(包括下和上二段)—全新统上部滴哨沟湾组[55]。
1989年,黄慰文将萨拉乌苏河发现的石制品置于小石器传统[56]。吴茂霖认为,河套人的时代晚于大荔人、许家窑人和丁村人,而早于峙峪人和山顶洞人[57]。祁国琴指出:“萨拉乌苏河动物植物群反映河套人生活在与今相当(或少偏凉爽)气候下兼有森林和草原的环境中。”[58]
1990年,吴新智也将萨拉乌苏河发现的人类化石归于晚期智人,并且应用了“萨拉乌苏”和“Salawusu”术语[59]。
1991年,盖培提出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三个石器组合:石叶组合、石片组合和细石叶组合。他将萨拉乌苏河置于细石叶组合的许家窑之后和峙峪之前,然后继续发展成南系和北系两个系列[60]。
1998年,董光荣、苏志珠和靳鹤龄对萨拉乌苏河地层的时代提出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属于河湖相的萨拉乌苏河组形成于140~70千年前,以风沙建造为主的城川组形成于70~10千年前,属于湖沼相的大沟湾组形成于9.7~3.8千年前,而跌哨沟湾组形成于3.8千年前以后[61]。不过,黄土—古土壤序列与萨拉乌苏河的沉积层的对比,必须考虑不同地貌单元上的岩相变化。
2001年,张守信对中国地层名称做了进一步规范,将“萨拉乌苏河组”录入其中[62]。但是,萨拉乌苏河的英文名称记录为“Salawusuhe Formation”。按规范的中国地名拼音规则,在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非汉语地名的拼音文字应该分别用蒙古语、维吾尔语和藏语拼写。
2001年,中国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榜上有“萨拉乌苏遗址”。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如果不是有意将“萨拉乌苏河”简化为“萨拉乌苏”,那么就是对萨拉乌苏河研究历史了解的一个失误。
2003年,黄慰文和侯亚梅发表文章,正式报道了1980年范家沟湾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文章中观测统计的石制品一共192件,包括石核10件、石片130件、石器52件,并进行了传统式记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范家沟湾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出现了真正的细石核(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旧石器编号:P.5419),“工作面上保留一系列相互平行的细石叶疤痕,显示出明确的压制技术印记”[63]。另外,文章提出:“因为后来的中文文献把‘Ordos误译成‘河套,‘河套人于是成了中国化石人类家族中的一员。其实,鄂尔多斯与河套并不相干。”显然,文章的作者阅读文献时有疏漏,“Ordos”伴随着人牙的发表一开始就译成了“河套”。后来裴文中赋予“Ordos tooth”为“河套人”中文名称的同时,对“河套”有明确的注释[64]。如果查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现代汉语词典》以及《辞海》中关于“河套”词条的解释,就会一清二楚。研究者重新定名“鄂尔多斯人”、“萨拉乌苏石器工业”,还正式出现了“萨拉乌苏遗址”和“Salawusu site”。类似的创新在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屡见不鲜,因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没有明确的定名规则,遗址或地点取名或依据行政区划,或按照自然地理,或其他。依据行政区划,“河套人牙”代表的应该是“邵家沟湾人”,或“大沟湾人”,或“萨拉乌苏河人”,或“乌审旗人”等等。
2004年,尹功明和黄慰文用光释光方法测定范家沟湾旧石器地点的年代为:61±4.9~68±7.3kaPB[65],从而又为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
同年,黄慰文、董光荣和侯亚梅发表了《鄂尔多斯化石智人的地层、年代和生态环境》。文章立意新颖,可是由于研究手段的原因,作者以过去地层、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孢粉和岩石结构的分析资料,再次采取时间和空间混合处理的方法表述其有关内容,尚未对所述出人类化石的地层逐一采样细致分析。文章中报道的人类化石6件标本分别发现于萨拉乌苏河南北大约2公里的范围内,在地层剖面分布于“萨拉乌苏组”下部至少有25米的垂直距离。厚度40余米的“萨拉乌苏组”岩相变化明显,其人类化石所在之地层至少有“层”的区别,或许存在“段”的差异,它们的年代无疑有先后之别。然而文章对于人类化石的地层缺乏准确交代,其年代缺少精确测定,生态环境的叙述仍然停留在地质学家们过去有关的研究资料之中。文章中将河套人称之为“鄂尔多斯化石智人”,并特别强调:“过去,‘Ordos在一些中文文献里被误译成‘河套,实则应译为‘鄂尔多斯。因为‘鄂尔多斯与‘河套……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因此,依照学术命名规则,……应根据化石原研究者的本意用‘鄂尔多斯取代‘河套人。”[66]按照文章作者的建议,因为1927年桑志华等发表“the Ordos tooth”时已经将“Ordos”译作“河套”,所以“Ordos”应该译作“河套”而不应该是“鄂尔多斯”。显然作者把地理学上的鄂尔多斯和行政区划上的鄂尔多斯混为一谈了。从科学命名优先的规则考虑,如果不是非改不可的错误,应该尽可能尊重前人,特别是发现者或报道者的意愿。
最近,为了弄清1923年桑志华发现的人类股骨PA62号标本的确切年代,卫奇征得吴新智院士的同意,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批准,曾经在标本的指定部位切割了1.5cm2,分成2份,一份经英国人Susan Keates介绍,寄给俄国Y.V.Kuzmin送到美国亚利桑那(Arizona)大学AMS实验室,另一份送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年代测定实验室吴小红,她在德国基尔大学加速器质谱和同位素实验室完成样品的制备和测量工作。测定结果,其年龄距今只有300年左右。贾兰坡说:“大腿骨的颜色与萨拉乌苏河发现的动物化石颜色颇为相像,并没有区别。”[67]标本保存良好,说明标本在埋藏前和出土后,暴露时间极为短暂。如果标本出自顶部黑色的草原层,它的颜色应该是黑色的。的确,标本已经具有轻微石化。如果PA62号人骨标本的年代测定无误,那么它的出土层位应该在萨拉乌苏河阶地地层。然而,在阶地地层中曾经发现过不少现代人类的肢骨,其颜色、重量和质感方面均与PA62股骨明显不同。如果标本是出自萨拉乌苏河组或城川组,那么其年代测定就存在一定问题,或许标本受到了后期的严重污染。
六、小议
过去的事实是现在的历史,现在的过程必然成为将来的历史。我们回顾历史不是指责前人的错误和缺点,而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健康地发展当今的考古事业。学术研究就是弥补科学的空白和修正不足。所以,科学研究永远是创新行为。
我们熟知前人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缺憾。我们今天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应该借鉴历史来思索如何创造未来的历史,负责任地考虑我们为后人遗留些什么,至少要有科学环境的保护意识,尽可能少地制造科学垃圾。
萨拉乌苏河的科学研究历史实为光辉灿烂的一页。萨拉乌苏河的科学研究,成果巨大而辉煌,但是,有些不应该出现的问题一直不为人们所注意,例如:“萨拉乌苏河”简化成“萨拉乌苏”,“Sjara-osso-gol”变成“salawusu”,“河套人”易名为“鄂尔多斯人”,还有“萨拉乌苏河工业”、“萨拉乌苏河文化”和“河套文化”,“萨拉乌苏河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和“大沟湾”地点等等,这些看来很好解决的问题,现在依然难以解决。因为在中国古人类学界随便定名司空见惯,而且高规格的出版物以及有地位的科学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常常有染。
笔者建议,“萨拉乌苏河”应该正名,保留“河套人”、“河套文化”、“萨拉乌苏河工业”等术语,发现的遗址分别以“范家沟湾”和“杨四沟湾”定名。旧石器“工业”包括原材料的采集、产品加工和生产技术,它应该是由某一阶段若干遗址的石制品和骨制品等的共同特征和组合所反映。而旧石器“文化”是古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应该是由较多人类群体在相当大地域占据相当长时段所创造的带有时间和空间色彩的遗物和遗迹。“文化”和“工业”应该类似于动物分类“属”和“种”的关系,“文化”的内涵比“工业”浅,也就是说“文化”的外延比“工业”广。
————————
[31]汪宇平:《伊盟萨拉乌苏河考古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4期。
[31]吴汝康:《河套人类顶骨和股骨化石》,《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2卷2期。
[31]中国地质学编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区域地层表》(草案),科学出版社,1956年。
[34]汪宇平:《内蒙古伊盟乌审旗发现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3年7卷2期。
[35]李有恒:《“河套人”的新材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3年7卷4期。
[36]祁国琴:《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13卷4期。
[37]裴文中、李有恒:《萨拉乌苏河系的初步探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8卷2期。
[38]刘东生、刘敏厚、吴子荣、陈承惠:《关于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问题》,载《第四纪地质问题》,科学出版社,1964年。
[39]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1期。
[40]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1期。
[41]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15卷1期。
[42]内蒙古自治区地层表编写小组:《华北区域地层表(内蒙古分册)》,地质出版社,1978年。
[43]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
[44]邱中郎、李炎贤:《二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载《古人类论文集——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报告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45]袁宝印:《萨拉乌苏组的沉积环境及地层划分问题》,《地质科学》1978年3期。
[46]董光荣、高尚玉、李保生:《中国沙漠形成演化气候变化与沙漠化研究》,海洋出版社,2002年。
[47]董光荣:《河套人化石的新发现》,《科学通报》1981年26卷19期。
[48]地质部地质词典办公室:《地质词典(三)——古生物、地史分册》,地质出版社,1979年。
[49][50]黄慰文、卫奇:《萨拉乌苏河的河套人及其文化》,载《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1981年。
[51]董光荣、李保生:《萨拉乌苏河地区第四纪地层及其沉积环境初报》(摘要),载《第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2年。
[52]董光荣、李保生、高尚玉:《由萨拉乌苏河地层看晚更新世以来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中国沙漠》1983年3卷2期。
[53]原思训、陈铁梅、高世君:《用铀子系法测定河套人和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人类学学报》1983年2卷1期。
[54]黎兴国、刘光联、许国英、李凤朝、王福林、刘昆山:《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的年代》,载《第一次全国14C学术会议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
[55]董光荣、李保生:《试论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沿岸马兰黄土与萨拉乌苏组地层的关系及其环境演化》,载《青海柴达木盆地晚新生代地质环境演化》,科学出版社,1986年。
[56]黄慰文:《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载《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57]吴茂霖:《中国的晚期智人》,载《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58]祁国琴:《中国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兼论原始人类生活环境》,载《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59]吴新智:《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人类学学报》1990年9卷4期。
[60]Gai Pei:《Microblade tradition around the othern Pacific rim?押 a Chinse perspective》,载《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61]董光荣、苏志珠、靳鹤龄:《晚更新世萨拉乌苏组时代新的认识》,《科学通报》1998年43卷17期。
[62]张守信:《中国地参地层名称》,科学出版社,2001年。
[63]黄慰文、侯亚梅:《萨拉乌苏遗址的新材料:范家沟湾1980年出土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2003年22卷4期。
[64]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
[65]尹功明、黄慰文:《萨拉乌苏遗址范家沟湾地点的光释光年龄》,载《纪念裴文中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人类学学报》2004年23卷增刊。
[66]黄慰文、董光荣、侯亚梅:《鄂尔多斯化石智人的地层、年代和生态环境》,载《纪念裴文中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人类学学报》2004年23卷增刊。
[67]贾兰坡:《河套人》,龙门联合书局,1950年。
(作者单位:泥河湾猿人观察站)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