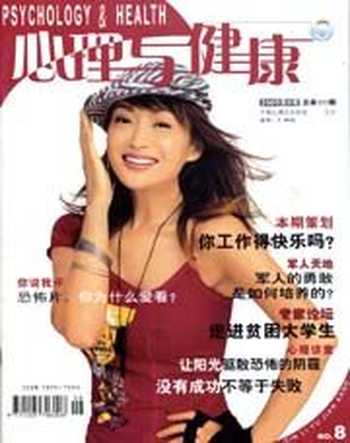让我们快乐地工作,健康地生活
梁彦蕊
1999年第1期的美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上有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焦虑的时代》。时尚健康杂志社2004年调查了北京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发现该地区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 岁。从开着大奔、宝马,过着空中飞人的老板、金领阶层,到为一日三餐忙碌奔波的芸芸众生,似乎都在承受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工作压力,人们在焦虑中忙碌,在忙碌中焦虑。工作是人一生中最重要也是占据时间最多的一个部分,我们不仅要问:你工作得快乐吗?我们还要问:怎样能让我们工作得快乐起来?
在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如同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国际劳工部2000 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工作场所抑郁症已经成为继心脏病之后最能够使员工失去工作能力的疾病。世界精神健康联合会的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行动,精神、神经和行为失调增加的速度之快足以在2020 年之前超越公路意外、艾滋病和暴力,成为早夭和失去工作能力而无法工作的主要因素。因此,工作压力与职业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充满工作压力的社会中,我们如何才能够快乐地工作,健康地生活?本人就这个问题,访问了香港资深心理咨询师、长期为企业高层管理者提供心理咨询的陈维樑博士,他就此问题提出了几点看法。
就工作压力的来源方面,陈维樑博士认为主要存在社会转型、工作变动、社会支持系统与成长环境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当今的中国社会还处在传统向现代过渡和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多元文化并存,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无处不在,人们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中显得无所适从。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来的“铁饭碗”,工作的安定感也随之被打破。
关于社会转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影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2003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因工作等原因构成的心理压力,知识分子比非知识分子高出10 %,35 岁以上人群则更为突出。在种种危机与压力下,人们开始频繁变换工作来缓解面临的压力。很多大学生毕业后“走马灯”似地换工作,有的甚至半年之内换两份工作。这样一来,原来的工作还未适应,又要适应新的工作,在工作上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另外,每换一份工作,都是打破原来的社会关系,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当做“小皇帝”、“小公主”,团队合作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相对较差,在困难面前往往退缩不前。有些人拿着高学历,嫌工作“太辛苦”,就待在家里拿社会低保或靠父母养活。目前社会上的“啃老族”、“高学历待业族”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陈维樑博士认为,在工作压力面前,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在工作中频频出差错,与别人发生冲突,责怪同事,顶撞上司,甚至跳槽。在工作之外,表现为疯狂购物、上网、打游戏等。还有的人不堪工作的重负,出现抑郁症、颈椎病、高血压等心身疾病,甚至自杀。工作压力也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美国职业压力协会(AmericanInstitute of Stress)估计,工作压力所导致的员工缺勤、体力衰竭、神经健康等问题每年耗费美国企业界 3000多亿美元。另外由于工作压力过大,有些人会急于寻求社会支持,不断更换异性朋友来填补心中的空虚。在这种心态下结合的伴侣在以后的生活中很容易出现问题而导致分手。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工作压力造成的,另一方面又会在出现问题时加重工作上的压力,这种现象在美国已经成为工作压力方面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陈维樑博士认为这些都是人们面对压力的反应,大多是不利于心身健康的。关于如何缓解工作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陈博士提出了几点看法。首先,要意识到自己应对压力的方式,人们如果作出反应之前反思一下自己的应对方式是否恰当,就不会作出种种不当反应。所以,经常静下来审视一下自己的处境,然后再作反应是非常有必要的。平时也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可以在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后作一个小结,在夜深人静时进行自我反思,每周腾出一天的时间做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可以读书、做健身运动等。其次,要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是人们应对压力的力量源泉,所以,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不要忘记经常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联系。可以经常给朋友打电话,在一起聊天,定期和家人相聚等。再有,定期出去旅游,亲近大自然。很多现代人都选择利用节假日出去旅游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方式,因为大自然的旖旎风光,人文景观的精雕细琢,乡村略带原始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人最好的心理按摩师。近年来,“森林疗法”在日本和欧美备受推崇,经常到森林里散步、休憩、呼吸新鲜空气,不但可以缓解工作压力,还可以达到治疗一些心身疾病的作用。
最后,陈维梁博士说,如果我们能够与自己,与他人,与环境,与信仰和价值观四个方面取得良好的互动,使这四个方面融合并达到和谐统一,就能够每天快乐地工作, 健康地生活,更好地享受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