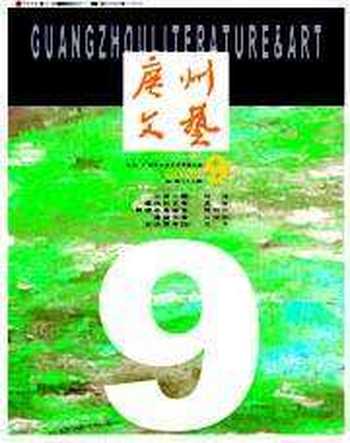县城小学飘来的歌
范晓波
气 味
我对学校最深刻的记忆不是它的建筑而是它的气味,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气味是完全不同的。县城五一小学对我而言是一种混合着橡皮和小孩汗臭的气味,它带给我的第一感受是恐惧。那时幼儿园也在小学里,从读幼儿园开始,我一直想逃出这种气味的控制。可是没有办法,我不能每天都跟外公说学校今天放假。我背着小书包和小板凳磨磨蹭蹭走在没有铺水泥的街道上,去学校做那种气味的俘虏。
校园也有其他的气味,比方说枫杨树浓厚的青气,一团一团绿云似地笼罩在头顶,在阳光暴晒的夏天它的味道浓得像流质一般在空气里蠕动。不过以我当时的身高,它离我的鼻子太远了些,丝毫不能冲淡教室的味道。我利用每个课间去捡拾枫杨树绿苍蝇般的果实,用它做弹药和同学开战,将一粒一粒的青气砸进同伴鲜嫩的毛孔。被踩出体液的甲壳虫的气味也不时地从某个角落冒出来,有些像芒果的气味,有些气味我则在成年后从巧克力里闻到过。它们星星点点散布在教室的四周,把我的嗅觉培训得比警犬还灵。新书的油墨香是我喜欢的。上课的时候我很少用眼睛看书,我使用鼻子读书,把脸埋在书页里像獾那样翻动鼻翼上的肌肉。等油墨被吸干了,我就对书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兴趣。这时我的成绩明显地下降,橡皮和一群儿童的汗臭味又席卷而来。
电 铃
虽然电铃的寓意有上课和下课两种,当我的回忆游回小学时,常常被骤然响起的电铃惊得像眼镜蛇那样抬起警觉的头。
读一年级时,我处于永远无法把握时间的状态,对时间的感觉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还粗放,我依据太阳的高度掌握上学的速度,因此不免出现差错。我经常在走到学校围墙外时发现本该拥挤的街道上空旷得弥漫着不祥之气,然后我听到了一浪一浪的诵读声从大海深处涌来。更多的时候是快跑到教室门口,铃声却等不及地止住了,把我搁浅在老师和全班人的注视中。有一次和一个比我高一级的玩伴一起上学,他是外公厂里一个搬运工的儿子,后来成为县城里最有名的罗汉之一。他说服我用自己的零花钱在听到第一遍电铃时还买了两根冰棒,结果赶到教室门口时,我的那根只吃了三分之一。我被老师的喝止钉在门口,右手却固执地背在身后滴着水。老师终于发现了秘密,揪出我的冰棒砸在地上。他愤怒的眼神强化了我对电铃的印象。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对电铃的惊惧随着我把握时间能力的增强而减弱,然而在梦境里(白天坐过有电铃的地铁或经过某小学),我还会不时地被小学的电铃击中。成年后我多次遇见那个骗我买冰棒的玩伴,第一次他刚从监狱出来,对我笑得讪讪的;第二次见他戴着耳环和一个妖艳女子占着半边大街打羽毛球。我想他对电铃的记忆和我是不一样的。用带电的小锤拼命敲打自身以使它颤栗地尖叫的电铃,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
自 卑
我不能有效地掌控自己的身体,不时地在课间奔跑时出洋相。一条沟,我以为可以飞跨过去,事实却不是这样,突然就坠向深渊,就要死去那样。我眼冒金星坐地上,疼得几分钟无法动弹,在腿部神经恢复知觉的过程中,我的失败成了一幅画挂在同学的面前。这其实只是我的错觉。所有人都在飞奔和摔跤,谁也不会注意一个小孩的跌倒,然而我脸上红旗和白旗轮番翻转,以为自己成了全世界的中心。
叫操、领唱、在大会上代表班级发言、被老师用右手抚摩脸蛋……这样的好事永远和我无关,每个班都有一对金童玉女包揽这些事。他们要么是教工子女,要么长得像宣传画里托着白鸽的祖国花朵。他们成为红花之后,其他同学就全成了绿叶——沉默的大多数。红花越来越红时,绿叶就越来越沉默。我们班的史丹和叶少华同学就是这样的明星,我认识他们以后,对朗诵、写作文、歌舞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只是默默地画着岳飞和他的战争,我惟一的幸运是史丹和叶少华同学当初没有爱好画画。
只有史丹等极个别同学不怕父母来学校探视。雨天教室窗口常会闪现一些微笑的头颅,有的挑着卖菜的担子,有的夹着的黑布伞破得像只残疾的蝙蝠。每当一个头颅出现,教室里就有一个更小的头颅惭愧地垂下,而外面的人往往对此浑然不知。一年级时,在外地工作的父母也到学校来看过我,手里拎着一袋刚出笼的热包子。由于长年不在一起,他们在窗口出现的脸上浮现着羞涩的爱意。他们搜寻我的目光把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我脸上,把它烤得灼热通红。后来我分析,不是父母使我羞愧,父母的外表和教养在他们那拨人里是出类拔萃的,我羞愧只是因为他们使我暴露在了大家的注意之下。那时的我虚弱到了只有把自己藏在一大群绿叶里才感到安全。
成年之后我曾见过不少在小学里给我带来巨大压抑的那些红花,至少有一半人让我大失所望,这使我想起了“笑到最后笑得最好”之类的俗语。然而我也知道,最后的笑其实并不能抹平最初的伤痕。
感 伤
二、三、四年级是在乡下读的,我寄情山水,把养八哥养狗当成主业,数学最低考到了27分。学校按规定要求我留级,父母只好把我送回县城的五一小学。五(四)班热情收留了我。语文和数学老师的年龄只略比我父母小几岁。语文老师是男的却性情温和,只是老将我姓名里的“范”念成很女性化的“樊”,令我对自己的姓感到自卑(在我当时的见识中,只有樊梨花这样的古代女子会姓这个奇怪的姓);数学老师严厉急躁所幸是女的,女儿又在我们班上,所以更像是全班同学的母亲。在这个班上我第一次尝到挨表扬的滋味。
《记一次劳动》是我们常写的作文题,那次我也用上了“牛毛细雨”等时髦词汇,并且把班上块头最大力气最大的孔军同学拉板车的样子,比喻成了一头默默奉献的大水牛。语文老师为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叫到讲台前享受了当面批改作文的待遇。走回座位的过程我感到腿是晃动的,我还没找到被人羡慕时该使用的走路姿势。数学老师也一样,每次考试有进步,都通报表扬一次。她每念一次我的名字,我的数学就要增加几分。结果小学毕业考试,我总分接近160分,远远超过了重点中学录取线。
小学毕业的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半夜醒来,想着明天早上起来就要去乡下过暑假了,想着以后就不用带着中午的饭菜去五一小学补课了,想着从此就要同两位和父母一样的老师分开了,忽然很伤心,眼里含着泪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翻来覆去。这是我第一次对亲人之外的人发生这样的感情,结果被子的一角滑落到地上的蚊香上。我用了好几脸盆水和半个夜晚的时间,才彻底熄灭棉絮里的火星。而另一种暗火,多少年了还在心里某个昏暗的角落明明灭灭。
音 乐 课
18岁以后我常因在唱歌方面有些特长,在公共场所受到女孩的另眼相看,没有人知道,在五一小学,我曾以为在唱歌方面自己是个哑巴。我比害怕数学还怕音乐课。
对幼儿园最主要的记忆就是音乐课。课堂在五一小学前面一间没有天花板的大教室里。老师按座位的顺序两个一对地把我们押解到黑板前合唱她刚才教过的歌。两个人并排站着,双手背在身后,头被手风琴的声音拽着左右摇晃。这样的情景使我联想到电影上国民党匪军挨个枪毙共产党地下党员,上课的过程在我心里就是等待被枪决的过程。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我记不住一句歌,实际上我压根就没开口学过一句。当我和另一个无辜者站到黑板前时,我几乎要昏厥过去。怎么过关的我一点也不清楚,下来后发现后脑勺变成了白色的。那时恐慌就是粉笔灰的颜色。
五年级时,我对上音乐课就是被枪决的印象得到了更正,原因是它不像在幼儿园是一门主课,老师不会让我们一一上台去测试了,我可以用滥竽充数的方式轻松混过45分钟。男音乐老师圆滚滚的身材和面庞赋予音乐课一点幽默的气氛,而且他还总想在那张松弛的胖脸上堆积出严肃的表情以威慑课桌下的骚乱,这使得音乐课更像一场戏剧表演了。老师板着脸眯着眼在脚踏风琴后奋力划动音乐的桨,我们像无数浪花在讲台下的海面上兀自亮晶晶地雀跃。
不记得在小学学过哪些歌,前几年晚上做梦,忽然唱起一首外国歌:国际纵队有个战士叫雅拉玛,人们都在怀念他……好像是歌颂西班牙内战时一位国际战士的,旋律有点像加拿大的《红河谷》。醒来后我想起来是那位胖音乐老师教的,我当初根本没怎么学,20多年后却在梦中把它哼唱了出来。后来我常在对生活感到伤心时在脑子里唱这首歌,这时时间就会在歌声里倒流起来,仿佛我还坐在五年级的教室里做讲台下的波浪,仿佛胖老师还在假装生气地瞪着我们,仿佛窗外的树叶还在摇晃着1982年的阳光。我的头在音乐里轻轻地晃着,晃着,不小心把眼泪晃出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