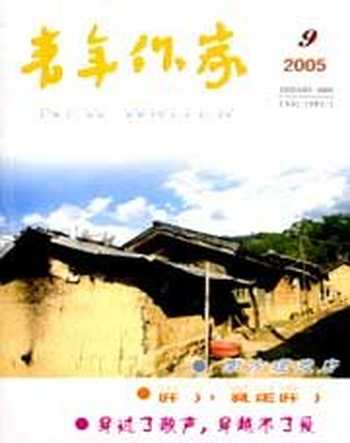穿过了歌声,穿越不了爱
coffee
“听过品冠的《陪你一起老》没有?去听听吧,歌词写得很好。”许久没联系了,那天在QQ上遇到,他跟我说的惟一一句话,就是这句。然后他下了,头像又变成了一贯的灰灰色,很冷的感觉,如同那些已经淡化的记忆。
在这些淡化的记忆里,我想起了那个雪夜,那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时,我们都上大四。临近寒假的那段时间,天空一直下着雪。师弟师妹们要准备期末考试,忙着抱佛脚,反倒是我们这些大四的比较清闲。找工作的,要么已经找好了,要么也只能等待明年春季了。准备考研的,也都几乎“尘埃落定”了。在大四的这两批人中,他属前者,我属后者。
雪停的那个晚上,他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出来走走吧,在我的心底,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和一个女孩一起在雪夜里散步,我还从来没实现过,你能帮我吗?我现在就在你们学校。我在犹豫了几秒钟后答应了他。雪夜是美的,愿望是美的,我不忍拒绝。他似乎特别的高兴。他说,我到你们宿舍楼下找你,几分钟后到。他的语气兴奋得像个领了奖状的小孩。
见面后我才知道打电话时他根本不在我们学校,而是坐在他宿舍的床上。他原本是做好了失望的准备的。他学校与我学校邻近,然而从他的宿舍到我的宿舍楼下,依平时走路计算,至少得半个小时。他只用了几分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奔跑过来的,但当我在宿舍楼下看到他时,他足足喘了十分钟气才笑着跟我说:“走吧。”我注意到他的两只鞋子都湿了,裤管也一直湿到了膝盖处。
那个晚上,我们就一直在雪地里行走着,把我的校园走遍了,把他的校园也走遍了。他一直不吭声,我也一直静静地陪在他身旁,陪他实现他那个心底里的愿望。我开始想,他在想什么呢,他应该也会觉得满足了吧,是那种实现了愿望的满足。没想到走着走着,他却突然笑着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好像陈红。”“唱歌的那个陈红吗?”“我只知道有个演戏的陈红。”我们相视无言,然后就一起大笑了起来。在宁静的雪夜里,我们笑得尤其畅快和舒心。那晚,也不记得走了多久,只记得我回到宿舍时正赶上传达室阿姨锁大门。
这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系过了。留在记忆里的只是那最后的笑,那雪夜里畅快、开怀、会心的笑。
后来,我考了研,来到了这所大学继续与书为伴。再后来,听宿舍老大说他也在这个大城市里工作。老大是我们宿舍的老大,也是他宿舍老大的女朋友。这一对“老大”显然是知道他的联系方式的,只是我没问,他们也没主动告诉我。就这样,我们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却不再有对方的任何音信。我知道,我们都在心底默默地祝福对方过得好。我觉得这样很好。
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在那个秋风瑟瑟的日子里突然叫我去听一首歌。
我迫不及待地下载了这首《陪你一起老》。我大概从没这么用心地听过一首歌。听着听着我真的哭了。我突然觉得它是那么熟悉,似乎在哪儿完整地听过。它似乎不是从外界传来,而是从我的心灵深处,从记忆的某个角落浮了上来。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作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伤心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希望你知道,我是真心的祝福,只要你过得好,快乐就好。”
我打心底里承认他是爱过我的,而且爱得那么深。我满带泪水地去承认,于是,那些淡化的记忆又开始在泪水中栩栩如生起来。
有些故事似乎从一开始就被涂上了宿命的色彩。就如我们宿舍的老大和他们宿舍的老大。那天明明是为我们的老四和他们的老二准备的“相亲”,结果老四和老二没看对眼,倒成全了这一对陪同而去的老大。据说这对老大是一见钟情。据说,老四去“相亲”的那天,老大原本是打算去逛街的,不料天空突然下起了雨,走到公车站牌的老大只好打道回府——其实这有点不像老大的性格,平时要说逛街,她可是风雨无阻的。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鬼使神差”。据说,他们的老大对这种灯泡差事也一向是只觉无趣的,但最终却还是被硬拉过去了。
也许,许多具有宿命色彩的东西都只能用“鬼使神差”来说明。我和他也这样。
话说这“相亲”的第二天,他们的老大和老二便设了“酒宴”来贿赂我们全宿舍的小妮子们。听说还是亲自下厨的,只要报上菜名,尽量满足。那段时间我刚迷上写小说,虽然写得不堪入目,但也自得其乐,如痴如醉,有时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纵然有七颗心,对这群小妮子们的“浪漫情事”我也是无暇顾及了。正逢文章写到顺心处,恨不能不吃饭不睡觉把它写完。却听见接电话的老四一个劲地对着话筒报菜名:红烧鲫鱼、鱼香肉丝、麻辣牛肉……清蒸鲤鱼。我敢说我的耳朵一直是竖着的,尤其是听到最后一个菜名时,我简直要跳起来抱着老四说“还是老四了解我”,也不管是不是自己“自多”。谁要我喜欢吃鲤鱼呢?我开始说服自己:有的吃,不吃白不吃。
那天天有点冷,是入秋的天气了。我记得自己穿了一套咖啡色——毛衣是浅咖啡,秋裙是深咖啡,靴子和背包也都是咖啡系列。大学里我一直钟爱咖啡色。我爱咖啡色就如爱吃鲤鱼一样,有点不可名状。
掌勺的不是他,他是上菜的。第一盘菜上来他就笑着说:“咖啡姑娘,麻烦把那个茶壶递过来吧。”一桌的人都知道在叫我,虽然以前从没人这样叫过我。我笑了。这以后大家就都很自然地叫我“咖啡姑娘”或“咖啡”了。
饭后,有人提议去附近的YES音乐吧唱歌。我听到他们在说,这家音乐吧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开的,还挺有文化气味的。里面的乐团是从我们学校请的。音响效果不错,价格也还便宜。吸引我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它的名字。我对老四说,为什么要叫YES呢?我将来就要开一个NO音乐吧。大家就都笑着嚷,好啊好啊我们的咖啡姑娘开音乐吧,到时我们就可以天天去泡吧了,至少给我们打个五折吧。
那家音乐吧真的不错,布置得很有韵味。有淡淡的烛光,有淡淡的茶,还有那么一点淡淡的情调。那晚大家都不停地唱,只有我和老四每人只唱了一首。老四唱的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我唱的是刘若英的《后来》,两首歌都有那么一点伤感。大家都说我们唱得好,跟原唱似的。
不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桌上喝茶聊天或把弄吉他。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宿舍个个都会弹吉他,他是弹得最好的。我不会弹吉他,但有那么一刻我突然心血来潮向他要过了吉他。我把吉他放在膝上,摆了个弹琵琶的姿势,然后胡乱地弹了一通。后来他半开玩笑地跟我说,我就是在那一刻爱上你的,淡淡的烛光里,那一幅女子琵琶图深深地印进了我的脑海。
回来的路上,大家谈的竟只有《城里的月光》和《后来》。歌词写得好啊。旋律也不错啊。这种或颓废或忧伤的感觉把人的心揪得很紧啊……
那时正是国庆放假。在那个美丽的秋风渐起的黄金周里,我们几乎天天与音乐为伴。他们用吉他弹那似老非老的校园民谣,我们唱着半流行半通俗的歌。我们在歌声里陶醉了,飞翔了,飞到了乡间的田野和小路上,飞到了山林和清泉旁。短暂的日子,因为有了音乐,这两个寝室(应该说是两个“组织”,因为那时我们约定俗成似的,从不叫“宿舍”或“寝室”,而都嘻嘻哈哈以“组织”冠之),很快建立了我所认为的很深的友谊。
假期刚过,我们学校便组织去外地教学实习。宿舍里八个人被分成了三批,去三个不同的地方。我独自一人,却恰巧被分到了他的家乡,一所重点中学的一个重点班。出发的那天,他们全“组织”都跑来了,忙着给我们搬东西,弄得全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用那种艳羡的目光瞅我们。
“咖啡姑娘,我们组织提醒你:今天气温降到十六度,切记加衣服,谨防感冒。”
“咖啡姑娘,组织提醒你:今日天将放晴,别忘了晒晒被子。”
“爱穿裙子的咖啡姑娘,组织提醒你,今天得穿毛衣了。”
……
自实习的第一天开始,我的手机上就天天出现这种短信息,虽然都以“组织”的名义,但发信人都是他。实习的日子忙,忙得叫人喘不过气。备课。上课。听课。找学生谈话。维持纪律。组织活动。够呛啊!加上水土不服,天气干燥,没两个星期我就快倒下了,不争气的鼻子天天流血。第一次发现老师这么难当。在这种时候每天能收到这些温暖人心的话自然是很受用的。于是我开始习惯了有“组织”的提醒,习惯了有那么一点莫名的依赖。
“咖啡姑娘,组织派我为代表,特地过去看望你。现在就在车站,马上就上车了。”“我又没啥事,看望什么?”回这条信息时我的鼻孔里正塞着棉花。突然发现我其实有点不想见到他。
“你都流鼻血了还说没事?”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组织本事大呗!”
“怎么组织老派你呢?”
“因为你在为我们家乡人民作贡献嘛,再说我这次是回家,顺便去看你的。上车了。很快就到的。”
“不行呀,我们学校上课时间不准外来人进入的。”
“没事,你就到校门口接我吧。还有十五分钟到你们学校!”
我听到有一个声音从我的心底浮了上来,只是我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如同很深很深的潭底突然窜上来一条从没见过的鱼,那么小,却有点幽幽的冷。
他穿得很帅气。拎了一大袋东西。我有点生气地说,不是叫你不来吗?他有点惊愕。但接着就傻傻地笑了:“组织给你送点东西,你先拿回宿舍去吧,我在外边等你。”这情形让我想起小时候爸爸或哥哥去学校看我的样子。他们也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拎着一大袋东西。在他们离开后,我就一个人跑回宿舍翻看袋里的东西,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爸爸或哥哥弄的,哪些是妈妈或奶奶准备的。
只是这次,我怎么也分辨不清这些东西都是谁准备的。那么多小瓶装的牛奶,那么多苹果和梨,还有一袋红糖,一袋干干的茅草根,茅草根还散发出悠悠的清香。另一袋黑糊糊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正纳闷,手机短信来了:“组织指示:用那包黑黑的东西和红糖一起泡水喝,可以治流鼻血,每次用量十分之一。平时多用茅草根泡开水喝。”我问他那包黑黑的东西是什么,他却怎么也不肯告诉我,只说是个药方,按照组织指示去做就行了。
后来在我实习完回到学校后,他终于告诉我是什么了。那一刻,半个月前喝的东西都快被我呕吐出来。他们全“组织”的人却还感动不已地说,人家为了烧那么一小袋黑糊糊,可弄了差不多一整夜,头发都快被他拔光了。他倒没说别的,只傻呵呵地笑着说,听我妈说,用头发烧的灰当药引子,混和红糖泡开水喝,对治流鼻血最管用了。
那一刻,我想我是真的感动了,但这感动总伴着那么一股无言的痛。
我想我终于明白了那来自心底的声音是什么。
有时得到是一种失去。有时失去是一种得到。我亲眼看见我所看见的熄灭了。我轻松了。也失落了。我总喜欢用线与线的关系来形容人与人的关系。线与线的重叠、交叉、平行或许很好地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某些解释不清的缘与分。“我们注定了是两条没有交点的直线”,这是个有点无奈却又最堂而皇之的理由,当然也有人认为是搪塞,是借口。
他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出了那三个字。我除了也半开玩笑地说出那句话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我仍然天天听刘若英的歌。在那段考研复习的日子里,因为有她的歌相伴,我一点也不觉得枯燥和寂寞。
像电影里闪过的回忆镜头一样,闪进我脑海的第一个镜头竟是鲤鱼汤,那一小碗一小碗鲜美的冒着热气的鲤鱼汤。每次从实习学校赶回去,无论是三五人聚会,还是两个“组织”全体聚会,他都会端出自己熬的鲤鱼汤给我。这时,就会有我的室友说,不会照顾自己的我就应该有个这样的大哥罩着。也有人笑他为我开小灶,居心不良。他仍旧是笑,对这些言论不置可否。然后细心地为我捆好要带过去的被子——那麻利的样子顷刻落进了我的眼里,也落进了我的心里。我后来试着去抹掉它,却怎么也抹不掉,没想到一不小心竟抹出了泪水。上车时,他把早已准备好的晕车药和矿泉水递给我,眼看着我吃了,才又从口袋里摸出一盒膏药:“拿一片出来贴在手腕的血管处。”我坐在车窗边,他就在窗外仰着头对我说。我笨拙地用一只手给另一只手贴膏药,怎么也贴不上。他一时急了就探过脑袋一把抢过了膏药,为我贴好,然后红着脸笑了。“这下应该没事了。”他说。
贴膏药的那块地方似乎还泛着异常的白,小小的一个正方形模样。我哭了。
离考研还有59天时,他给我写了封信。信是他自己送到我手上来的。把信递给我时,他的手有点颤抖。我第一次发现他是如此拘谨。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我也是。一段时间没见,竟很快就陌生了。他试图像平常那样笑,却没有成功,他笑得有点难为情。我知道,很多东西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在信里没说别的,只叫我安下心来好好复习。他说,你现在什么也不要去想了,全力以赴利用好这59天吧。他用了一大段文字分析了我在考研上的优势和不足,之后,他说,我仔细观察过你的脸色,也偷偷看过你的手,这些都明显说明,你的健康状况不怎么样,而且有些营养不良。你太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你觉得我还可以信任的话,那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像大哥一样照料你两个月吧。现在,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赶快调整好状态开始工作了。
我默认了。我有种预感,这将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两个月。我们将以这样的方式告别。
那段时间他无非也就是给我送点吃的,打打开水等等。偶尔,他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听的唱片,或者提醒一下我注意休息和营养。我们很少说话。在那59天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因为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关注着我,关注着我的考研。我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整天埋头苦干,足不出户,看书累了就待在房里听听歌。我们的关系有点像坐牢的跟探监的。
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跑过来,送给我一盒唱片,我一看,是刘若英的新专辑《一辈子的孤单》。
在考研复习将近尾声的那个元旦夜,他第一次主动叫我出去放松放松。学校里热闹非凡,红红的篝火照亮了两所校园,也映红了校园顶上那片广阔的天空。我们选择远离人群,到了那间YES音乐吧。
一样淡淡的烛光。一样淡淡的茶。一样淡淡的情调。他不停地弹吉他,很多都是我没听过的。他说他喜欢光良和品冠,今晚弹的全是他们的歌。他把吉他递给我,叫我弹《爱的罗曼史》——他教会我的唯一一支曲子。我想起很久前的那个夜晚,没敢接。
我只唱了一首歌,就是刘若英的那首《一辈子的孤单》: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有的爱犹豫不决,还在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歌声响起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种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我的眼睛湿润了。
送我到宿舍楼下时,他对我说,应聘的那家单位叫我过去参加岗前培训,所以不能实现诺言陪你到考研了,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坚持下去,考个好成绩。然后,他就像往常那样傻呵呵地笑了。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涌上了我的心头。我会的。我说。
再见面时,已是那个雪夜了。我记得雪停前,我还静静地仰望过漫天飞舞的雪花,看它们轻轻地、轻轻地落在树叶上,挂在树枝上,或掉进大地的心窝里,那么柔顺而乖巧。我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么美丽的雪花,因为我在南方的这座无雪城市的缘故,也因为某种心情的缘故。
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给他打电话报喜,但一拨竟是个空号。心里有点失落,却也觉得这样的结局很好。
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
这是我唱给他的最后一首歌。
转眼,我在这座大都市已生活几年了。我挤着公车,规规矩矩地上着枯燥的班。日子平淡而充实,我的感觉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闲暇时,我就逛街,在人堆里像挤油饼一样地行走,在繁华的高楼间穿梭,带着目的,或漫无目的。有那么一天,我的眼前突然一亮,因为我看到了一行大大的字:NO音乐吧。
我听到有人在说,这么难听而拗口的名字。也有人像是自言自语地问,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
那首《陪你一起老》的旋律和歌词又从我的心灵深处浮了上来。我差点落泪,但终究只是欣慰地笑了笑。
我想对他们说,这只是一种纪念,纪念一种在歌声里浮动的穿越不了的爱。但我没说。我沿着我来时的路轻轻地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