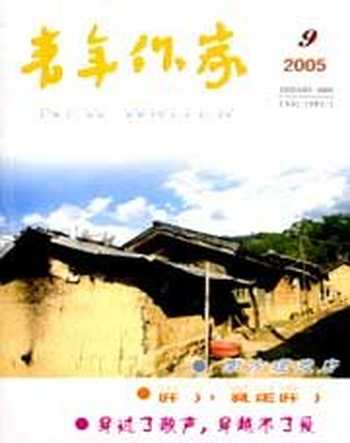南方理发店
章 元
“你家老赵在外面有女人了!”卖服装的女人脚刚迈进门就嚷嚷开了,恨不得手里拿着一个麦克风才好。
小安徽正在往楼上住的大娘头上抹冷烫精,听了这话,手一抖,冷烫精全洒在了大娘的脑袋上,一直顺着她的右耳朵流到脖子里。烫发大娘不满地拿手抹了一下,从镜子里看了小安徽苍白的脸一眼,没言语。
“谁看得上他啊!”小安徽虽是笑着说的,可心里还是别扭,心想,这婆娘自己的是非最多,她的风流韵事每天都会传到这里,她居然还有心思去对别人说三道四?老赵怎么会在外面有女人?
卖服装的女人见小安徽不信,马上来了精神,一边对着镜子摆弄头发,一边绘声绘色地描述“老赵和那个女人”的故事,就像她亲眼看见了老赵和那个女人睡觉似的,一副定要小安徽听了就要心肝俱碎的架势。凭借她顽强的叙述,小安徽已经知道她家老赵昨天在卖服装的女人的店里买了一件“只有三陪小姐才会穿的衣服”。这衣服是给谁的?难道是给她小安徽的吗?烫发大娘眯着眼睛听得出了神,直到小安徽喊了她四五声,她才回过神来,稍感尴尬地站起来坐到蒸汽帽底下。
“快帮我剪剪刘海,我还急着开门呢!没准你家老赵今天又去给她买衣服了!”卖服装的女人幸灾乐祸地对小安徽说,还十分投入地帮她出主意,“你家老赵上哪儿去了?我跟你说,他一回来你就问他,跟他哭,跟他闹,一分钟安宁也别给他!让他知道你的厉害,有这一次就不敢再有第二次!哈哈……”
卖服装的女人彻底陶醉在自己的幻想里,沙哑的笑声显得分外猖狂,好像已经看到了老赵跪在小安徽面前求饶的模样。小安徽往她的头发上喷了点水,开始剪,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专心听她说话分了神,刘海剪得像拿菜刀剁出来的。卖衣服的女人急了,腾地一下站起来嚷着:“你家老赵让人勾搭走了,你也不用拿我出气啊!又不是我让你守活寡的!该找谁找谁去!你让我这样怎么出门?”
小安徽被骂呆了,直到卖服装的女人走掉,她才想起那女人还没给钱呢。她小声骂了一句,心里却在盘算,这个该死的老赵,到底是给什么人买那样的衣服?难道他真的在外面有女人了?
烫发大娘轻轻咳嗽了一声,小安徽回过头来看她。弥漫出来的蒸汽笼罩着她的脸,谁也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能看见她那十个枯瘦的手指一共戴了六枚戒指!
小安徽有点心酸,除了结婚时婆婆给了一个黄金戒指,老赵到现在还没给她买过一件首饰呢!人家现在都流行买钻石的,可她有什么?这也要怪她,老赵一说给她买,她就说干活不方便,万一丢了还不心疼死。结果呢?现在她的脖子、耳朵、手指都是光秃秃的,反倒便宜了那个狐狸精!
“要我说啊……”烫发大娘不把自己当外人地做了一个开场白,“她的话你也不能不信。”
小安徽没接茬,不知道这老太太又要说什么。
“你家老赵啊,还真在外边有女人了。那天我看见一个男的背影挺像你家老赵,跟一个女的挎着胳膊逛超市。后来我还问你,你家老赵干什么去了,你说帮你进货去了,你还记得吗?就是那天,黄瓜大减价,9毛5一斤,我当时没来得及过去打招呼。心想肯定是我看错了,你家老赵不是那样的人!可今天听她这么一说啊,我再一仔细琢磨,那衣服、那头发、那身板,不是你家老赵是谁?要我说啊,男人都是猫,贪腥!你家老赵虽说看着挺老实的,可再老实的人也架不住有不要脸的女人勾搭啊!唉,要我说啊,算啦,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家赵蕊都长那么大了……”
小安徽本来正在收拾,听了这话,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就那么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捏着几只发卡,一动不动的。顺着她空洞的目光望过去,你可以看见一面布满整个墙壁的大镜子,镜子上没有一个污点;镜子前是一排木匠做的白色小隔板,钉在墙上充当桌子,这是小安徽的主意,油漆虽有些斑驳,倒也干净,一尘不染;隔板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种剪刀、梳子、喷发胶、染发剂、电吹风、电推子,每样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从来不会乱放;隔板的右侧下方角落里堆着今天剪下来的头发,大概有两簸箕那么多。无论谁走进这家理发店都会觉得摆设虽然简单了些,却很干净。何况只要剪发的技术好就可以了,要那么豪华的装修有什么用?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实惠最重要。
小安徽盯着那些头发——她给老人和孩子剪发只收4元,给大人剪发才收5元,那些头发代表了多少个4元和5元?扫帚倒了,靠在剪发的客人坐的椅子上,还没有完全倒下去,想是刚才卖服装的女人碰倒的。它旁边的那把椅子是给染发的、烫发的、做营养油的客人准备的,坐在这把椅子上的客人每个最少要付给她10元,她喜欢站在这把椅子前忙活。再旁边的那把椅子是给修面的客人准备的,最近十年似乎都没有用过,可是小安徽一直没舍得处理掉。在没有发明电动剃须刀的那几年,等客人都走光了,她家老赵每天都会坐在那里,把头靠在她丰满结实的胸脯上,让她来修面……小安徽的眼睛里好像进了东西,不然怎么会有水流出来?
手里的发卡噼哩啪啦地纷纷落地,声音是那么轻微,轻微到几乎没有声音,在小安徽耳朵里却像是拳头大的冰雹打在钢板上。她的心疼啊!
我这么辛苦是为了谁?我天天呆在这个破地方累死累活的是为了谁?老赵啊老赵,你这个死没良心的,等你回来,看我不和你拼了!
“听说你家老赵在外面养了个女人,又年轻又漂亮,那小细腰还没有一尺八!还给她租了个房子,每个月光零花钱就给好几千!”
说话的人是芳芳妈,她说起话来就像一只上满弦的鸭子,恨不得浑身上下都生满嘴巴才好,不然就会把她憋死。
“对,对,对!那个女的腰是特别细!走起路来,那屁股就不够她扭的!”烫发大娘出人意料地接上一句,好像很高兴有人证实了她那天所看到的。
芳芳妈被吓了一跳,刚才光顾着传达最新消息了,根本没注意到理发店里还有别人。可听烫发大娘这么一说,她那点仅存的愧疚——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她怎么能替小安徽宣传这个,何况她家芳芳和赵蕊还是同学——可马上,反而多了一份理直气壮。原来大家都知道啊!
原来大家都知道啊,小安徽想,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我怎么这么傻呢?老赵啊老赵,你把我骗得好苦哇!可心里这么想嘴上还不能说,还得替老赵辩护:“不可能!他兜里有几个钱我还不知道吗?他往哪给人家偷几千块去?把他卖了也不值!”
小安徽说了几句并不幽默的话,脸上甚至还真的挤出了一丝笑容,好像只要这样就能证明她家老赵是清白的。她知道芳芳妈的嘴有多快,但凡她说老赵一个不字,明天就能传进赵蕊班上所有同学的家长耳朵里。老赵虽然干了不要脸的事,可不能让闺女在学校里被人戳脊梁骨!
芳芳妈知道小安徽是在“护短”,她冷笑着看小安徽手忙脚乱地拆着烫发大娘头上的发卷,头发在她手里就跟拔野草似的,把烫发大娘疼得嗷嗷直叫。小安徽这么多年的手艺,连个发卷都不会拆?哼,还嘴硬?还不承认?可想归想,芳芳妈还是语重心长地劝小安徽:“这事你跟老赵闹归闹,可千万别闹到离婚。芳芳班上的那个孙鹏——你听你家赵蕊说过吗?他爸妈一离婚,学习也没人管,天天挨留,现在连老师都不愿意管他了!老赵这是第一次,以后不犯就是了,你得为你们家赵蕊想。再说了,这个家不都是你在撑着吗?他离开了你,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烫发大娘对小安徽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你看这左边的头发,弯度根本没有右边大嘛!但考虑她家老赵干了这种事,虽然觉得自己有些吃亏,可还是按照事先说好的给了小安徽25元。她认为小安徽之所以没有打理好她的头发,完全是因为现在这个女人和小安徽说话造成的,所以临走时说了一句:“哼,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没事嚼什么舌头根子!”说完,她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的一块被她当成水迹的阴影,走到门口去拿她的篮子。真搞不懂就凭烫发大娘的这种眼神,她是怎么在超市的茫茫人海里,面对黄瓜大减价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清楚地看见老赵与一个女人挎着胳膊的?
芳芳妈一下就愣住了,等她反应过来,烫发大娘已经拎着菜篮子出去了。
“哎,这老太婆没事甩什么闲话啊?她这是说谁呢?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嚼谁的舌头根子了?我又没说她男人偷人……”
偷人,偷人!这个字眼让小安徽的心哆嗦了,就像遭遇大地震时的房屋,摇曳、震荡、翻腾,那样的无助。偷人!她该怎么办?老赵在外面有女人了,她该怎么办?!
芳芳妈瞥了一眼站在柜子前一动不动的小安徽,柜子的抽屉是开着的,再伸长点脖子往里瞧,里面有好几张鲜红的大票子呢!啧啧,要是一会儿在牌桌上都输给我该多好!还没来得及感叹,芳芳妈的手机就响了,是牌友催她快过去,人手凑齐了。正好理发店进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女顾客,芳芳妈看了一眼她纤细的腰肢,走了。小安徽看着打开的抽屉,觉得应该收烫发大娘30元才对。刚才冷烫精洒了,是洒在她头上的!那不是钱吗?可是……小安徽的眼圈突然红了。我这么算计是为了谁?就为了让他出去找女人吗?
“好多人跟我说你家老赵在外面有女人了,有这事吗?那个女的今天还来过是吗?老赵还要和你闹离婚是吗?听说他连赵蕊都不愿意要,是真的吗?”对面卖烧饼的安阳女人风风火火地跑进来,神色慌张地先是看看有没有人,然后才拉着小安徽贴着她的耳朵悄声问。
一刹那,小安徽所有伪装的坚强全都不见了,见到安阳女人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扑进安阳女人怀里痛哭起来。安阳女人皱巴巴的围裙畅快地吸收着小安徽的泪水,也吸进了她的全部委屈与悲伤。
大概因为都是外地人吧,小安徽和安阳女人的关系最好,她们虽然不是老乡,但是难以言表的相同感受使她们成了“姐们儿”。尽管她们在这里嫁了人、生了孩子,可她们的声音让本地人一下子就听出她们不是这里“原产”的,从心底轻视她们。就拿小安徽来说吧,她在这里开了十几年理发店,别人却从不问她姓什么,只问她是哪里人。当着她的面他们叫她“你”,背地里却她叫“小安徽”。她十几岁来这里开起这家“南方理发店”时就叫“小安徽”,十几年过去了,她还是叫“小安徽”。她不和安阳女人好,还能和谁好?
“光哭有什么用?还不快给你家老赵打电话,叫他回家,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还要不要这个家了?这日子他还想不想过了?”安阳女人焦急地说。
“他根本就没有手机!”小安徽委屈地说。
“你怎么不给他买个手机啊?”
小安徽只是哭,不说话。老赵平时到点上班,到点下班,有什么事就拿单位的电话打给她,她说要给他买个手机,他说只有往返路上的一个小时身边没有电话,没必要浪费那个钱,他还说每个月的电话费还不如给她买点好吃的。可哪知道这样的一个男人也会在外面养女人啊!
“真是怪了,你家老赵连手机都没有,怎么在外边养女人?现在哪个女人会看上一个连手机都没有的男人?”
小安徽的哭声变弱了。安阳女人说得对,现在哪个女人会看上一个连手机都没有的男人?可转念一想,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他要是没有别的女人,怎么会跑到卖服装的女人店里买衣服?还是一件“只有三陪小姐才会穿的衣服”?烫发大娘在超市看到的人是谁?腰围还没有一尺八的女人是谁?老赵昨天倒是给赵蕊买了一件衣服,是一件成人穿的紧身的半透明的白色上衣,说给赵蕊当生日礼物,夏天穿也凉快。小安徽当时就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你闺女才11岁,你怎么给她买这种衣服?穿出去不让人笑话死?你在哪买的?花了多少钱?你给我退了,退了!”老赵什么话都不敢说了,唯唯诺诺地答应明天就去退。就是那件衣服吗?
“他干什么去了?”
“上班。”小安徽止住了哭声。
“什么时候回来?”
“一会儿吧。”小安徽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6点1刻,再过45分钟老赵就回来了,她连饭还没做呢。
“卖烧饼的!”外面有人喊。安阳女人担心地看了小安徽一眼,小安徽说没事了,让她快去照顾生意。安阳女人又安慰了小安徽两句,匆匆跑了出去。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呢?
小安徽拿毛巾擦干眼泪,搬出电饭锅想做米饭,后来觉得实在没有心情,就抓了两把绿豆,放上一大锅水熬汤。天气热了,老赵下班骑车累,绿豆汤解暑。煮汤的时间,她把今天的事想了一遍,忽然有一种想要和老赵“说个清楚”的冲动。不管那个女人是谁,也不管有没有那个女人,她小安徽都要让他老赵知道,自己不是好欺负的!
拉开电视柜的抽屉,找到一本赵蕊的练习簿和一支铅笔,铅笔杆上还有赵蕊的齿印。小安徽打算给老赵留个条子,告诉他,她走了!她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她有多重要!小安徽想,他回来看见这里黑着灯,非把他吓死,让他知道老娘不是好惹的!
我走了,你有了别的女人,我再也不回来了。锅里有绿豆汤,去暑,喝不喝都别忘了关电源。
小安徽对自己的字条很满意,她想象着老赵看到字条后惊慌失措到处找她的样子,觉得这样的惩罚已经足够了。然后她把字条放在烟灰缸旁边,又有点担心老赵看不见,结果把电视遥控器和烟灰缸放在一起才放心。最后她把电饭锅调到保温档,关上灯,出了门,锁上之后还不放心地使劲拽了拽。兴高采烈地走出几步,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马上奔了回去。跑到门口她才想起来自己为什么要回来——她天天在理发店里呆着,老赵出门养成了从不带钥匙的习惯。她走了,谁来给老赵开门?没有人来给老赵开门,他又怎么才能看见那张字条知道她已经走了?
老赵定做的灯箱还亮着,她忘了关这个电源,简单的白底红字——南方理发店,在这条深邃的小巷里,这个理发店成了一个标志。小安徽站在灯箱跟前,想起老赵那天装灯箱的样子——发了福的他踩在小板凳上摇摇欲坠,努力把灯箱挂到墙上去,赵蕊在底下给她爸爸递螺丝,小安徽站在门口嗑着瓜子看他们父女俩忙活,不时地指挥一下,过路人都要停下来说一句:“好气派的招牌!”老赵会憨厚地笑一下,并不言语,继续干他的活。
我就这么走了?小安徽想。我为什么不等他回来问问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