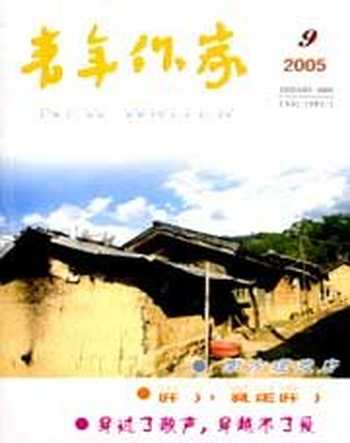我写故我在
唐仲清
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窃以为,笛氏所谓的思如果就只是沉思默想,在我看来意思不大。正如普列汉诺夫那句名言:“没有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其本身也模糊的思想。”依我之见,“我写故我在”要比“我思故我在”更有意义。正所谓:“写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写则殆矣”。
用我本人说事儿,我写故我在之道理如下:
窃以为,写作是消磨时间的最佳方式。据吾人之观察,世上绝大多数消磨时间的样态都没有工作成果。麻将连打一星期,一个个牌友疲惫得变了形,稀里哗啦,麻将收进盒子,人呢,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例子太多,恕不详表。唯有写作消磨时间后还有工作成果,君不闻,某退休老干部每天只用三小时手抄《红楼梦》,抄本已被估价为85万元,该退休老干部坚持其抄写行为实乃娱乐;其余时间还要打太极拳、唱京剧、下象棋;可惜,拳剧棋三项连一分钱都不值。
写作也是一项愉悦身心的活动。鄙人对人们热衷的一切娱乐从不染指,电子游戏麻将字牌稍稍复杂的项目都不会,只会打扑克争上游,但也没甚兴趣;鄙人远离娱乐活动的原因有二:拒绝学习所以不会;以为这些娱乐一点儿也不乐,窃以为,许多娱乐其实就是一套游戏规则不断重复,正如赌博的真正乐趣并非来自游戏而是来自输赢;写作要有乐趣,非得创新不可。前述退休老干部如把手抄《红楼梦》改为创作《红楼梦》,那他享受到的愉悦决不止于85万元手工费。对我本人而言,一切文体运动皆无,写作便是我唯一的体力劳动;写作让我得到延续生命必需的最起码的体育锻炼。当然,写作集体育、智育和娱乐为一体,是其他单纯体育运动无法比拟的。
写作让我获得守财奴的快感。巴尔扎克小说里的葛朗台以清点财产账目聆听金币响声为乐趣;吾人则以码字数目增长为幸福,十万百万千万,写上一亿个字的人就是亿万富翁。每每夜静更深,吾人在万籁俱寂中用眼看用手摸历年所写下的“作品”,第一千次心算咱已经写了多少万字,自我感觉像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如空空,空空如……》·源清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