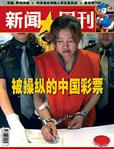迟到的父亲
程绮瑾
最初关注《云的南方》,并不是因为它顶着“今年柏林电影节惟一获奖华语片”的光环,也不是因为它的导演朱文是作家出身,而是因为它的片名——云的南方——一个充满诗意、让人憧憬的词语组合。
然而看过影片之后,我却发现另一个更具魅力的符号——“父亲”,这个让人想起权威、安全感、灵魂引导者的词语,其魅力丝毫不亚于“云的南方”。
徐大勤是以父亲的身份存在于影片中的。徐大勤是朱文父辈那一代人的典型,而朱文是如此理解他们的:“他们毫无怨言地度过非常的年代,在现实的生活中表现出一种超现实的忍耐。他们的性生活从来都是一个秘密”。最后一句暴露了他的本意。徐大勤不仅作为父亲,而且更作为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在朱文眼里,就像一个值得探索的神秘花园。
且不论朱文最终是否理解了“父亲”的生存状态,他试图探索就足以令人欣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国产的影片里,父亲一直是缺席的。我们只能通过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影片来审视父亲的存在。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影片《无因的反叛》,片中的父亲作为权威的代表而遭到反抗;80年代的台湾影片《童年往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片中的父亲作为原乡的代表而遭到现实的颠覆;90年代由李安导演、郎雄主演的“父亲三部曲”,片中的父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几经困顿而终获最后的圆满;世纪之交的日本影片《菊次郎的夏天》、《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片中的父亲作为灵魂的代表而显得虚无缥缈,令人哀伤。这些父亲的形象都有其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几乎每一次对父亲的审视都伴随着当时当地一种认同的危机,也伴随着一种电影风格的崛起。
如今我们的国产电影终于也开始迈出这一步,且呈现出与美国、日本、台湾等电影不同的面貌。从张杨的《洗澡》、徐静蕾的《我和爸爸》,到朱文的《云的南方》,我们逐渐开始重新认识“父亲”:原来他们也如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在现实中艰难地成长着。朱文说:“我们这一代人给父母讲了一个我们的故事,父母那一代人也应该给我们讲一个他们的故事。我想帮他们来讲这个故事。而讲完后,才发现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导演的这种理解,让这部影片对父亲始终保有一股脉脉温情。而这种理解的背后,是中青年一代的成长与成熟,是他们在反叛与迷茫之后重新寻求平静、宽容与归宿的情绪。
徐大勤终于到了他梦想半辈子的云南,云南的神秘被消解了一点,又被重新建构了一点。我们的镜头终于对准了父亲,对他们体贴了一点,也宽容了一点。虽然来得有些迟了,但终于,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