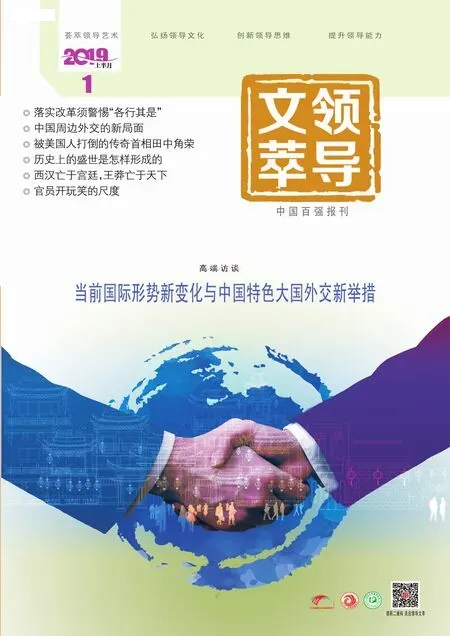阅读2:与时俱进是政党生存的基础
宋少鹏
当代政治是政党政治。
政党作为代议制运作的客观需要出现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1800年美国的杰斐逊以共和党侯选人的身份当选为美国第三届总统,也算是人类政治史上政党政治的开端。尽管17世纪英国的议会中已经出现了政党政治的雏形,围绕着詹姆斯的王位继承问题,议会内出现了保王派和国王反对派,后演化成托利党和辉格党。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讲,托利党和辉格党只是议会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群众性政党的出现却是伴随普选权的扩大因组织选举的需要而出现的。但政党产生之初因其明显的党派偏私的特点被近代民主制度的缔造者们所忌讳、厌恶甚至压制,而被排斥在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宪政结构的框架之外。华盛顿在他著名的告别演说中,以“最郑重的态度”警告国民注意“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
尽管,政党和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惯例被各国的政治实践所接受,但政党的法律地位却只是作为公民结社权的个人自由权的体现和扩展。直到二战之后,西方各国才从法律上确认政党作为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基本工具的职能,联邦德国出现了第一部《政党法》,西方各国纷纷在宪法性文件中承认政党在宪政体制中的法律地位。二战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政治的某种标志,成为衡量传统部族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指标。是否存在竞争性政党政治成了西方国家衡量民主化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尺。虽然,以西方为标准的发展观和现代化理论遭到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理论和政治上的批评,但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却是不争的事实。
政党作为代议制民主的工具上升为民主制度本身,或是抽象为社会发展必由之路中的必然,是对政党和政党功能的一种政治神化。一个具体的政党的生存和消亡并不是一个社会政治系统的崩溃,只是表明这个社会的政治系统一度出现了问题,甚至是危机。如同一个人的死亡不能代表人类的灭亡。反之,一个人要健康长存必须了解健康的原理,适应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政党亦如此。只有适应社会大系统,能圆满完成自己功能的政党才能在政治体系中立足、生存和发展。所以,理解了政党在代议民主制中的工具身份和代表角色,才能理解与时俱进作为政党生存基础的重要性。
换言之,政党作为一种代议工具,它架起了了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桥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党是集合民意、表达民意的工具。也正因它是民意集合和民意表达的工具,伴随所代表民意的变化,作为民意集合的政纲应随着民意的变迁而变迁,而不能固守有所谓的执政传统,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抛出政治舞台成为历史陈列室的教材。
综观当今各国,传统大党都面临着各种挑战,新生党派影响日增,从垄断政坛多年的传统大党的分裂或下野,到欧洲极右翼政党进入联合政府,各国频频上演因政党格局的变化而引发的政治地震,而全球范围内这种政治地震此消彼长,余波绵绵,延续至今。面临挑战,适时作出调整的政党保持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反之,不得不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1993年8月日本政坛出现自二战后38年第一次出现联合政府,结束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历史。1994年意大利的第一大党天民党失去传统优势,沦为小党。二战后到1994年,意大利天民党始终保持其在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曾组织过15届一党政府。虽然多数情况下都是天民党为首联合社会党、社民党、共和党、自由党联合的所谓“中左五党政府”的形式。90年代初意大利开始的反对贪污腐败的“净手运动”冲垮了天民党、社会党等传统大党,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
无独有偶,就算传统政党格局未被打破的英美国家里,传统大党也遭遇到前所未所的挑战。1992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以独立侯选人的身份获得了18.9%的普选票,取得了自1912年以来,美国两大党以外的总统候选人所取得了最好成绩。尽管,障于美国“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作为第三党的侯选人几乎不可能夺得总统宝座,亦很难瓜分议席。当年入主白宫的克林顿也只获得了43%的普选票。美国选民对佩罗的支持映像出选民对传统两大党的不满和传统两党所面临的挑战。当然,1992年参加竞选的克林顿早已意识到传统政党面临的挑战,打出“新”字招牌,以示与传统旧党的区别,从而作出回应。
克林顿是以“新民主党人”的形象出现在选民面前的,“寻找一种介于自由放任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克林顿语)。大西洋彼岸英国布莱尔打着“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帜,以“改革的化身”入主唐宁街十号。当然,这篇文章我不想讨论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及其实际政策效果,也不讨论“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关系。我们虽不能简单地论断,第三条道路是对选民意愿的直接体现,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但以美国民主党的克林顿、英国工党的布莱尔、法国社会党的若斯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左翼民主党(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的达莱马等人上台执政为代表,曾在欧美兴起了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潮,却是事实。我们强调的是克林顿他们不拘泥传统教条的改革意识,“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布莱尔语),与时俱进的精神。
“第三条道路”最大的特点是“中间化”,淡化左右之争,模糊意识形态分歧。如果说,布莱尔希望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一些学术修辞,“既要突破旧左派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观念,又要突破新右派倡导的那种狭隘的个人主义、相信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放任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则更坦白地承认“新中间”就是一种实用主义,“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
“中间化”不仅体现在理论和政纲中间化,也体现在党的群众基础的中间化。英国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按“新模式”着手改造工党。1992年,对党内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在领袖选举上取消了工会在选举中的集体投票制,实现“一人一票制”,减少工会对工党的控制。布莱尔的“新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已削弱到破裂的地步,“新工党”把工党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所谓的“超越于左右”之间的中间阶层政党,成为“企业界和商业界的政党”。意大利共产党在1989年3月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把一个阶级政党改造成“代表全体意大利的公民”的纲领性政党。1991年,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索性将党易名为左翼民主党,以示与旧党的区别。
虽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光谱中一直有左翼和右翼之分,但执政的政党或政党联盟,不管是“中左”或是“中右”,实质上都只是政治天平在中间准星方位处左右的摇摆,而不会过分脱离中间区段。二战之后,这种左右两翼政党的从党纲到政策的趋同现象越来越明显。 相比于旧左派和旧右派在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坚持阶级对应和实际政策上的中间化的表里不一,“第三条道路”把“中间化”理论化,明确承认走中间化道路。
当然,“中间化”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二战之后,西方世界从围绕物质财富的工业时代进入以信息和技术革命为标志的产业多元化的后工业时代:“一个私有财产、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已经失去了‘中轴原理的社会形态。”工业大生产使社会分裂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利益分化以阶级分野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里,政党很容易地找到自己的群众基础,政党与社会阶级之间对应关系非常清晰,政党很容易地实现着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的功能。产业结构的调整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西方社会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两极结构逐渐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转型。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虽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国的统计数据有所出入,但“中产阶级”倾向却有一种扩大效应。1980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46.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普通白领工人”愿意以中产阶级自居,以其价值标准和政治倾向作为自己的行为参照。所以,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不能仅以社会中职业分布数量来判断,应考虑其辐射效应。在中产阶级数量和政治影响占优势的社会中,中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和政治需求会决定政治市场中的需求,影响各政党所提供的政治产品——党纲和执政政策的内容。中产阶级不同于传统阶级,传统阶级具有相似的职业背景、集中的劳动场所,容易形成阶级利益。而在“中产阶级”这个标鉴下,是多样的职业分化和不同的利益要求,多元成了中产阶级的特征。多元的利益格局下很难形成一个简单、明了、统一的阶级利益。在以中产阶级为基础选民的西方社会中,各政党基于选票压力,只能以模糊和中间化的纲领来融合不同选民的不同的利益要求。政党在民意集合方面的中间化一方面使社会实现一体化,不至于走向分裂;另一方面利益的模糊的表达方式,泛化的表达内容使政党不能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要求,政党作为代议工具,民意表达方面这种功能缺失,加剧了政党危机。“选谁都一样”使许多选民放弃投票,造成政治冷漠的直接原因。而过度的政治冷漠会直接造成政治合法性的缺失。
所以,与欧洲的中间化道路相对应的政治现象是极右翼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从法国的勒庞现象到奥地利的海德尔现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极右翼势力的关注。极右翼势力的出现与欧洲的经济状况和移民状况有关之后,选民把选票投给极右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惩罚性的投票,表达对由传统大党及其传统政客控制的政府的贪污、低效、迟钝的不满,对国内各主流政党模糊的政策的一种反动。选民在挑战传统政党的时候,往往宁愿选择缺少政治经验的年轻的精英取代传统政客。1992年46岁的克林顿击败华盛顿的政坛老手布什;1997年43岁的布莱尔取代资深稳健的梅杰;2000年政治经验明显不足的小布什击败曾担任过两任副总统的戈尔,选民渴望变革的要求表达的可谓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尽管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交互技术的发展,电子民主能否取代代议民主制给人类政治带有直接民主制的曙光尚是一个未知数,除了技术的可能之外,代议民主制作为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和对暴民政治的忧患而建构的特殊的政治设置,短期内尚不可能退出人类的政治舞台。代议民主制仍然需要政党这种组织。在承认人民主权的社会里,政党作为一种代议制工具,民意集合和表达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伴随民意的变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是政党生存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