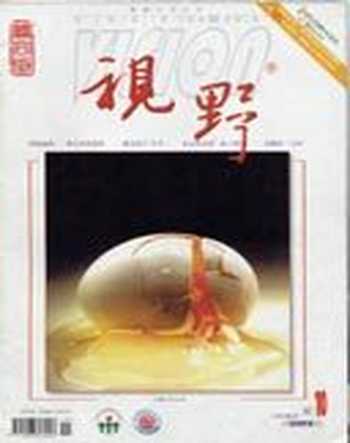爱某一个,爱每一个等
陈蔚文等
爱某一个,爱每一个
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一书中说: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使她摆脱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爱情。如果她真的爱一个人,那么她对其他人的命运不会漠不关心,因为她所爱的这个人和其他人是共命运的,和这个命运是有直接联系的。”
——世间就是这样为爱所串联、兼容。因为爱一个人,我们同时爱他(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师长、友人……最终,我们爱这个世界,这个缺陷与奇迹共存,粗鲁与温情兼在,破灭与梦想同等的世界。
因为爱人住在这个世界。
爱情将相互的命运紧密联结、扭缠,谁也不可能空泛地去爱一个人,要爱,就必得爱他(她)在人世遭遇的所有甜蜜、辛酸、委屈乃至苦痛,爱他(她)被撞得青紫的膝盖,被吹得粗糙的脸,被划出伤口的心,被磨得沧桑的灵魂,爱他(她)背后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对方多疾的母亲、下岗的大哥,或者,贫困的父亲。
爱是一种承担。温暖的、善良的承担。
它那般抽象,又如此具体,它不能被独立、被脱离——爱某一个,其实也就是爱每一个。
只有去爱每一个,爱才不至于自私、偏狭、跋扈,才不容易像脱水的花朵般凋败、萎顿,才能受到更恒久更普遍的祝福。
学会真正去爱一个人,就是学会爱身边,爱世间。
一夜之间,希望发芽结果
〔美〕康纳德·克奇尔
小时候,我每年夏天都要随父母去内布拉斯加州的爷爷那里。
我记忆中的爷爷是佝偻着身子,瘸了腿的。听爸爸说,爷爷年轻时很英俊,很能干,他做过教师,26岁时就当选为州议员了,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患了病——严重中风。
宽阔的原野,高高的草垛,哞哞的牛声,脆脆的鸟鸣使我流连忘返。“爷爷,我长大了也要来农场,种庄稼!”一天早上,我兴致勃勃地说出了我的愿望。
“那,你想种什么呢?”爷爷笑了。“种西瓜”。“唔,”爷爷棕色的眼睛快活地眨了眨,“那么让我们赶快播种吧!”
我从邻居玛丽姑姑家要来了五粒黑色的瓜籽,取来了锄头。在一棵大橡树下,爷爷教我翻松了泥土,然后把西瓜籽撒下去。忙完了这一切,爷爷说:“接下去就是等待了。”
当时我并不懂“等待”是怎么回事。那个下午,我不知跑了多少趟——去查看我的西瓜地,也不知为它浇了多少次水,把西瓜地变成一片泥浆。谁知,直到傍晚,西瓜苗却连影子也没有。晚餐桌上,我问爷爷:“我都等了整整一下午了,还得等多久?”
爷爷笑了:“你这么专心地等待,也许苗会早点长出来的。”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往我的瓜地跑。咦!一个大大的,滚圆滚圆的西瓜正瞅着我笑呢!我兴奋极了——我种出世界上最大的西瓜了!
稍大些,我知道这个西瓜是爷爷从家里搬到瓜地里的。尽管这样,我不认为那是一种游戏,是慈爱的爷爷哄骗孙子的把戏,而是在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心里适时播下的一颗希望的种子。
如今,我已有了自己的孩子,事业上也有所成就。而我觉得自己乐天的性情与成功的生活是爷爷为我在橡树底下播的种子长成的——爷爷本来可以告诉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种不出西瓜,八月中旬也不是种瓜的时节,而且树阴下也不宜种瓜……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让我真真实实地体验了“希望”与“成功”的滋味。
我真的想拥抱你
〔美〕琼·唐纳森 胡向春编译*
去年,我参加辅导儿童读写的志愿活动时,认识了四年级的小学生迈克。他“骨瘦如柴”,才10岁就总喜欢模仿“硬汉”的形象,让我感觉他身上总有一股怒气。
迈克不愿读书,总是板着脸把书“砰”地扔到桌上。他不但写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而且字迹潦草难辨。有时还会冷不丁地冒出些脏话来。我想尽办法鼓励他,总是在他取得一点进步时表扬他,或是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对他的赞赏。
一次,迈克写了一篇小故事,紧接着又顺利通过了测验。这样,他就获得了从礼品柜里挑选一样礼物的机会。迈克挑选完礼物回到座位时,我表扬他学习刻苦,为这份礼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我对他说:“迈克,你非常努力,做得很好,我真的想拥抱你!”
迈克默不做声地摆弄着手中的玩具,然而就在同学们快要回到教室的一刹那,他忽然伸出手臂紧紧地抱了我一下,又很快地跑开了。不管怎样,我拥抱了迈克,这是我早已有的念头。
在我们相处剩下的几个月里,迈克成了班上的模范生。他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功课对他来说轻而易举,每次课后他总要和我拥抱一下。渐渐地,我发现他眼神里的怒气消退了。
志愿活动结束时,我送了一件礼物给迈克。
“我会想你的。”我说。这是真心话,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像迈克这样让我留恋,虽然他长得瘦骨嶙峋,而且总穿着肮脏的牛仔裤和一件黑色的T恤。
“我也会想你的。和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快乐。”迈克回答我。最后我们俩又相互拥抱,这是最后一次拥抱。然后他走回教室,冲我挥了挥手。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就不再有这样的读写辅导,所以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看见他了。
我明白我们在一起的短暂时光不会解决他的所有问题,但是他的每一点进步和他目光中的希望让我懂得,我对迈克的拥抱改变了他幼小的心灵,改变了他的世界。
斑马为什么有黑白条纹
徐静
很久以来,斑马为什么会有色彩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对我来说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在非洲大草原上,这身打扮实在是太显眼了,这使它们很容易成为狮子、土狗之类食肉类动物的攻击目标。而且,就是吃肉的狮子和土狗,也有着与环境相匹配的保护色呢。
斑马为什么有黑白条纹?我曾经多次向人请教过这个问题 。有人一本正经地说,这种条纹可以让智商差点的捕食者分不清斑马的头和尾——有一种鱼就是这样干的,电脑的屏幕保护里就能看到——而众所周知,斑马的后腿十分强劲有力,不小心站到后面的捕猎者必受重伤。我不以为这种说法能有多少道理。有人说是因为斑马天生爱美,还有人说这是造物主一时的疏忽。
昨天闲翻书报,才发现正确答案。原来,在非洲大陆,有一种可怕的昆虫——舌蝇。动物一旦被舌蝇叮咬,就可能会染上“昏睡病”——发烧,疼痛,神经紊乱,直至死亡。科学家研究的结果,舌蝇的视觉很特别,一般只会被颜色一致的大块面积所吸引。对于有着一身黑白相间条纹的斑马,舌绳往往是视而不见的。斑马的条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斑马的选择虽然使它有更多的被捕猎的风险,但也使它成功地躲掉昏睡病的困扰,使它们的群体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现在,斑马已经成为非洲大草原上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
斑马为什么有黑白条纹?我唯心论一点说,这是造物主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成年人的成熟睿智和青年人的充沛精力。你不可能同时拥有舞者的欢呼鲜花和隐者的清逸自在。你不可能同时走上两条不同方向的道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好处都占完了。你总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些什么。你总要学会接受生命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
因为,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