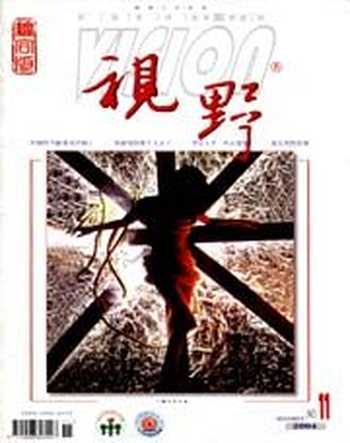我把两罐青春忘在车上
孙梓评
那时年轻,倚靠着围墙就爱眺望所谓远方。围墙之外,只不过是几户矮屋、几亩野田、几棵乱树。那不是我们目光所系之处;我们的眼睛,属于青春的眼睛,还要努力地振翅高飞,跃过西北方一条大河,随着公车行驶的路线,经过普通小镇三两个,来到星星灯火点燃 的彼处,那里有一座圆柱状高塔好似巴比塔,诱惑着我们骚动的身体,要出发,去那里,不特别为了什么。
传说中那座高塔之尖可以旋转,透明玻璃窗轻巧地围出全方位的视野,然后在里头喝一杯咖啡,或是优雅地进行一场晚餐,可以感觉身后天光渐暗,暮色像不死心的潮水一样涌上来,淹没了脚踝、腰身,终于我们咕噜一口气都淹没在黑暗里,无边无际的黑暗就是城市上空的风景,然而其下灯火璀璨,万户人家随着街道的流向蜿蜒四漫,那是何等奢华的梦寐景观,像一张等候得太久的明信片,终于握在手中的时候,应该会有忍不住的泪水滑落吧。
每一日,我们都在持续的眺望中,督促那幢与我们并无实质相关的巴比塔的工程进度,完全无视于校园里庞大的课业压力:难解的几何、无聊的教条主义、秩序颠倒的历史、虚构自满的地理、饶舌结巴的英文字母。那些被称之为知识的,被剪裁成长宽高相等的方形书本,在书包里彼此拥挤。
直到某一堂课中,一枚折叠成星状的纸条隔空飞来,击中了我昏昏欲睡的眉心;推开来,熟悉的字体写着:我们翘课吧。
像是预谋许久,然而只是一时兴起,我们反背着书包,在不应该的时间搭上老公车,去到远方。短短的一个偷来的午后,忙不迭拍动身后隐形双翅,来到巴比塔前,静静仰望它的魁梧。那纯粹是一种对于离开的渴望,希望在城市与原乡之中,借用某一种塔的高度,串连两者:让城市可以俯瞰她的城邦,让远方的原野,知道一个清晰的标识物,以穿越仰望的迷雾。
长大之后,我如愿来到了城市。
基于对城市的迅速认同与过早的熟悉,我们的相处毫无颗粒,溶解得相当完美。
然而,成长所拥有的会不会其实是失落呢!一日一日,一年一年,那座巴比塔始终没有启用,后来辗转听说是因为资金周转的缘故,神话才不得不破灭。然而我独自站立塔前,想知道,破灭的除了巴比塔之梦,还有什么。
更多的高楼矗起。
我们相约前往城市里的另一座高塔,虽然不再有旋转观看的诱惑,但我们并没有对城市的迷恋免疫。崭新偌大的卖场里,有来自各地的生鲜食品,我们驻足在冰柜之前,忽然望见那种传说中好喝的日式桃子酒,取了一个使人为此惆怅的名字:“青春”。
我不假思索便买了两罐。又挑选了一些沙拉、饼干,才满心喜悦地走出卖场。
挥别新的巴比塔,在城市兵马奔腾车流中,我随手招了一辆出租车,车子漂亮地转弯,雨水落下,像暧昧的薄纱,遮掩着这些似是而非的建筑体。
雨越下越大,我仓皇地离开出租车,穿过笔直坠落的雨水,穿过城市暗夜里一条静静燃烧凉意的小巷坐在雪白色系的咖啡馆里,正准备挑选一杯合适的口味,才怔怔然想起:啊,刚刚买的那一袋东西忘了拿下车了。
我把两罐青春忘在车上,也把已经泡软了、不适合出发的自己忘在车上,微凉的夜里,我忽然如此想念那个眺望远方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