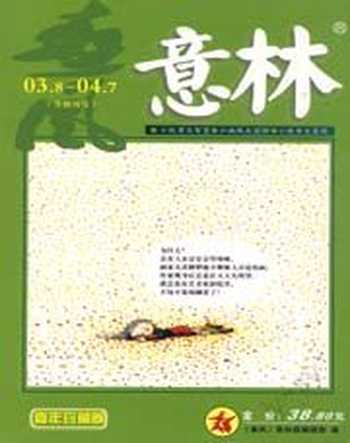穷人的自尊
苁 蓉
丈夫在一所重点中学教书,我们便住在这所学校里。这天,一个女学生来敲门,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位中年人,从眉目看,显然是女学生的父亲。
进得屋来,父女俩拘谨地坐下。他们没有什么事,只说“顺便来瞅瞅老师”。女学生的父亲是特地来看女儿的,他骑自行车走了80多里路。父亲说:“农村没什么鲜货,只拿了十几个新下的鸡蛋。”说着,从肩上挎的布兜里颤颤巍巍地往外掏,布兜里装了很多糠,裹着十几个鸡蛋。
我提议中午一起包饺子吃,父女俩一脸惶恐,死活不肯,被我用老师的威严才“震慑”住。吃饺子时,他们依然拘束,但很高兴。送走女学生和她父亲,丈夫一脸诧异,惊奇我从来都把送礼者拒之门外,为何因十几个鸡蛋折腰,还破例留那父女俩吃饺子?望着丈夫不解的眼神,我微微一笑,讲述了20年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我10岁那年的夏天,父亲要给外地的叔叔打个电话。天黑了,我跟在父亲身后,深一脚浅一腿地去10里以外的小镇邮电局。我肩上的布兜里装着刚从自家梨树上摘下的7个大绵梨,这棵梨树长了三年,今年第一次结了7个果。小妹每天浇水,盼着梨长大,今晚梨被父亲全摘下来了,小妹急得直跺脚。父亲大吼:“拿它去办事呢!”
邮局已经下班了,管电话的是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父亲让我喊他姨爹。进屋时,他们正在吃饭,父亲说明来意,姨爹嗯了一声,没动。我和父亲站在靠门边的地方,破旧的衣服在灯光下分外寒酸。一直等姨爹吃完饭,剔完牙,伸伸懒腰才说:“号码给我,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能打得通不。”5分钟之后姨爹回来了,说:“打通了,也讲明白了,电话费9毛5分。”父亲赶紧从裤兜里掏钱,又让我快拿绵梨。不料,姨爹一只手一摆,大声说:“不要!家里多的是,你们去猪圈瞧瞧,猪都吃不完!”
回来的路上,我跟在父亲身后,抱着布兜哭了一路。仅仅因为我们贫穷,血缘和亲情也淡了;仅仅因为贫穷,我们在别人眼里好像就没有一点点自尊。
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姨爹摆手的动作一直深深藏在我心里,它像一根软鞭时时鞭打着我的心灵。我不会做姨爹那样的手势,给一个女孩子的记忆抹上灰色的印痕。我相信,我今天的饺子将给女学生留下抹不去的记忆,因为爱心的力量总比伤害的力量大得多。
文/《小品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