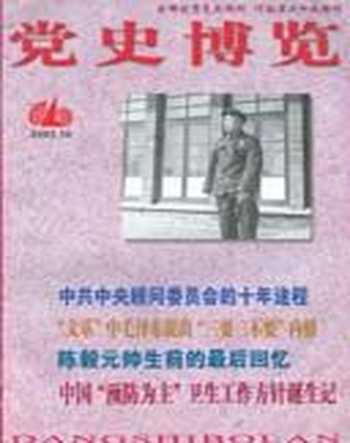漫议“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
鲁 丁
一
搞革命,不但要有对象,还要有依靠力量。“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按照毛泽东的讲话,按照中共中央当时发布的文件,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这对象不外乎三个:一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曰“四类分子”(或“五类分子”)。那么,依靠力量又是谁呢?
工农大众?不是。“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特别是从大中学校开始的。当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工农大众不要介入,不要干预。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过社论(见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至于工宣队进驻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那是后来的事情,而且也是不成功的事情。
广大干部?不是。尽管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曾经自豪地说过:“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珍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套干部,不论是全国解放后的,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甚至北伐战争时期的、建党时期的,有多少没有受到冲击,没有成为革命的对象,可以说是“寥若晨星”,何谈依靠!况且好几年前,毛泽东因为“他们不听话”,就有“洗刷几百万”的打算和计划,这也就是次第实行的所谓“剥笋”政策。林彪还称,“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更是直接把矛头指向干部了。
“文化大革命”首先从大中学校开始,依靠力量是不是广大教师?不是。按照常识和常规,要办好学校,主要依靠教师。新中国17年教育取得了巨大成绩,教师功不可没。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的估计却是:17年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既然从他们“开刀”,当然就不能依靠他们了。
二
“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是什么?究竟是谁呢?……这责任和重担便“历史”地落在了青少年学生身上。从五四运动起,历次政治运动,多是由青少年打冲锋,这是青少年的光荣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也是打冲锋的,且被捧得最高——捧上了天。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这都是上了中央文件的话,也就是必须执行的纲领!事实也正是这样。不论大学、中学,不论哪所学校,都是学生起来造学校领导的反,造教师的反。这种“造反”的残酷性很多,文章多有叙述,这里不再赘述。1966年秋冬的一天下午,我曾到离钓鱼台不远的一所中学去看过。学校没什么人,上了楼,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蓬松着头,正在打扫楼道,劳动很卖力,神情却很惶恐。我没跟她说话。见旁边一间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有三四个十三四岁的男女学生在聊天,我便进去和他们攀谈起来。我问他们,那个打扫楼道的是谁?他们脱口而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说:“她是你们老师吧?”一个女学生粗野地说:“狗屁老师!我们现在监督她劳动,只许她规规矩矩,不许她乱说乱动!”从学校的规模和设备看,这好像是一所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班级的中学。我看到很多教室的门窗都烂了,玻璃也被打碎了,有的还留着玻璃茬子。我看到的这些情况并不典型,也说不上严重,但确实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我觉得中学生“造反”对物质的破坏很多、很大,他们可能由于“青春期孩子的骚动”,表现得特别冲动、蛮横。在“造反”的队伍中,最神气的是他们;穿军装、扎皮带的,也多是他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破四旧”的,主要是他们。中学红卫兵在“文革”中是最横冲直撞的一支队伍。他们说“大学生是策略派”,“中学生是敢闯派”。周恩来当时也指出,“中学红卫兵走得更远一些,做得更激些”。
三
毛泽东除了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表示对青少年的赞扬和支持外,还多次说过鼓励青少年的话。
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说,不要压青年人。又说,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有这样一件事情:几个少先队员给他们的父亲贴大字报,说父亲忘记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只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赏。毛泽东听到这件事后很高兴,他让陈伯达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其实并不只是贴大字报,子女对父母实行“武斗”的也很多。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的一次汇报会上发表讲话:“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子教三娘”是毛泽东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实际情况很形象的说明和概括。叶剑英不止一次地向红卫兵和“造反”群众传达过毛泽东的这个说法。他说:“主席说,过去看旧戏,是看‘三娘教子;现在看新戏,‘子教三娘。”他还说:“毛主席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孙子教爷爷,儿子教老子,青年教育老年。”
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红旗》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第11期发表了《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的评论员文章,其中写道:“令人非常高兴的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说得出,做得到。”“革命的青少年们,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极力赞扬红卫兵“打、砸、抢、抄、抓”的所谓“破四旧”行动,称之为“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广大青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显出了“威风”,他们唱够和唱足了“子教三娘”的新戏。“文化大革命”的局面确实是他们在最高统帅的指挥下“开创”和“打开”的。红卫兵“神通广大”,毛泽东赞不绝口。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说: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历史已有定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浩劫和灾难。广大青少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蒙蔽,在这场浩劫和灾难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需要指出,也有极少数青少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和心理,在“文革”中表现得极其残忍,打人不择手段,杀人……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没有理由也不能过分责备青年,更不用说少年了。“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关键在于领路人。
光阴荏苒,当时十三四岁的少年,如今也是已届或超过“知天命”之年的人了,许多人担任了相当高的领导职务,或成为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因此,适当地作些反思,总结和吸取应有的教训,于己、于人、于国、于民都有益,都必要。也有许多人这样做了,并且做得很诚恳。我认为,由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就是反映这方面情况的一本不错的书。有鉴于此,让我们,特别是以这样或那样的身份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为我们国家从根本上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发挥自己的智慧,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事情。应该说,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