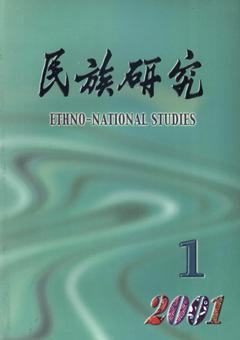元代色目人史事杂考
色目人对元代历史的发展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史籍的基础上,对色目人的一些历史史实作了考察和论述。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忽思慧的族属问题,指出忽思慧其人不应是穆斯林。第二部分全面考察了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的生平仕履。第三部分对元代于阗人非畏兀儿之说予以补证。第四部分对元人关于回纥信奉“佛教”的史料进行辨析,明确指出刘祁《北使记》中有关回纥国的记述真实地反映了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关键词:元代色目人史事
作者尚衍斌,1958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地址:北京市白石桥路27号,邮编100081。
一、忽思慧的族属问题
忽思慧,又称和斯辉,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擢任饮膳太医,主管宫廷饮馔、药物事宜,积累了丰富的营养学知识,缀集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和宫廷日常所用奇珍异馔,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编成《饮膳正要》一书。关于忽思慧的生平仕履《元史》无传,仅凭虞集为此书所作序言,难以考知。至于其族属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蒙古族,另一种认为是回回人。这两种观点中后者拥有更多的赞同者。邱树森和周良霄先生分别在《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部分》忽思慧条及《元代史》中即持忽思慧为回回人说。笔者进一步研读《饮膳正要》后认为,忽思慧为回回人的说法实有重新讨论之必要。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元代回回人的文化含义。有的研究者指出:“元代的回回,指来自西南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成员”。也就是说回回这一概念是时人对蒙元帝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的总称。正因如此,在宪宗蒙哥的圣旨中,回回一词已与木速儿蛮(波斯语Musulman的音译,今语穆斯林)通用。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颁布的《户口条画》中,将伊斯兰教寺院称作“回回寺”,可见元代的官方文书中将回回作为伊斯兰教徒的名称已经确定。周密于宋元之际成书的《癸辛杂识》将寓居杭州的穆斯林称作回回。必须指出,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蒙古统治者将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作回回,但有时亦将非穆斯林成员冠以回回之称,如谓犹太教徒为“术忽回回”,谓来自叙利亚的基督徒爱薛为“爱薛回回”,称信奉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作“罗哩回回”。由此看来,当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群体概念时,“回回”等同于穆斯林,而作为一个民族概念时,“回回”并不完全等同于穆斯林。这一点,白寿彝先生在其《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论述详明,兹不赘议。
如前所述,元代回回可区分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两类。凡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一般都恪守真主的法度,即伊斯兰教法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伊斯兰教法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领域里划定了合法(Halal)与非法(Haram)之界限,对教法认定为非法的事物明令禁止,谁违犯了这方面的禁律,谁在来世将遭受真主的惩罚,也有可能在现世便受到教法的制裁,食物禁律便是其中之一。《古兰经》第五章第三节记载说:“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抵死的、野兽吃剩的动物——但宰后才死的,仍然可吃——禁止你们吃在神石上宰杀的;禁止你们求签,那是罪恶”。
唐宋以来,寓居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教徒被称作“蕃客”、“蕃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恪守穆斯林的食物禁律。对此,北宋文人朱彧于12世纪撰就的《萍洲可谈》卷二记曰:“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日:“汝必欲食,当自杀自食,意谓使其割己肉自啖。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
朱彧的上述记载与《古兰经》有关禁食猪肉的规定大致相合,但有两点仍需加以说明:其一,禁食猪肉的条款系伊斯兰教由犹太教中引入,亦与古代闪米特人的习惯有关,但与佛教(瞿昙氏)没有关系。其二,“自杀自食”、“非手刃六畜则不食”是尊奉伊斯兰教法中禁食物或食用以真主名义而宰杀的动物的规定。
伊斯兰教法中的食物禁律迨至元代仍是入居中国内地的穆斯林们坚守的阵地,这从“断喉法”与“开膛法”的冲突中即表现出来。这一事件在《元史》、《元典章》及《史集》等中外文献中均有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有八里灰回回进京贡海青,皇帝赐之食,贡使不受,称“此食不洁”,皇帝大怒:“你们是我的奴仆,怎能不食我赐予的食物?”于是颁发诏令说:“从今已后,木速鲁蛮回回每,术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休做速纳者,若一日合礼拜五遍的纳麻思上头,若待加倍礼拜五拜做纳麻思呵,他每识者别了这圣旨。若抹羊胡速急呵,或将见属及强将奴仆每却做速纳呵,若奴仆首告呵,从本使处取出为良,家缘财物,不拣有的甚么,都与那人。若有他人首告呵,依这体例断与”。并且明令:以后回回人只能依蒙古法开膛屠羊。关于蒙古人宰杀牲畜的做法是:“必须缚其四肢破胸,人手紧握其心脏”,至到其毙命,这就是“开膛法”。而伊斯兰教法对宰杀牲畜也有明确的规定。首先,宰牲畜前必须诵颂真主之名。因此回回人“非自杀者不食”。其次对宰杀时下刀的位置教法也有明确的规定,刘智在其《天方典礼》卷十七中谓:“故凡宰牲,吾教同人必断其二喉二筋”。此乃文献中所谓的“断喉法”,对穆斯林而言,宰杀羊只不做速纳食之有罪。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穆斯林非但不吃猪肉,即便是不以法宰杀的羊,也被视为不洁,不准食用。蒙元王朝对穆斯林的种种限制,致使“大部分木速蛮商人离开汉地”,元朝贸易因此蒙受损失,统治者不得不收回成命,“有旨允许[以断喉法宰羊]”。元顺帝时,摩洛哥的伊斯兰教徒来华访问。他在杭州受到当地总督(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郭儿台的宴请,“郭君使回教厨役备菜,宰牛烹汤,悉依回教法”。高启《高青丘集·凫藻集》卷五《元故婺州路兰溪洲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记载,回回人倒刺沙倒台后,有人企图嫁祸回回平民,向官府状告日:“回回百余人匿海渚杀猪会饮,谋为乱”。当即被官府识破,理由是“回回不食猪肉,今言杀猪,诈可知也”。可见,元代内地居民对穆斯林的食物禁律多有了解。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元代无论是回回人本身,还是整个社会对穆斯林不食猪肉的食物禁律当已明晓。如果时任饮膳太医的忽思慧是一位严格恪守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想必对回回人不食猪肉的饮食禁律应有一定了解。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编撰的《饮膳正要》一书中多处提到“猪”字。如卷一“聚珍异馔”类中就保留着“猪头姜鼓”这道菜的配料:“猪头二个,洗净切成块;陈皮二钱,去白;良姜二钱;小椒二钱;官桂二钱;草果五个;小油一斤;蜜半斤”。倘若一位穆斯林在其著述中屡屡使用“猪”的字眼,实在是一件煞风景的事。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现在穆斯林聚居相对集中的西北地区一些街道两旁悬挂着的“大肉店铺”的牌匾,“大肉”乃是当地汉人及穆斯林对“猪肉”的另一称谓。这一名称的真正含义对于久居内地的汉人来说未必人人知闻,但长期生活和工作于西北边疆的穆斯林和汉人似乎人人明晓。遗憾的是,我们
目前还没有在文献中发现元代穆斯林是否也会像今人一样用“大肉”或别的一些什么名词来替代“猪肉”的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禁食猪肉的穆斯林决不可能满口“猪”字。
又,根据元人虞集于天历三年(1330)为《饮膳正要》所作序言可知,忽思慧尝为赵国公常普兰奚下属,两人关系甚为密切。《新元史·常咬住传》亦谓:常普兰奚于延祐二年(1315)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徽政院使,掌侍奉皇太后诸事。且虞集序中尚存“褒颂”圣后之语。可见忽思慧在元廷中是以饮膳太医的身份侍奉皇太后答己与皇后卜答失里的。虞集和忽思慧为同时代人,且受圣上之命为此书作序,所记不应有误,况且忽思慧作为宫廷膳医的身份还得到《新元史》的印证,如此看来,虞集的上述记载是可信的。
既然如此,有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什么元仁宗会选中一个回回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事?蒙古与回回饮食习惯各异,在宰杀牲畜中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开膛法”与“断喉法”。对穆斯林而言,宰杀不以法便是不洁,食之有罪。显然,蒙古皇室只能依照开膛法宰杀牲畜,身在皇宫的忽思慧能否享用到以“断喉法”宰杀的羊肉?如果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又如何以不洁(即按“开膛法”宰杀的羊)的肉为皇太后和皇后膳疗进补?作为蒙古皇室和忽思慧本人双方是否都能接受这种现实?这实在令人费解。
此外,饮酒同样亦被伊斯兰教法视为大逆不道。《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说:“凡是穆斯林喝酒者,须鞭打八十,并在地窖内关押三个月”。然而,《饮膳正要》的作者在该书卷一中不仅列有“饮酒避忌”,而且规定“饮酒时大不可食猪、羊脑”,这似乎也与穆斯林的身份不合。唐人杜环在《经行记》中记载说:大食人“断饮酒,禁音乐”。伊斯兰法中关于禁酒的规定是逐步形成的,起初《古兰经》中曾将用椰枣和葡萄酿制的醇酒视为安拉给人类的恩赐,后来鉴于信徒中有人饮酒后妨碍宗教活动,遂降示新经文,指出饮酒害大于利,再后来明令予以禁止。倘若忽思慧是一位具有丰厚伊斯兰文化背景的穆斯林——木速蛮回回,这些规定应当知晓。实际上,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一书中的揭示与伊斯兰教法的相关规定大相径庭。种种迹象表明,忽思慧并非是一位纯正地道的穆斯林,至于他的确切族属有待日后详考。
二、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的生平仕履
关于鲁明善及其《农桑衣食撮要》一书,魏良弢和王治来先生分别撰文作过一些研究。今天重读这两篇文章,仍受到不少启发。笔者最近翻阅元人虞集的《道园类稿》,在该书卷四十三中发现了《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该碑刻记录了鲁明善的生平仕履和家庭情况,但前人未能充分利用。今据此碑并结合其他史料对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的生平作一考释。
鲁明善,《元史》无传。据《神道碑》记载:“公,讳铁柱,以明善为字,而以诚名其斋。”明人林钺、邹壁编撰的《重修太平府志》卷三《职官志》中有关鲁明善的字、号与《神道碑》相同,当无误。明善之父迦鲁纳答思,畏兀儿人,为高昌名族,《元史》卷一百三十四有传。史载:迦鲁纳答思“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由于翰林学士承旨安藏的举荐,奉召入朝,受命为国师(八思巴)讲法。国师是吐蕃人,言语不通。忽必烈命迦鲁纳答思从国师学习其教法及语言文字,不久皆通。他以“畏吾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现藏德国编号为TM14(U4759)号的吐鲁番文书为一份佛经残件,其中有一篇是用头韵诗写成的题记,提到了一位名叫Karunadaz的人,就是迦鲁纳答思。该题记云:“这项最优秀的翻译作品由迦鲁纳答思Sidu(释都)圆满而又无遗漏地实施并完成了。翻译地点在大都(今北京)精美奇妙的白塔(Stupa)寺中进行,时间吉祥的虎年,十干(Sipqan)之壬(sim)年七月”。如此看来,迦鲁纳答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据《元史·迦鲁纳答思传》记载,他曾任世祖朝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后尽忠于成宗、仁宗两朝。
迦鲁纳答思久居汉地,其子明善自幼研习“圣贤之学”并“因父字取鲁以为氏”,担任宫廷必阇赤,为天子主掌文史。后因世荫及其贤廉被授以奉议大夫、使佐江西行省狱讼之事。延祐初年,仁宗帝念其父迦鲁纳答思为朝廷重臣,特命鲁明善为中顺大夫、安丰路达鲁花赤,赴任前仁宗帝亲赐“白玉之鞍”及“御服”相勉。在安丰任职期间,他“修学校,亲率弟子,为之讲明修农书,亲劝耕稼。从义役而民力始均,理狱讼而曲直立判”。由于鲁明善政绩益著,“郡人惧其去而后来者改其成法,乃刻石以识”。秩满以亚中大夫任太平(郡守),以往该地“无赖夺货于市,豪民夺人之妻,皂隶旁午索钱”。鲁明善至,“按以天子之法,而郡以治”。太平之地有娥眉亭,郡人为之立碑以记其政绩。此后,明善转兼池州(辖境相当今安徽贵池、青阳、东至等县地)、衢州(今浙江衢县)等地。衢州“郡有古堰水,可灌田数百顷,士民有擅其利者,民不可言,吏不敢制。”明善“按以法,水利均及于民,不待治而安矣。”延祐三年(1315),他转兼桂阳,同安丰、太平、池州、衢州四郡相比,桂阳最为远小,明善受命赴任。到官之始,岁遇大旱。明善以粟赈饥,“郡人活焉”。然为时不久,桂阳蛮僚又起,道、州、帅、府檄公(指鲁明善)督之。“公明赏罚,示好恶,绝奸吏,兵法严整,而力求所以生之之道。叛者悦服,不战而定。邻郡虽干戈,公处之皆按堵。”由于鲁明善久事于江海间,京师执政的故旧无不为之惋惜,丞相亦欲留其为某部郎官,明善以“吾老而贫,得一小郡以治斯足矣”之言谢绝。晚年他任靖州路达鲁花赤,为政勤勉。
鲁明善足迹遍及六郡,治政有声,其中安丰、太平、池州三地为之刻石或立去思碑。明善平日好鼓琴,得古人之意,亲定《琴谱》八卷。此外,又撰《农桑衣食撮要》二卷行于世。
三、于阗人非畏兀儿补证
元代畏兀儿人的主体是唐代回鹘人的后裔。早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就有一些回鹘部落徙居天山以北和河西一带。公元9世纪中期,回鹘汗国崩溃,部族离散。其中有一支迁至天山东段南北诸地,宋、辽、金时代的汉文史料称之为“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这就是后来畏兀儿人的前身,他们分别以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哈喇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彰八里、仰吉八里、唆里迷为中心形成畏兀儿地面。哈密里(今新疆哈密)在元代不属于畏兀儿,它应是一个与畏兀儿地面并存的封建地方政权。同样,元代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地区居民的族属问题始终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杨志玖先生认为:“居住在今新疆西部的斡端(今新疆和田)人、可失哈尔(今新疆喀什)人是畏兀儿人,但被称为回回,信奉伊斯兰教”。陈得芝先生在《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一文中明确指出:元代的于阗人实泛指中亚人。笔者赞同陈先生的意见,并就此作些补证。
首先需要指出一点,元代的维吾尔族应以畏兀儿人为主,同时包括曲先(今新疆库车)人、斡端人、哈密里人、可失哈尔人等,他们都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但用“畏兀儿人”来统称元代整个维吾尔族是不合适的。
学人谂知,畏兀儿是部族名,而于阗则是一地理概念。元人对此区别甚明。王恽《乌台笔
补》记载说:“早得钦奉先命圣旨节该:斡脱做买卖、畏吾(兀)儿、木速儿蛮回回,交本处千户、百户里去者”。在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颁布的《户口条画》中,畏吾(兀)儿户作为一类户计登记入籍,而与蒙古户、回回户、河西户、契丹户、女真户、汉人户相区分。又如:“至元五年三月丁丑,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由上引史料可以看出畏兀儿同蒙古、回回等是以族名形式出现于元代史文的,这是一种不争的事实。然而,还留有些许争议余地的则是于阗人是否属于畏兀儿人系统?这一问题似乎也引起元人的注意。他们称“高昌回鹘”为畏兀儿,把于阗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回鹘人称作“回回”。元末明初儒士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于阗玉佛”中有“丞相伯颜尝至于阗国”的记载。可见,在元代文人看来于阗国王与畏兀儿亦都护之间并无隶属关系。翻检《宋史·于阗传》和《宋会要辑稿·蕃夷传》有关史料发现,汉地史官把于阗国首领称“黑韩王”。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记载说:“绍圣三年(1069)五月七日,枢密院言: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于阗国进奉般次罗忽都卢麦等进奉方物,黑韩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上表……”此类记载很多,笔者无意缀集史料、详备援引,只是想说明在宋代于阗国首领的确称“黑韩王”。魏良弢先生考证认为,这个“黑韩王”乃是喀喇汗的汉译。其时,于阗国已是喀喇汗王朝的一部分,故有此称。《宋史·高昌传》载日:“太平兴国六年(981)其王始称西州外甥师子王阿厮兰汗”。“阿厮兰”、“阿萨兰”等,是突厥语Arslan一词的音译,意为“狮子”,唐至元代中亚具有突厥语背景政权君主常以此为名号。显然,高昌回鹘同于阗国王在首领的称号方面亦不相同。由此看来,在13世纪初于阗应是一个与畏兀儿地面并存的地方政权。据《元史》卷七记载:“至元八年(1271)六月,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等处居民。”其中斡端,即指于阗(今新疆和田)。其后以斡端封给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至元十一年(1274)四月,诏安抚斡端、雅儿看(叶儿羌)、合失合儿等城。十八年(1281)诏谕斡端等三城,是知斡端为阿鲁忽封地。此外,斡端等地也是忽必烈与西北叛王争夺的场所。至元年间(1271—1294)尝置斡端宣慰司都元帅府于此。
有些内迁的西域人则以于阗为籍贯,如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一《资善大夫中政院使买公世德之碑铭》记载于阗人买述丁的谱系:马合麻——撒的迷失——阿合麻——买述丁。业师陈得芝先生考证认为,上引《碑铭》中的马合麻是从不花剌迁来的,而并非来自于阗。哈八石,于阗人,登延祐二年(1315)乙卯科进士。其父勘马剌丁,仕至广州盐课提举,娶牙里干氏,此“牙里干”应即“雅儿看”,今新疆莎车(叶儿羌),而其祖担任牧民官之“邵儿千”,亦应为“邪儿干”之误。“雅儿看”属于阗地区,哈八石的祖籍当确属于阗人。
在上举两例中,就有一家和于阗毫不相干。为什么碑传资料称他们为“于阗人”?原来于阗一名除特指于阗外,在文人笔下还有另一含义。马祖常《石田集》卷九《送李公敏之官序》记日:“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人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百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于是可谓盛矣。”此序谓李公敏为于阗人,然其家世不详,无法判断其真实本贯。但上引材料中的“于阗”一名与朔方、大食并列,显然不是专指于阗地区,而是用作西域(或中亚)的代名词。又,廉希贡是廉希宪之弟,布鲁海牙之子,出身于畏兀儿世家。对此,《元史·布鲁海牙传》、《南村辍耕录》卷七《待士》及《书史会要》均有明确记载,然而元人鲜于枢所撰《困学斋杂录》记日:“两浙都转运使廉希贡……公于阗人。”这里为什么会将廉希贡的籍贯误记为于阗,或许是不明沿革任意篡改所致。元明时期的史官往往把籍贯不明来自西域或中亚的色目人统称为“西域人”,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如《弘治岳州府志》卷七《名宦》中的别都鲁丁、《嘉靖定海县志》卷十三《流寓》中的丁鹤年以及《弘治直隶凤阳府宿州志》中的木撒飞、马思忽等均被记作“西域人”。反之,将于阗作为西域的代名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关于回纥信奉“佛教”的史料辨析
佛教是元代畏兀儿人的主要宗教之一,这已成为学术界不争的公论。对此,葛玛丽、安部健夫、杨志玖、刘迎胜、荣新江等中外学者均有专论。笔者无意缀集相关琐碎的史料就此再予复说,这里只想就元代旅行家关于回纥信奉“佛教”的一些史料作些辨析。
自唐末至元初的数百年中,佛教在畏兀儿地面久兴不衰。13世纪20年代邱处机西行朝觐成吉思汗,途中经“鳖思马(即别失八里)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道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泊于城西蒲萄园之上阁……侍坐者有僧、道、儒……,有龙兴西寺……寺有佛书一藏……”。“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儿与镇海有旧,率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洎其夫人劝蒲萄酒……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②上引史文显示:其一,在畏兀儿人相对集中的鳖思马和昌八剌城流行着佛教,建有佛寺。此外,道、儒并行。其二,邱处机对回纥与畏兀儿的概念已有所区别,但十分模糊。如“至回纥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儿与镇海有旧”。笔者以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显然是将族名误作为人名。更有趣的是他们已经知晓回纥(指回回)信奉伊斯兰教。刘祁所撰《北使记》似乎对回纥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将回纥分为没速鲁蛮回纥、遗里诸回纥、印都回纥。黄时鉴先生考证认为:没速鲁蛮回纥指河中地区和花剌子模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人和突厥人,遗里诸回纥是指也里一带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人,实际指呼罗珊地区之居民,而印都回纥则指呼罗珊以东迄至印度河上游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这一科学的分析甚为精当,也就是说金元之际史文中出现的回纥之称即指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而“伊斯兰”一词出现在汉文文献中,应首推《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其载:“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诏曰:‘此人非隶朝廷番部,不须发谴,可于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毋令失所。”
“览”字在古汉语单韵中,以-m收声,所以以“移习览”一词对译Islanm,其音正合。学术界现在一般认为“移习览”一词是Islanm在汉语中最早的音译形式。因此上引文中的回纥未必特指畏兀儿。王恽在《秋涧集》卷九五《玉堂嘉话》中记载曰:“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理解刘郁《西使记》中“三月一日过赛蓝城,有浮图,诸回纥祈拜之所”的记述?此赛蓝城当指今哈萨克斯坦之奇姆肯特以东地区,似无问题。《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的“赛拉城”与上述“赛蓝城”的关系不甚明了,伊本·白图泰明确指出:“赛拉城,是苏丹乌兹别克
的京城。……该城有清真大寺十三座,供聚礼之用,其一是供沙非尔派用的”。而“诸回纥祈拜之所”应指供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做礼拜用的清真寺(masjid)。对此,陈得芝先生已考详明,且与穆斯林作家的记载可相印证。现存争议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有浮图”的记载,有的研究者解释说:“从此记载看,13世纪50年代,此地(指赛兰城——笔者注)仍有信奉佛教者”。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请看刘祁《北使记》中有关回纥(指回回——笔者自注)国的另一段记载:“其食则胡饼、汤饼而鱼肉焉。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髯者,并业歌舞、音乐。……其书契、约来并回纥字。笔苇其管,言语不与中国通。人死不焚,葬无棺椁,比敛,必西其首。其僧皆发,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惟和、沙州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这段材料较真实地反映了穆斯林社会的宗教生活,其内容涉及妇女服饰、丧葬制度的诸多方面。唐人杜环所作《经行记》记载大食妇女的装饰时提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这与刘祁关于回纥国妇女“面亦衣,止外其目”的记载相合。这种特殊的风俗在伊斯兰教法中有法律依据,《古兰经》中主张男女有别,规定穆斯林妇女“要目不邪视,掩蔽自己的面部。不显露自己的装饰,可在外显露的除外,要把头巾下垂衣领上”。至于穆斯林的丧葬也有种种规定,一是以布缠身入敛;一是土葬。教法反对使用棺椁,并且规定,在墓穴中要使亡人面朝天房。刘祁文中“人死不焚,葬无棺椁,比敛,必西其首”即指此意。然而,对于长期生活在内地并非穆斯林或对伊斯兰文化知之不多的刘祁来说,误将“木速儿蛮”称作“僧徒”无可厚非。但必须指出,刘祁的观察仍极为细致,“其僧皆发,寺无绘塑,经语亦不通”,这些已深深引起了他的疑虑。不过,他对“和(当指和州、火州,即今新疆吐鲁番)、沙州(今甘肃敦煌)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的记载颇符合实际。至于刘郁在《西使记》中记载“赛蓝城”出现的“浮图”之误,笔者以为原因如下:依照伊斯兰教的习俗法,为召唤穆斯林按时礼拜,清真寺中设立了宣礼楼(Midhanah),由于波斯语中“召唤”一词作Bang,因而又将其称作“邦克楼”。宋人方信儒著《南海百咏》中的“蕃塔”、岳珂《桯史》中的“率堵波”、郑思肖《心史》中的“叫佛楼”均指清真寺中的这种塔。元人刘郁大概也犯了南宋诸学者同样的错误,故将“赛兰城”中供回纥(回回)祈拜之所——清真寺中的塔,误作“浮图”。
[责任编辑华祖根]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