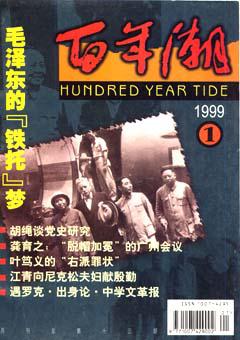我的父亲朱自清(续完)
朱乔森
中国终于抗战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对外,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16日,三万多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军警“自由行动”。游行队伍同军警的大刀、水龙进行了英勇的搏斗。这天,父亲本是受命去劝阻学生的,却毅然跟学生们一道,参加了游行。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虽然很担心他们流血,但仍真诚地支持了他们。不久,国民党军警特务到清华进行搜捕,六名同学(其中有韦君宜)一整天躲在我们家中。父亲无论是抗战前或抗战后,曾多次在家中掩护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
国土的沦丧,强敌的深入,使父亲不能再沉默。他这时写了多首爱国歌词来鼓舞青年,也一舒久久压抑在自己胸中的块垒。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二十天后,北平沦陷。父亲在散文《北平沦陷那一天》中写道:“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久是咱们的!等着瞧罢,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
这年9月,父亲秘密只身南下,辗转千里来到长沙。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最负盛名的大学合并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父亲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系主任),并担任为学生解决经济困难的贷金委员会召集人。次年2月,临大又不得不迁往昆明。途中,拖拽船只上水的纤夫们那悲恸的呼喊,使他深受感动,成诗数首,表达了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例如:
龟行蜗步百丈长,蒲伏压篙黄头郎。
上滩哀响动山谷,不是猿声也断肠!
4月初,临大改为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父亲继续担任中文系主任兼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随即跟联大文法学院一道迁往蒙自。在那里,同从北平赶来的母亲及我们几个孩子会合,不久,又迁返昆明。
10月,广州、武汉继上海、南京等城市之后失守,国内外对中国抗战的悲观论调,一时又起。父亲却与这些人不同。他虽然颠沛流离,生活不安定,且越来越困苦,精神却极为兴奋,因为中国毕竟抗战了!“七七”抗战两周年的时候,他写了短文《这一天》,热烈歌颂人民的觉醒:
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
正是从人民的奋起中,他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1944年又写了《新中国在望中》,认为中国必将从民主化、工业化中新生。
一切为了抗战
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却越来越腐败,以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民不聊生。父亲上有垂老的双亲,下有七八个子女,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1939年11月,他不得不辞去联大中文系主任等行政职务而专任教授。次年,为生活所迫,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迁往物价相对便宜些的成都。父亲也在这年到成都休假。一家人住在从一所尼庵租来的三间茅屋内,房顶是稻草,墙是泥糊的竹篱笆,地上连一层砖都没铺。这潮湿之极的环境,加上营养的缺乏(食米还要经常靠亲友接济),使我们几个孩子都连续得了重病。这就是父亲在《近怀示圣陶》一诗中所说的:
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距躟孰能主?不忧食无肉,亦有莱圆肚。不忧出无车,亦有健步武。只恐无米炊,万念日傍午。况复三间屋,蹙如口鼻聚,有声岂能聋,有影岂能瞽?妇稚逐鸡狗,攫人如网罟,况复地有毛,卑湿丛病蛊。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盬!……死生等蝼蚁,草木同朽腐……
这首风格近于杜诗的长诗,也同杜诗一样写的不仅是个人的苦难,同时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反动统治下的苦难。
1941年,父亲一个人回到昆明,第二年就赶上了一个最寒冷的冬天,他穷得连御寒的棉衣也添置不起,只好在集市上买了一件赶马人用的披风,披着它从乡下步行约二十里进城上课。加之营养不良,他的胃病愈发严重,几乎每两三天甚至一两天就发作一次,给他带来极大痛苦。他的身体不仅日渐憔悴,简直被折磨得形销骨立,头发像铺了一层霜。四十出头的他,已经像个老人了!
父亲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痛苦。他认为抗战第一;为了抗战,个人和家庭总是要作出些牺牲的。在上面那首长诗中,他还写道:“健儿死国事,头颅掷不数。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蝼蚁自贪生,亦知爱吾土。”“天不亡中国,微忱寄千橹”!橹,大盾牌,在这里比喻千千万万的抗战将士。为了他们,为了“吾土”,谦称“竖儒”的他,是愿为中国的弦诵不绝而受苦的。
然而,事实在教育着他,他那高度的正义感也促使他认清现实的真相。1941年天旱,米价又大涨,成都农村的大批贫苦人民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得不一群群地起来“吃大户”,抢米仓。国民党以“共产党煽动”的罪名,残酷地镇压了这次人民的自发行动。父亲目睹了这幅饥民求食图,受到强烈的震动。他后来写的《论吃饭》这篇文章,就在字里行间对贫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父亲这个时期的散文,不但在艺术风格上继续发扬了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内容上,在反映时代上,较之过去更前进了一步。如他在《语文影及其他》一书自序中所讲的:“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玩世主义盛行的时候,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时代,作者大概很受了些《语丝》的影响。但是,三十年代渐渐的变了,四十年代更大变了,时代越来越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哪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
对于自己长期坚持的追求“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的爱国理想,经过反复的思考,1943年他这样写道:“理想上虽然完美,事实上不免破烂;所以作者彷徨自问,怎样爱它呢?真的,国民革命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以来,我们都在这般彷徨自问着——我们终于抗战了!”这是说闻一多先生的,也是在说他自己。他认为抗战既“是坚贞的现实,也是美丽的理想。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这便是理想。理想是事实之母;抗战的种子便孕育在这个理想的胞胎中。”因为“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了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中国是自己的。……固然完美的中国还在开始建造中,还是一个理想”,但是父亲说,他想借用美国的一句话:“我的国呵,对也罢,不对也罢……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他又说:“要‘抱得紧,得整个儿抱住;这就得有整个
儿理想……包孕着笼罩着整个现实的理想”——那便是“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正是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现实的,也是理想的。”
父亲说出了抗战前许多爱国者心中的苦闷:确实,频繁的内战使中国四分五裂,一届届政府不维护中国的却维护外国的利益,使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国家究竟在哪里?父亲在总结了这些痛苦的经验后,要求一个“咱们的中国”,也就是一个大众的、人民的中国。是的,在抗战中,他进一步认识了时代,发现了“大众的力量的强大”,因而使自己的作品采取了更严肃的态度,并开始自觉地“面向大众,诉诸大众”。他前进了!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为了欺骗社会舆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曾经对少数上层知识分子实行笼络政策,几次请父亲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去做官,国民党在昆明、成都的某些“要人”也几次对他表示特殊“关怀”,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他宁肯继续过一个穷教授的生活!他在逐渐分清大是大非和逐渐认清中国的未来。1945年暑假,他从昆明回到成都时曾对母亲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这不是容易的简单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人也许走得没有年青人那么快,但是,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着走!”
从抗战到逝世,是他身体最坏的时期,但却是他无论在教学工作上、学术研究上,还是文学创作上,出成果最多的时期。教学方面,他开了“宋诗”、“李贺诗”、“谢灵运诗”、“文辞研究”、“中国文学史”等许多门新课。仅从《中国文学史讲稿提要》所征引的典籍的广泛性,我们就不难看到这些年他下了多么大、多么深的功夫!学术和文学方面,连同与叶圣陶先生合著的三本,他一共出了十本书,另外还写了七八十篇文章。他的《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书,都是深具功力的。《经典常谈》高度概括而又比较系统地向一般读者介绍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它力求通俗化,又力求采择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因而今天还受到许多青年和中学语文老师的欢迎。特别是对于诗,无论是古典诗歌或新诗,他的研究都系统化了。他对一些基本概念如什么是赋比兴等所作出的新的正确解释和关于新诗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散文创作方面,则着重加强了说理,以适应抗战的时代要求。
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是当天深夜传到我们家们的。父亲立即兴奋地走上大街,和老百姓一起狂欢了一整夜。但回到家里,他却心情沉重地对母亲说:“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不起内战,国家的经济可以恢复得快点,老百姓也可以少受些罪。”
他的这点希望,很快就被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现实打碎了。几个月后,国民党军警特务就在昆明惨杀了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父亲“悲愤不已”,“肃穆静坐二小时余”,并亲往西南联大图书馆灵堂,向死难的四烈士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敬意。
1946年6月,父亲最后一次到成都,准备举家迁回北平。是月下旬,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新的全国内战因而爆发。7月中旬,又传来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父亲和闻一多虽然说不上是挚友,但这位爱国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的死,特别使他悲愤和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李公朴街头遇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这是什么世道!”他接连写了两篇悼念文章,指出“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可是“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尸最后这句话,一再被父亲写进他的文章,说明他已下定了同反动的法西斯统治作斗争的决心。
他已经十多年不写新诗了,这次,强烈的愤慨使他又拿起笔来写了一首。诗中歌颂闻先生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照见了魔鬼”的火;相信在这火的“遗烬里”,必将“爆出个新中国!”
8月18日,成都各界人士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事先就传闻特务要捣乱会场,许多人不敢参加了。父亲毅然出席大会作报告,介绍闻先生的生平业绩,正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这个悲愤而又真挚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全场多次鼓掌,许多人都被感动得落泪了。
1946年10月间,父亲带领我们一家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因为清华园正在修葺,临时住北大四院。利用这个机会,他带笔者步行到天安门一带观览,不想却看到美军大卡车在三座门附近撞死一名中国妇女后扬长而去。联想到前不久在重庆,也是他带着笔者,看到美军吉普车一下子撞死撞伤了四五个中国人,司机还满不在乎地跷着二郎腿在抽烟……他逛天安门的兴致全被打消了,往回走的一路上,都沉闷不语。没过两三天,又看到警察“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三轮车夫一顿拳打脚踢”,父亲愤怒地上前跟警察讲理,高声说:“他们是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回来的路上,他非常激动地对母亲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该挨打?真可恶!”他深切地感到:他爱着的“北平是不一样了”,“穷得没办法的人似乎也更多了”,“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了”;“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加上被群众称之为“劫搜”的国民党大小官吏的“接收”和军警宪特的横行,普通老百姓确实苦不堪言。父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能平静。他大声地喊出:“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他热烈地为人民“起来行动”辩护,深信“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他的心同在压迫下挣扎和反抗着的人民进一步连在一起了。
父亲一回到清华园,就抓《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和出版,把这看作是对亡友的纪念和对法西斯的抗议。1946年11月,以他为召集人的“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组成。此后一年间,他收集遗文,编辑校订,拟定目录,花费了许多精力,并亲自为编定的《闻一多全集》写了序和编后记。在他的主持下,整个清华中文系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正如吴晗先生所说:“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集的。”全集终于在:1948年他逝世前的一个月出版,他可以告慰亡友于地下了。
1947年,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一下子逮捕了两千多人。父亲痛恨这种大规模迫害人民的暴行,签名于“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由于公开发表时,他的名字是第一个,宣言在当时的报纸上曾被称作“朱自清等十三教授宣言”。这立刻招来了反动舆论对他的围剿。国民党发动各家反动报纸拼命地诽谤、攻击他和其他签名的教授,国民党特务也三次到我们家寻衅。然而,父亲没有退却。他在反动派面前坚定地站起来了!
国民党多年的黑暗统治,使他毅然决然地同当时的学生运动,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站在一起了。从1947年到他逝世这一年半时间,他写的四十多篇文章和多次在学生集会上的演讲,正如他在《论雅俗共赏》一书自序中所说,都是在朝着“近于人民的立场”这个方向说话的。父亲主张使新的民主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指出抗战胜利后,文学紧缩了那严肃的尺度而强调人民性,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并高度评价了解放区作家和人民打成一片,成为“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这种新的文艺方向。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使读者更会躲向那些黄色、粉红色的书刊里去。在《论标语口号》一文里,他颂扬了革命的标语口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要避免落套子、公式化;那些装点门面、口是心非的标语口号,“终于是不会有人去看去听的,看了听了也只是讨厌。古人说:‘修辞立其诚。标语口号要发挥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都是遮掩不住的。”他真诚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但不说过头话,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专长,积极提出有益的建议。他的散文中所讲的上面这些道理,至今读起来还感到非常亲切。
在《论气节》这篇文章里,父亲还充分肯定了五四以来青年知识分子用正义的斗争行动代替消极的“气节”这种“新的做人的尺度”。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新的认识。他说到做到,不但继续在一些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宣言上签名,有时还亲自去征集签名;并且还主动为清华的教授们起草了反饥饿反迫害、罢教一天的宣言。
人格的升华
父亲的晚年,可说是完成了自己灵魂的净化。李广田先生说他有“最完整的人格”,他的同事和学生也说他有“完美的人格”,并且还出版了两本同名的集子。在父亲晚年同他相处较多的李广田,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他何以是“一个最完整的人”:第一,他“是一个有至情的人”。他对同事,对朋友,尤其是对晚辈,对青年人,都是毫无保留的诚挚与坦白,都是处处在为对方打算。“他是这样的:既像一个良师,又像一个知友;既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兄长。他对任何人都毫无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与谦恭里面。”第二,他“是一个最爱真理的人”。凡是认识他的,跟他同过事的,都承认他是最“认真”的人。“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自己的私事认真,别人或公众的事他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凡是公家的东西,他绝不许别人乱用,即便是一张信笺,一个信封。”第三,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说是有幽默感亦未尝不可,但他从不为幽默而幽默。“他的风趣之可爱可贵,正因为他的有至情,爱真理,严肃而认真。”
晚年的父亲,在我们子女的感觉中,的确是“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他尊重我们的政治选择,从不干涉。他要求我们为他做任何事时都要说“请”,说“谢谢”。这不是一般的礼貌,而是源于更深刻的对我们人格的尊重和关心。特别使我们感到他人格的纯净的,是在公私关系上。他当时的收入虽远远不敷支出,身体也已衰弱不堪,却从不占公家一分便宜,包括李先生所说的一张信纸、一个信封。对我们的要求也极其严格。一次学校在我家门前倒了一堆黄土,六岁的妹妹要拿些来玩,父亲也不许,说“这是公家的”。抗战胜利后初返清华园,我们从日本人扔的破烂儿里拾回一张破桌子,父亲竟少有地大发雷霆,说这是公家的,让立刻送回去。他处处想着的,都是“公家”,都是别人,都是人民大众。父亲所留下的这种正气,确乎是我们终身受用不尽的。
父亲晚年人格的纯净,还表现在他勇敢地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向新时代学习。他向自己的学生借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各种革命读物来看,甚至向当时还是中学生的笔者借了通俗的革命宣传小册子来看,并在日记中写道:“这本小册子观点鲜明,给人以清新的思想。”他从不故作高深,鄙薄这些通俗的革命读物,既然认识到向新时代学习的必要,就认认真真地学起来。他和进步同学谈话,是那样认真地倾听,像是个在虚心求教的小学生。他的进步和他的治学同样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往前走,绝不做虚有其表的事情,也没有当时某些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浮夸气。
当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一辈子不苟言笑而又身患重病的父亲,竟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学起扭秧歌来了。有人曾大不以为然,认为这对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来说,是可笑的,无法理解的。而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日趋疯狂的情况下,像他那样的人参加这种文艺活动,也确有再次成为被攻击对象的危险。然而,在1948年中文系的元旦晚会上,父亲却又一次兴奋地和大家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使许多师生为之感动,并留下了亲切的记忆。
他的人格的净化和升华,也表现在他的散文风格上。在《标准与尺度》一书的自序中,父亲说:“复员以后,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他感到人民需要他写,需要他这支笔为他们服务,需要他为新时代的来临多作些催生的呐喊。他这个时期的散文,不仅更加精炼、明达,而且在先前已经转向说理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群众斗争的需要,把道理讲得更加通俗、明白、透彻了。他用历史的方法来说理,仍旧是那么诚恳谦虚、平易质朴,使人们在作者的亲切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新时代的精神,不感到有半点说教气。这说明他的散文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更加成熟了。
1948年,父亲快五十岁了。在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的身体被疾病连连折磨得更加痛楚不堪,但他的思想、感情却更年轻了。他把近人改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而成的一副联语,亲笔抄在一张宣纸上,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来表明自己的心境,作为对自己的勉励: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人格和心灵的净化,使他撇开了一切个人的烦恼和痛苦,而乐观地期待着一个新的“咱们的中国”的出现!
“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48年春天,蒋介石要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时,清华竟有个别教授积极“竞选”所谓“国大代表”,跑来要父亲投他一票。父亲断然告诉他:“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他的票,别人的我也不投!”表现了对国民党伪“国大”的极大蔑视。在这前后,父亲还拒绝了一些老朋友要他参加一个中间路线刊物——《新路》的邀请。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向上爬,做人民头上统治者的帮闲、帮凶;一条是向下去,同人民在一起争取解放。“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1948年6月18日,父亲签名于《抗议美
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宣言的全文是:“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拒绝购买每月的两袋美援平价面粉,相当于全家的收入每月要减少五分之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父亲虽是当时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但每月的全部薪水也只能买三袋多市价面粉,家庭人口又多,每天吃两顿粗粮,还得他带着一身重病,拼着命多写文章,才能够勉强维持下去。虽然他的胃病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签名的前几天体重已减到38.8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名,并在几天后让笔者把配购证给退了回去,拒绝了这种“收买灵魂性质”的施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气节。
正像吴晗先生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一文中所回忆的:“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的签上他的名字。”
直到弥留之际,他还谆谆嘱咐母亲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过名的,以后,不要去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对父亲这一行动给予了很高评价。文中提出:“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48年8月6日,父亲的胃病终于发展到胃穿孔。12日,实际年龄还不满五十岁的父亲,在他长期渴望的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像群星中闪烁着的一颗,当自己光华最盛的时候,却在黎明前的黑夜中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