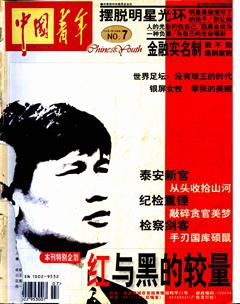知青史蒙太奇(谁能告诉未来一段真历史?)
□采访报道:赵为民
□图片提供:《走过青春》(黑明/著)
三十年很短,当初事已成追忆!一万天太久,后来人可知真情?
残酷青春伤心物语真实谎言
【写在前面的话】
申请这个选题,出自我个人的一个私心。30年前,大批城市知青应毛主席号召下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同一年,父母抱着刚出生的我也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一直到1974年我们回到北京之前,每逢周日,爸爸都要炒出一大罐肉松让来家聊天的知青带走,而我抽屉的最底层至今还有他们给我做的弹弓和沙包……岁月如梭,如今我的年龄也早超过他们当年的年龄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把他们遗忘很久了。岁月的冷漠使人们只有当时间到了周年、到了逢五、逢十时,才想起来大肆纪念一番,我惭愧地发现,我对他们的了解太少了。
在对知青、对知青周边人的采访中,有两个问题渐渐凸现出来:
一是从1968年他们大批下乡,到1998年重新回顾,看似漫长,可知青的影响仍然会延续下去。1998年3月,当世界瞩目中国召开“两会”时,面对电视,我突然想,如果再过20年,当过知青的人当上中国的总理,知青的生活和经历对治理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影响?而且那时,知青的第一代子女已经成为国家的栋梁,在生活方式、处理问题上直接受到知青影响的这一代人,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第二个感触是什么人来写知青史,其实这也是所有历史都要面临的问题。30年来为此写诗歌、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历史书的人数不胜数,然而,真正在社会底层的知青是绝大多数,他们的有苦难言使这段历史并不像现在呈现出来的那样简单。对于所有后人来说,想了解、进入那段历史,“记录”更像一副“眼镜”,不可或缺。盖棺论定虽然为时尚早,但时常检查“镜片”是否失真、是否清晰,却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谁能告诉未来一段真历史?
为此,我想集中采访一些“写手”——还原历史确实很像“瞎子摸象”,我不奢望从哪个人手里能“粘贴”出一个完整、“真实”的原形,只是希望借助比较逼真的“镜片”,看到哪怕一小片“真迹”。青春有多么残酷
张辛欣,我接触的第一个被访者。作家。
朋友说她1953年出生,15岁在黑龙江当农场工人一年。这次回国时间很短,只好赶在她上飞机前匆匆一见。看上去,她比她的同龄人显得年轻、活泼,语速飞快,而且没等我寒喧,她就劈头一句:“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采访?”
我预料她有可能拒绝,却没有想到她的反客为主。冷静之后,我简单地告诉她,我一不想猎奇,二不想廉价同情,只是希望后人能看到并记住“真实”的历史。
“可是我无法把自己当做‘知青作家,虽然我是那一代,但我很快离开了。”她说。
“很多时候,记忆的深浅并不是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我仍然坚持。
不知是什么地方触动了她,她沉吟片刻,开始和我交谈起来。
“我有一篇涉及我的知青生活的小说,写即将离开北京时,火车站台上,女生们哭成一片,男生也哭了,只有我仰天大笑。因为我很傻。连男孩子都想到未来的很多困难,起码很感伤,但我却只看见眼前的阳光灿烂。可能在那个真实时刻,在开车铃和汽笛长鸣的震天动地中,我是惟一没有哭的少女?
“回城之后,我曾作为北京医疗队的成员去过西双版纳。那里的知青,砍伐参天古树,栽橡胶树,修永远漏水的水库,一边干着于地球很荒谬的事情,一边卷在私人生活的荒谬性里:非婚的怀孕,然后,自己做堕胎,还召集了同伴,把胎儿和鸡一起炖,自己吃自己的孩子。当地老乡吓唬孩子的时候说:‘再哭,就让北京知青把你吃了!”
……看着她激动起来,想像着“知识青年”这个定义的悖论,我无言以对。
同事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每天中午都要听她讲比她更为幽默的哥哥的趣事,笑得大家总吃不好饭。得知她哥哥也是一名知青,现在美国打工,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写知青小说上。我缠着她帮我发一封电子邮件过去,问问他的感想。没有想到,回来的信全没有想像中的幽默,满满两页纸上是我难以承受的沉重:
“我很反感那些知青文学中所描写的,要么‘充满激情被愚弄,最终大彻大悟;要么‘文革受害者,动不动就痛心疾首。我为此写了我的农场生活,算是为了表现‘真实。我不想给农场的人们看,因为完全是涉及他们的事。我只想反省在那年头我看了多少‘红旗杂志,写了多少思想汇报,这是我记忆里最难堪的、永远挥之不去的印记。”
按照人们的思维惯性,1968年12月的“最高指示”被当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始,而在历史学家眼中,知青运动上迄1953年,下到1980年。社科院定宜庄和刘小萌两位博士为此耗费了8年的心智撰写了《中国知青史》上下两卷。当我见到定宜庄时,我给她讲起我对于苦难的震惊。她苦笑着告诉我她的经历:
“我见到过一个美国人,聊天时限定了一个话题,就是讲从20岁到30岁之间的经历。他讲他从20岁怎么到中国留学,怎么世界各地地走,怎么读博士,怎么当了教授。而我讲的全是特悲惨的事儿,即使觉得是快乐的事,讲出来也不是那么回事。同是‘战后的一代,他们的生活就是那么丰富、多彩,得到了那么多东西,而我们的生活那么贫乏、不幸。”
而定博士的尴尬经历,在张辛欣那里,我已经听到更激烈的反应了:“60年代末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法国在“五月风暴”,美国在越战。我们大多是初中生,小学生。他们的参与者大都是大学生。我们在这边声嘶力竭,将荒原改造成新荒原,而西方的年轻人玩得形同游戏!”
青春,这两个字眼儿,在人们心目中意味着快乐、精神、放肆,青春万岁,青春之歌,总是古今中外的人们咏叹不完的乐章。而对于这一代人,从十几岁到20几岁,除了残酷,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形容。在《中国知青史》下卷的封皮上,一代人短暂的英雄主义和激情之后,我们只能见到一言难尽的苍凉慨叹:
大潮涌来——
几千万少男少女的黄金年华卷进了
黑泥黄沙红壤,山川田野莽原
风潮落尽——
留下多少春风般的顾念,夏日般的历炼,秋雨般的失落,冬霜般的哀怨
故事最让人伤心
在我耳畔,总响着这样一句话:
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值得庆幸,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今天,还有一些为别人伤心、为别人悲悯的人。
黑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见到黑明之前,我先采访了马晓峰。
他是知青子弟,父母至今还在陕北,他只身在北京上学。很多知青都见过他,每逢老三届聚会,他都要替妈妈跑去看看。他遗憾地告诉我,去年11月8日,摄影家黑明为100名陕北知青拍照的摄影集签名售书时,他曾拿着书拼命地追黑明签字,“人太多了,他走得又太快,没有追上”。
当马晓峰翻着我带去的那本《走过青春》,给我一一指着他妈妈的同学、同事时,我在心里衷心地为这个孩子、为他的父母感谢着黑明。
随后见到黑明。果然风风火火的,却没有我想像当中摄影记者应该随身挎着的相机,他的解释是:“我从来不拍城市,只拍知青和农村。”
《走过青春——黑明百名知青报告摄影集》在北京引起爆炸性反应,刚过而立之年就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大大地得意一把了。然而,眼前的他虽然还背负着为出这本书欠下的重债,谈的更多的则是在他镜头里面人物的喜怒哀乐。
——这个人,穷,老婆跑了,他不去找,说他的老婆戴项链,已经变“修”了。他的思维方式早就不是知青了。
——这个人,第一个理想是到动物园喂老虎,因为老虎有肉吃,他就会有肉吃;第二个理想是到中央电视台看大门,因为演员有肉吃,他就会有肉吃。
——这个人,到了陕北后不久,就得了精神病,拉下了不少饥荒。我拍照之后几天,房东就把他们轰出来了。
——这个人,两口子,从1986年到1995年,一分工资都没有领到。
——这个人,和朱明瑛是小学同学,在电视里看见她唱歌激动得哭了。养不起老婆,只能贴很多“大美人”挂历,打发寂寞。
当然,在他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成功人士。然而,在长达5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给我讲得最多的是那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的故事。也是这一点,在他的签名售书活动中引起众人的唏嘘不止。在这里,我不忍复述他在书中用冷静、白描的新闻口气讲述的那一个个让人掉泪的故事。然而,在所有知青作品中,最令人伤心的也正是他这些用黑白相片表现出来的真实。
谎言为什么真实
几个月来,人们一直在考虑黑明出现的意义。北京著名报人杨浪一语中的:“从传播的意义上细细想来,这许多的感动源于‘命运的无情,而对‘命运的了解来自详细的文字,照片则以无可辩驳和生动冷峻证实了这‘命运的真实存在。”
中国人总希望在白纸黑字中,由别人给自己一个正确答案。然而,看法总是要过时的,事实却永远真实地留在原地。更多的时候,命运的看法比亲眼所见更准确。
对于以往的关于知青的文字记录,我所采访的几个人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反感。
“后来王蒙小说《如歌的行板》中一个飘飘然的句子刺激了我。原句大意是:一颗星对另外一颗星的召唤,是人和人的呼应什么的。这使我极反感。”张辛欣对那些被情感美化了的文字同样不以为然:“我以前觉得张承志的《黑骏马》是利用异国情调的煽情作品,而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写知青回城了,又感觉乡下如何好,想回去,并且真的回去了。这明明是对‘皇帝没穿衣服的大撒谎。当年谁不想方设法钻回来?看看叶辛,一个上海人,带回一种小鼻子小眼的云南。再看王小波,他也在云南插过队,但是,他的故事没有唐代诗人写边塞诗那样的意气风发,不飞扬。”
在我同事的哥哥的信中,也有类似的感慨:
当我给现在的年轻人讲当年的故事时,他们常说:“这不是真的!”或者说:“你们那时觉悟真高!一说要上山下乡,没有不去的!”
——我是这一代中最普通的一员,讲述自己的生活怎么会被认为“不是真的”?在那个人人盲从的日子里被动地卷到了边疆,怎么会被理解为“觉悟高”?
等一等!
每当我听到被访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时,我总觉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是什么使“镜片”在这里变得朦胧了起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既然文学是追求真实的,历史是追求真实的,镜头是追求真实的……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那样不能令人满意的白纸黑字?
想来想去,答案恐怕只有一个:真实的谎言。
每一件自以为真实的事情,都只是接近于近似值。
真实?谎言?也不简单为是非的判断。
一个知青事业成功了,好比下海吧,他会激动地说:我的成功得益于我当过知青,天塌下来我都会抗得起。
而当有一天,生意赔了本儿,他最容易说的话还是这句:我是知青,先天不足。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辛欣解释文学中的这种“误差”说:“距离造成虚幻,距离也造成真实。我们回忆‘知青时代,因为那些日子是青春的,这样,我也原谅安忆刚回来就要回去的、用小说‘做梦的方式,体谅她的不真实。”这个问题在定宜庄博士那里得到了比较清晰的解释:“文学的真实是能够真实地反映当事个人的感受,史的真实是尽可能接近真实地阐示这件事产生的原因和它的后果。”而在《中国知青史》中,随便找一处文字,就能体会到两种表现形式的不同:
比如在“上卷”里,丁宜庄写道:“每一次到经济转入低谷的时候,都要弄一批知青去下乡,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为这个国家扭转败局做贡献的。”
史书中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包含着不知多少人的眼泪。而关于血泪具体是怎样呈现的,则是文学家的任务。“我不喜欢文学家总自以为他们也可以写出历史来,事实上我就从不认为史学可以代替文学。”
正因为有了这样尽量客观、冷静的思考,读张辛欣、刘小萌、定宜庄、黑明的作品,你会觉得以往知青作品所喊出的“青春无悔”是多么轻率和奢侈。
说到这点,即使是温和宁静的定宜庄博士也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没有选择的自由何谈‘无悔?我们这一代人喊这句话很矫情,很做作。反正我从来不喊。”
事实上,另一种“真实的谎言”更不容忽视。
在一次知青恳谈会上,《中国知青史》的另一位作者刘小萌指出:“近年来,常有一些当年的知青典型、甚至包括在‘文革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誉为‘反潮流勇士的人物很是活跃,频频亮相于杂志报纸。在他们的自述中,有的只是当年‘在农村战天斗地的大事渲染,有的只是与‘贫下中农水乳交融的关系,却罕有关于自己在一场场政治斗争中‘出色表演的回忆和起码的自谴自责。”
刘小萌的话让我重新审视这种确实存在的怪现象:一些知青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伤疤,擅长掀起衣服给人看,甚至干脆把知青经历当做一块闪闪发亮的勋章挂在胸前,他们的自我炫耀恐怕并不排除他们自身是这场运动的既得利益者。如果知青史由这些人来执笔,我们,我们的下一代……恐怕更难接近那个“真实”历史了。
定宜庄在接受采访时,也肯定了这种说法:“除此之外,还有话语权的就是一些知青作家和成功人士。而我们史学家不应该把眼光只关注在他们身上,而是作为整体的知青,生活怎样。很多人死在那儿了,很多人到现在连个饭碗都找不着,他们没有心思跟你玩什么知青情结,玩什么青春无悔。我们想写的是个群体,而不是这里跳得最高的。”
和他们进行着不同记录形式的张辛欣直言不讳地说:“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而所谓知青中后来出人头地者,包括写作得利者,换个目光,都是比较机灵的生存者,而另一些生命,体力和精神上都消磨太大,已经发不出个人的声音了。”
在张辛欣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中,我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回音壁的失真——1988年,张辛欣遇到两个博士生,打算采访知青,他们放弃条件优厚的美国教职,并且相互提醒,不要在中文里加英文字眼儿……当时的她对他们说:也许你们要失败。因为相当多知青固守着自己的经验,他们会摇着煤球,斜眼看你们这些文质彬彬的“小四眼儿”。因为经历的不平等,他心里问:“你凭什么知道我们的苦难?”
摇煤球的那些人,是落在底层,真正有苦说不出了——当每一个人都向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时,在我心里对于这些“写手”价值的认证也在一步一步地加深着:抛弃掉“自恋”情结,展示有苦难言的人们的苦,爱着别人的爱,苦着别人的苦,悲伤着别人的悲伤,幸福着别人的幸福,在今天,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这一切远不是那些靠着拍卖苦难为自己“镀金”的知青所能达到的境界。
残酷造成激情,残酷也造成美。而在史学家笔下,这种残酷的激情是要以另一种方式传达给下一代的。定宜庄对她的儿子的话让我非常感动:
“元元,妈妈这本书是写给你的,我不希望你理解、羡慕、怜悯我们,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黑暗的一幕,我希望将来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
——把一代青年的青春毁掉,确实是人类史上令人发指的惨剧。然而,历史无情,无论如何,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对他们这一代人,仅有怜悯是远远不够的,对历史负应负的责任是不论哪一代人都推卸不掉、逃避不了的。正视历史悲剧,对既得利益者甚至受害者进行无情解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是每一代人翻阅历史时应有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待知青史,更需要这样的态度。
【背景】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指示发表后的庆祝盛况: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纷纷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当时就有人写出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随后,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革”以来的初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和参加工作的外,纷纷被动员去农村、边疆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