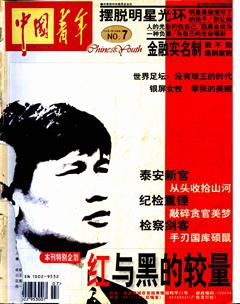拒绝同化 等
许多年过去了,我却常常用自己的想像方式来完成对那个颇有争议的时代的怀念。那里有慷慨激昂的演说,不绝于耳的国事天下事,狂热的校园摇滚,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和尼采哲学……今天,当我有幸步人大学时,美丽如初的校园里,我却再也看不到能让学生们趋之若鹜的学术讲座。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录相广告,信誓旦旦的“拾者有重谢”的寻物启事,人头攒动的商场、夜夜爆满的舞厅,“玩一玩”的情侣双双……
这是一个没有激情的时代。经历过社会变革的校园早已不是净土。各种迥异的心态把校园装点得不是多姿多彩而是变幻莫测。我无法掩饰对渐渐尴尬的校园文化的失望。那些曾经造就过许多才华横溢大学生的校园社团,你现在怎么啦?在那些健身、电脑等各式各样的培训班的挑战下,你为何如此不堪一击?沉寂在语言世界的校园诗人,当你注定只能是这个时代的散兵游勇时,你能否耐得住被抛弃的寂寞?静坐于书架上的哲学文学名著,你是否会为匆匆而过的读者不屑的目光感到寒心?在学生们被计算机、公关、岑凯伦、梁羽生等各种畅销书籍“围剿”得乐此不疲,你能无动于衷吗?对不起,所有的孤独者!我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向你们表示尊敬和同情。
学生们都很忙很累,他们依然在忙考试忙文凭忙于学那些能够带来实利的电脑、英语等实用技术。他们似乎来不及也没有兴趣去思考,去问为什么,因为这是很容易被人嘲笑的。实用主义的生活模式和纯粹的娱乐方式在这个时代已无人非议甚至深入人心,它们拒绝思想的深度。自以为是的大学生在囫囵吞枣的快餐文化和能带来一时实利的操作性技术中沾沾自喜。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科学技术,却不知道自己已被科学技术掌握得没有了思想和灵魂。
“陌生的人啊,当你走过我的身边时,为何不和我说话?”这句不知看自何处的话引起我刻骨铭心的孤独无助。眼前总是来来去去年轻依然的面孔,我却很难看到一丝兴奋、激动和热情。千篇一律的是茫然冷漠和沧桑或者令人恶心的矫揉谄媚。我们渴望安慰鼓励,我们却时时在孤独无聊中同样给别人以冷漠和拒绝。在这里,似乎很难再找到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再相信什么,无所谓相信什么。所有曾被我们极度虔诚地为之欢欣为之奋斗的信念的光彩在躁动着的“实用”主义、“务实选择”中被稀释。所有诉诸心灵的东西在履经百年的剥落拷打中被肢解得支离破碎。90年代的校园我们再感受不到那个激情时代的脉动了。昔日的硝烟已经飘散,兴奋激动或是愤怒狂躁的反叛面孔已经消失。现实是至高无尚的权威。被动地接受和认同一切都显得天经地义。此时,超越变成认同,激情成为堂吉诃德式的多余和可笑的浪漫。校园在各种思潮的肆意冲击下失去自我,成为时代的文化边缘。
“一个时代若不能容忍一位真正的批评家,这是这个时代的末日。”我的耳边不时回荡着这句刺骨的真言。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校园,是你主动放弃了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吗?在整个社会弥漫“实用主义”“务实选择”以及世纪末的浮躁危机时,你本应该拒绝同化的。你是知识精英萃集充满青春朝气的象征;当有一天,大学业已完全成为世俗认同的场所,还能指望谁来对躁动的社会尽一份应有的批判?
江西吉安师专中文系95系彭林生
我的生活主张/痛苦
世间欢乐少有,而痛苦常有。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消除痛苦而不断产生新的痛苦的过程。痛苦有时意味着对真的背叛、对善的戕害、对美的蹂躏。山河破碎、骨肉分离固然令人捶胸顿足,然而更多时候,痛苦乃是欲望与能力之间的级差。低能而多欲,是衍生痛苦的酵母。
痛苦分肉体的痛苦和灵魂的痛苦两种。灵魂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更甚。肉体的痛苦可以随时间的流逝渐渐抚平;灵魂的痛苦往往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经常将“痛苦”两字挂在嘴边的人并不真正痛苦,他的痛苦已在喋喋不休中稀释;真正的痛苦像沉睡期的火山郁积在心,说不清,道不明;像一团麻,剪不断,理还乱。
罗曼·罗兰说:痛苦像一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我们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新的水源。
南京邮电学院300号信箱徐雷
我的生活主张/两种爱
大学时,一位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懂什么是爱?谁能立即告诉我,你的恋人脚上穿的鞋是几码的?谁能说出来?”没有人能回答他。“你们懂爱?”老师的表情很是不屑。
一位同室兄弟从大一到大三一直在追本班的一个女孩子,追得很苦,很累,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能看出来。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那女孩子永远是若即若离,快毕业时,他停下来了,很痛苦。忽然有几天,那女生没有来上课,后来听别的女生说,她的腿摔伤了,在家休养。那位仁兄竟立即买上一大袋水果,跑去那女生家里看望。
我们只当他勇气重燃。回来时,便笑问他“岳父岳母”的态度如何?“谁?”他擦着脸上的汗,有些发懵。“哦,你们想哪去了?我要是真是那个意思,能这样去她家吗?”的确,也许是走得匆忙,他衣衫不整,头发零乱。“就是听说她腿伤了心疼。”最后两个字他说得很慢,声音也很低。
吉林省四平市李立波
守望心灵的春天
很多时候,我都有一种欲望,试图对这个时代和自己做一番理性的总结,揭示出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但我发现,这很难,就像小猫打着转不停地追逐着自己的尾巴一样无法把握。
曾几何时,那曾滋养过青春岁月的梦想已背影模糊,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并被自己奉为圭臬的人生准则被现实弄得樯倾楫摧,残骸遍地。所有关于形而上的谈论往往会赢得一片讥讽声。也许他们说得对,一个生存时时受到威胁的人,还谈什么理想、人生?于是自己也变得身不由己,一任金钱欲望左右自己灵魂的走向。忙忙碌碌,奔奔波波,危机感和紧迫感贯穿于每一天真实苍白的日子。这样一路走来,与以前相比,自己的生存条件相对改善了,但灵魂却无处安放,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呐喊让我无法原谅自己。生存的意义、青春、理想、热情、信念等人生命题又在眼前不甘心地盘旋,但不甘心又怎样?你能超越现实吗?
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科普期刊社,大部分员工都是招聘来的。事实上单位之所以招聘他们,是因为他们年轻、能跑、能写又能说,没有人为他们今后的出路提供任何保障。你会说,国家不是有《劳动法》吗?如果你真的诉诸法律,单位损失的只是一些钱,而你损失的不仅是饭碗,还有极度的精神损伤(在中国大部分用人单位都如此)。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喜欢自己的工作?仅仅是空怀抱负暂时没有出路的无奈的选择,不知道明天自己又将漂向何方。在这里,除了能力,还需要讨好领导,因为每个人的去留只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问题。于是,拍马溜须、曲意奉迎则成为“把根留住”的守身符。虽然我很唾弃这种行为,但我也经常不得不为领导充当“三陪先生”:陪打牌、陪吃喝、陪玩,这不但引起不少人的忌妒,我也时常想打自己的耳光,是不是要生存就必须以失去尊严、降低人格、压抑个性为代价呢?
我不愿为活着而活着,但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神仙。赵传老兄在歌中唱道:“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到底哪个更重要?”这几乎成为常常徘徊在我心中的天问。
不仅仅是我,举目四望,我悲怆地看到,一群打工妹被厂主无故扣发工钱,饿得在宿舍里抱头痛哭;50万年薪的中国第一打工仔最终在被愚弄的旋涡里满身伤痛地挣扎;深圳的一群打工仔跪倒在韩国老板的脚下。当所有的人都在寻找那个不跪的人时,我的目光却疼痛地关注那些下跪的人,难道他们不懂得人的尊严吗?还是我们的社会还不能为他们提供不跪的条件?
至于道德,似乎也在这个时代塌方了。打开电视、报刊或者走入人群,耳闻目睹的是:落水者的呼救声唤来的是岸上冷眼旁观的看客;路见不平的英雄流血之后悲伤的眼泪;国库里的硕鼠越打越多……我们信念中的道德感已去向不明。
爱情呢?已沦落为一个风尘戏子,尽管所有的歌曲曲曲含情,都以“LOVE”为主题,但我还是失望地看到了爱情在金钱面前匍匐而行。“没钱搞什么对象?”没有谁耐心地为爱情付出与承担责任,那些永恒美好的爱情已遗落在发黄的古书里,踽踽于现代诗人伤感的咏叹中。友情更是如此,现在你几乎很难找到几个能与你平心静气坐下来喝酒品茗谈诗论道的朋友,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像遇到外星人一样,以惊异的目光看我:都什么时候了,还谈这个?大家都很忙,偶然相逢,匆匆丢下一句“有事CALL我”便不见了踪影,言外之意呢?没事别烦我?
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人说“难得糊涂”;有人说“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不能接受,为什么要装糊涂呢?如果清醒是一种痛苦,那么糊涂就会是一种快乐吗?我毕竟还年轻啊!我拒绝平平淡淡养生式的生活态度,也不愿消极避世。我需要满怀希望、激情、尊严自由地活着,尽管这注定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永远在心灵的舞台上上演。
西安市158信箱李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