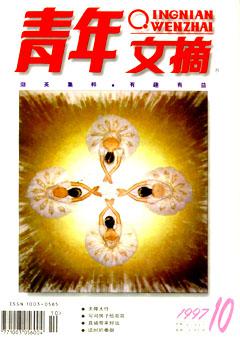写间房子给哥哥
周凡恺
那是三年以前,我和妹妹约好,共同出资给我们的胞兄买间房子。
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虽然觉出了肩上的压力,但心情毕竟还算轻松,尤其是看到母亲少见的舒展的笑脸,我们便感到了一丝安慰,那种心情是做儿女的终于能够为母亲承担了一点什么才会有的。况且还有人所不知的一点,即我们可以有一千个理由拒绝给哥哥买房子,可这一千个理由纵使再堂皇,在哥哥的痴笑面前也会立刻土崩瓦解,因为我的哥哥在智力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的确,哥哥可以说是一个半傻不傻的人。
他虽非先天痴呆,但小时的那场大病却使他变得愚钝。从小学到中学,他所有的功课都不及格,因而也就成了被人戏弄的对象。譬如,他常常被人剥掉了裤子,光着屁股回家;再譬如,他的脸上总是被人画得一塌糊涂,要么是一副眼镜,要么是几根胡须,每天都脏兮兮的看了让人难受。有一次,他被几个同学押着,头上戴着一顶破钢盔,举着双手在操场上转圈儿,那时我的血就涌上来,操了一根铁棍冲入人群,闭上眼睛一通横扫。有一个时期,我与一帮流氓搅和到一起,四处寻衅,也多半是为了他的缘故。
我那时就已经知道,哥哥虽然从死神的魔掌中逃脱出来,但他漫长的人生将是屈辱的孤寂的黯淡的,我们虽有能力保护他,可终不能一辈子守着他,我清晰地记得,父亲临终之前,目光久久地凝在哥哥的身上,一滴混浊的泪从他的眼角爬出来,在散乱的阳光下抖动着、闪烁着。我从这滴泪中读懂了父亲对哥哥的牵挂,也读出了未来的生活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
我和妹妹上大学时,哥哥已经谋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医院的传染科扫厕所,他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拿着最低的工资,并且医院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唤狗似的对他吆来喝去。即便如此,无论是母亲还是哥哥本人,都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他终于有了一个饭碗,可以自食其力了。偶尔,我和妹妹还可以接到他寄来的汇款单,虽然只有几元钱或者十几元钱,但我们却在他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中品出了其中的分量,心里颤颤的,不知该怎样将这一小笔血汗钱花出去。
大约30岁的时候,在几个热心人的撮合下,哥哥结识了一个山里的残疾女孩,此时的母亲虽已改嫁,却仍旧顷其全力,为他们操办了婚事。然而新婚的喜气还没有过去,两人便平静地分手了,本已愁肠百结的母亲心力憔悴,病卧在床。我曾劝慰母亲说,散了也好,不然于人于己都不人道。母亲是有文化的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接受我的想法,而实际上,她几乎是神经质地到处求告,拜托朋友为他的傻儿子说上一门亲事。她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从小跟着我吃了很多苦,我或许活不了儿年了,趁着还有一点力气,我要把你哥哥的事情安排好,不能让你们去背这个大包袱。想想母亲这一辈子,我们的心中酸酸的,只能沉默不语。
终于有一个被人遗弃的女人同意与哥哥过,但她及她的家人提出了一个条件,而且是必须的,那就是马上给他们买一座房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愁云密布,一夜之间白了头发。她说就算把她的老骨头榨干了,恐怕也买不上两扇门窗,况且她是一个改了嫁的人,她不想因为自己的儿子去烦忧别人的生活。万般无奈之中,她只得电召我和妹妹回去,替她想个周全的办法。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大雪下得铺天盖地,我和妹妹很悲壮地走在雪地上,把积雪踩得吱吱乱响。妹妹凝视着幽不见底的夜空,我也凝视着幽不见底的夜空。我们就那样嘴里喷着白气在寒夜中转着圈圈儿,看着不远处的火车一列一列地开过去,看着一盏又一盏的红灯笼在新年气息已浓的冬夜中忽明忽暗。
后来妹妹就对我说:咱是该给哥哥买座房子!
后来我也对妹妹说:咱是该给哥哥买座房子!
后来我们就去与傻哥哥和新嫂嫂喝酒。
后来我们就在一张纸上签了字,答应先给他们租房子,两年之内一定让新嫂子搬进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居。
我们第一次从真正的意义上理解了什么叫责任和沉重。
妹妹给我来电话说,她想放弃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一工作,她要下海,她要开一家时装店,去掏女人和儿童的钱袋。我说节目主持人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差事,不要因小失大。她便沉默了几天,然后又来电说她去炒股票了。她的心情当时很开朗,一个劲儿地和我开着玩笑,说假如她一不小心炒成了“资产阶级”,就给我们全家所有受苦受难的人都买幢别墅。我在心里笑着,仍旧平心静气地每晚去编书写字儿。我知道自己没有别的能耐,只能靠写字儿去给哥哥买那一砖一瓦。我承认,有一段时期,我的写作动机可能只有一个:挣钱。我也的确在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读者的情况下挣了一笔自认为很可观的钱。于是我便给妹妹打电话,说两年的期限眼看快到,咱们该行动了,可妹妹说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是熊市,不仅房子买不成就连股本也给套牢了。我叹息一声只得回到桌前继续写字儿。
然而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先是妻子遗失了公家的一笔巨款。无论在办案人员还是其他人的眼中,妻子都是被怀疑的第一对象。为了洗刷这种耻辱,妻子多次企图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以致我每天必须对她实行24小时的“监视”。我如今已无意对此事以及赔偿作出任何评说,但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个至今仍隐蔽着的大盗,或许脸上依旧堆满了笑容,觊觎着,正在寻找着另一个倒霉蛋儿。
也就是在这之后,我上了一趟庐山,且抽得一签,曰:月落星稀,风生雨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抽签,当时只是觉得好玩,并未仔细研究签中谶语,更未品出其中的宿命味道。然而半年后当我接到妹妹车祸罹难的消息时,这8个字就变得有些狰狞可怖了。
我不否认,在妹妹突然离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几近崩溃。从小到大,我对她一直在行使着“父亲”的责任,她的每一步,都是在我的呵护声中迈出的。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夜还未深,我便熄灭了那些曾经伴我静读的灯,在黑暗空落的房间里呆呆地坐着,直至天明。有时,我在微露的晨曦中睡上一会儿,便觉得很累,觉得身心已经成了一滩稀泥。我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睡下去,被浓重的梦魇笼罩着。我的梦中总是飘荡着家乡的雪霁,就如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笔下的那样明澈寒峻。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我站在窗前望着楼下空寂的广场,那里每天都有一个老人在太阳底下坐着。他很老很老了,目光也像幽灵一样。他总是久久地凝视着天空,脸上的表情很神秘,他肯定是看到了什么,就如两千多年前楚国的屈子所看到的一样,只是他缄口不语。因而当他那弯曲的影子从这个广场上消失时,他也把他所看到的一切一同带走了。阳光依旧好。此刻,我知道在家乡那两株老榆树下还坐着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傻哥哥,他们在等着我去兑现我与妹妹所许下的诺言。
我开始清点我的所有,我知道我必须付上妹妹的那一份。妹夫冬波是个好人,他说等妹妹的抚恤金下来,就给哥哥买房子。可我怎能要这笔钱呢,那是妹妹的血啊!况且肇事的各方至今仍在扯皮推脱。冬波又说,那就等妹妹炒股的合伙人把钱送回来再买。我说你知道她的合伙人是谁么?人家若是有意,钱早就送回来了。于是冬波不语。于是冬波感叹:人呐!
我把买房款寄回老家的那天是个好天。我听着汇兑员在那几张单子上响亮地敲上邮戳时,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我看到妹妹坐着一驾马车,回头冲我笑着,在烟尘中远去了。我在心里说:该歇歇了。
(孙朝晖摘自《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