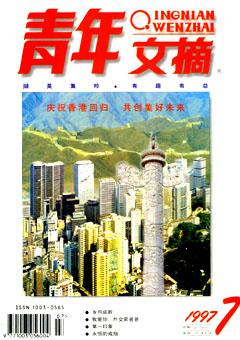在心里种花
燕 黎
一个轻寒的秋日下午,我开始在屋后的小斜坡上掘地。一包泥炭、一袋骨粉和一大堆浓厚乌黑的混合肥料将成为篮中那些球茎们赖以生长的根须交错的土壤。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花费功夫来种这些春天和夏天开的花——郁金香、水仙、百合等等。这片土地和坐落于其上的这幢老屋子都不属于我。幸运的是,主人们还能迁就我的出于改善家居热情的“园艺狂”举止。蔓生的薄荷装饰着起居室的窗;多彩的紫罗兰星罗棋布于厨房门边的成群假山上;还有那些肥美的洁白的果仁,一片片地摊晾在我周围冰冷的土地上。可是,我为什么要把时间和金钱花在这些我只能享受一或二个季节(然后就迁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不属于我的花园去)的东西上呢?
是我父亲、一个业余农民,第一次教我懂得万物如何生长,以及长期投资的价值。整整30年时间,他作为一名市政工程师为政府工作,设计了无数条高速公路。进入花甲之年并在母亲去世后,他开始喜欢画画,好像那些颜料、刷子、亚麻子油只体现了一种微不足道的工具变化——从前他打交道的是辗碎的石子和沥青。
父亲对他认为重要的小事物非常仔细,但他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无心机的人。他从不投资风险超过政府债券的任何东西,这种债券,要捂上多年才到期,然后发旺增值,然后在某一天,当你用它来支付新汽车或学生贷款时,忽然就消失成空了。对父亲来说,这种类型的交易能带来良好感觉,它是一种自然法则、世界法则:你播种,然后你等待。
然而,不知怎么的,即使再大的盈利,花呀、果呀、手中的大笔现金呀,所能给予的也只不过是强烈而短暂的快乐,一个梦想的最后证实,更深层次的满足总在成长过程自身,在那满载所有对未来的甜蜜的、不确定的期盼的生命力里。
坐在异乡小山坡高高的草丛中,我不由想起很久前许多个潮湿的夏夜,父亲锄完草走进谷仓,随手抓起一把矮牵牛、菩提瓜或其他任何需要种植的东西。在浓重的汽油味、汗味和新剪下枝叶的清香味的薰陶中,他跪在苍白的暮色里,用一把旧的木柄泥铲挖坑。他的左臂不停地挥来挥去,以打散脑袋周围如云的蚊阵。
这把泥铲如今就握在我手中,尽管它的柄已因岁月漫漫而松落。阴霾迅速积聚起来,现在是白昼变短的秋日了呢,我更着意地加紧工作,弯腰、挖坑、播种、盖土、夯实,一次又一次。太阳已经沉到了地平线下面,巨大的枫树冠像红色的金子在屋檐上方闪着微光。一些还未种下的球茎仍静静地躺在地上,它们是活的期票,将于来年春天成熟和兑现。
(段伏加摘自1997年3月20日《上海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