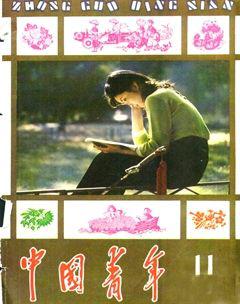无花果的时代
夏辉强
终于有一天,当我们发现儿时所有的憧憬或者全部的希望在他人眼前的现实里是那样可笑甚至不值一哂时,我们1那时的感觉便像用手小心地捧起水待送到嘴边时,水却从指缝间溜走了,再也把握不住,一种无言的苍凉深深地压上我们的心头。
这个社会变化节奏太快,因而前人留下的理想的种子在我们心灵中的位置越来越退后。有人急急忙忙步入金钱运作体系,如同流水线上一颗不能脱身的镙丝钉;有人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体验着醉生梦死的滋味;有人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品味着贫穷和凄凉;有人整日留心哪个又发了谁又爆出了新闻……天地悠悠过客匆匆风风火火都说累,只是日子照样钟摆似地一如从前,至于爱情已快成了明日黄花,信仰变成一杯浊酒,伟大则成了传奇中的神话,理想终于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于是,在这个有人称之为“无花果的时代”里,一种失望的感觉在弥漫,可是,正如一位诗人说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冷峻而严酷的竞争是不是已构成我们生活的全部?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与为求一饱终日翻山涉水追获猎物的四足动物又有何异?生存是我们的理由,但为了生存而生存则是我们漂亮的借口。当我们的口袋越来越满而脑袋越来越空,当我们的感情变成了沙漠当行动失去了方向奋斗没有了动力,当我们越来越不能忍受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喊时,我们才清醒地意识到:金钱再多,也不能化为血液流归人体,世上还有许多如芝兰般芳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追寻探讨。
我们生活在世纪的交汇点上,在这个各种思潮各种观点交相变更的特殊年代里,价值体系价值观念都发生着让人惊讶的变化,新的尚未完全建立,旧的尚未完全解体,在这个中间状态下,注定我们这一代人在心理上处于“断乳期”。人类的烦恼根源,不是做人,而是“我想变成什么”,而有关理想最基本最终极的则是“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由此可见,人类的诸多烦恼都是根源于理想的未实现,自我的受压制。因此,关于理想的考虑应该是“我是什么——我能变成什么——我想变成什么”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少一个环节都不行,都不会有任何作用。
其实,我们再次注目世界,还是会看到哑巴妈妈靠捡破烂、卖血拉扯大四个孩子上了大学;失去四肢的朱彦夫写出了33万字的《极限人生》;还有李素丽还有徐州下水道四班……一句话,这世界上还是有人有滋有味地活着,兢兢业业地干着,生活依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所失落,也就有所重建。泰戈尔说:“如果你因失去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我们年轻,青春是我们宝贵的资本,我们不会永远颓唐,正如福珂在旷野里大声呼喊:“我梦想成为这样一个现代人——他努力在时代的惯性和约束网中探查并指明弱点、出路与关键联系。他不断变换位置,既无须知道明天的立场,也不限定今后的想法。因为他对现状的关切超过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