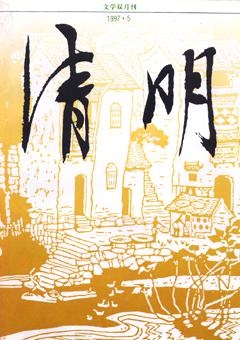生
吴其林
一
“梆、梆梆。”
“梆、梆梆。”
伸手不见五指,四境黑浓如墨。有节奏的打更声又一阵响起。然而这并非子夜,梆梆的敲击声也不是打更。这是石家贵用斧把敲击着管道。他没听见一丝反应、看不见任何景致。黑暗中放下了丁字斧,继续等待着、休息着。这是李家坝矿,水平标高为一492,具体地点在3028(9)槽工作面。
家贵穿着两件褂子,胶壳帽放在地上,腰中的灯带系着自救器和矿灯,脖子上围着半新的毛巾,左手腕上戴着电子表,还有那把斧子。这便是他的全部。他脊梁抵着棚腿子,说不上是坐,是倚、是躺。眼睛睁着和闭上差不多。反正没有一点亮。刚才他开灯看一下表,下午五点零八分,正好一整天,24小时。这期间他约有两个小时的假寐。怎么可能安睡呢?壁立的煤,从五个方位严密地堵着他;水在下边,像一柄无形的铡刀陈列于前。现在家贵的空间用数字表示只有这么大:1.2米×1.5米×1.8米。
这是一间不大不小的特殊地下囚室。家贵被平时温柔的水撵到了这里。那是一天前的事情。
八月十七日中班,李家坝矿掘进403队出勤二十一人,分成两组,主力放在十三槽进尺,安了十七人,一人送饭,剩下家贵、小顺和周庆到九槽回风巷道改橱。计划修改三棚。四时整,第一棚改好。五时十分时,家贵这边的第二栅腿窝挖出,腿子栽好,小顺那边也快差不多了。五时十五分,灾难突然降临。一股汹涌的来历不明的水,由上部巷道奔腾而下。水量特大,水声咆哮着像一匹怪兽从他们的施工地段掠过。三人猝不及防,周庆当即像一捆稻草被席卷而去,“啊”了一声便无踪影。小顺迅速向左边蹬去,他喊着家贵,等家贵起斧头抬起脸来,小顺也不见了。水很快漫到腰部,家贵来不及想,忙朝右边废弃的巷道蹬去。水也紧逼着上来。他一拐弯,钻进一个干燥的保险峒,水也接踵而至。他脑子乱糟糟的,看着这不讲情面的上涨的水,家贵心底叫苦不迭。生死存亡的关头,水也暂时停止了进攻,只将家贵抛进了这个峒里。
他蹲在保险峒里,其实这个峒子以前是个绞车房。在过去的一昼夜里,他试图突围,无奈水几乎漫到棚顶,突围无望,所幸的是目前的栖身之地是块制高点。他捡起干燥的细煤粉,试着风流,风微弱地拉向上部的老墟。他放心了,便用斧子把敲击着压风管,向外边发出信号。起先,他用紧急的梆梆之声呼救,后来意识到营救人员不会来得这么快,于是改用“梆,梆梆”的敲击。好像叩门,又像是打更。他想起这个比喻,嘴角不觉浮起一丝苦笑。
二
十七日这天真是个没法说清的日子。石家贵本该休息。邻居彩妮那有长有短的哀嚎干扰了他,搅得心闹得慌。她丈夫死了,那男人在柏家洼矿当测气员,五大三粗,壮实得像头牛。不久前,柏家洼矿发生了一起小型瓦斯爆炸,一伤一死,其中彩妮的丈夫受到刺激,一边往井上兔逸,一边不住声地驴吼。到井口,人就死了,医生说是气管破裂致死。讲起来,谁都不信,可那个壮实的小伙子,确实从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了。家贵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既为死者悲哀,也对死者表示鄙夷,尽管他没明显表露。完丧已好几天了。彩妮这天携子归宁,便开演了孟姜女的节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家贵在家呆不住,便加班去了。这天本该他休息。
师傅有句口头禅:“歇班不歇,违章作业。”此话家贵真实深刻地得到了应证。怨谁呢?那寡妇?当然不是。那么怨自己?家贵有这么一点牢骚,但他不想更多地归咎责怪自己,他认为这是老天爷同自己开了个玩笑,他不希望这个玩笑开得过头。也许一两天问题就会有结果的。他在无边的黑暗中给自己打气。
这时,一阵窸窸窣窣声传了过来,家贵忙坐起身,旋亮不敢久开的矿灯。
过来的,是一只老鼠。
这是一只相当丰满的鼠。灰色的毛潮湿柔顺,尾巴修长,胡须一撅一撅的,两只豆眼,小而亮,紧盯着家贵手里的灯。家贵高兴,总有一个活物来陪伴自己了。他把手抻过去,老鼠束手就擒。家贵从支架的空帮上找到一根细炮线,拴住鼠腿。同时模仿电影里日本鬼子的口吻“哟嘻哟嘻”地叫了两声。
家贵记得刚开始上班不久,经常见到这些井下的老鼠。有一回推车时,窜过一只老鼠,引起三个伙计不约而同地丢下车,兴奋地抓矸石捡煤块向老鼠投掷。老鼠没击中,家贵的头被师傅敲了一个包。比他大十岁的师傅寒着脸训他:“不懂规矩,煤矿工人和老鼠有什么两样?”原来,年岁大的矿工对井下的老鼠有着特殊的政策,凡有鼠活动的巷道,瓦斯都不大,能进出人员。鼠兼当清洁工,吃人们残剩的班中餐及人的粪便,而更为重要的是鼠是生命,所以倍受矿工的保护,对它秋毫无犯。
家贵中等个,中学毕业后他一心想当兵,体检时被1.O的视力拉了下来。到煤矿干工不比参军严格,于是他投身煤矿,卖汗珠子吃饭。想不到,这次连命也要搭上了。
他话不多,和师傅一样。每天点名、更衣、下井,到工作面就默默地干活。有人说他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其实这是在地层深处,在煤层皱褶中的施工场地,若是换一个环境,换一群人,家贵就判若两人了。工友们没听过他幽默的趣语,才当他不爱说话。在煤海深处,他只用眼睛观察,用耳朵放哨。
前年,师傅还没调动工作,家贵在师傅的后面攉煤,师傅正挖着,顶上一块矸石离体而落。要不是家贵手疾眼快,那后果真不堪设想。师傅被他拽个仰巴叉,却摸着高压锅般大小的矸石,笑了。次日,师傅吩咐家贵去他家帮忙干活。家贵当真,二话没说一溜烟跑到师傅府上。嘿,师娘已整治好一桌菜,有凉有热,酒瓶开着,双轮池。此时家贵不能再想了。越想,肠胃的呼声就越强烈,局部向整体的示威就越高涨。黑暗中,家贵无意碰到了拴在支架边的小动物,那东西吱吱地惊叫着。
饿。渴。
灾难发生时,家贵趟水进了这个避难所,喘息之余,家贵没有慌乱。他观察了附近的支架、帮、顶,没有什么威胁,唯一构成威胁的就是下边的水。他担心水上涨,看来这担心成了多余。水势稳定后,他用胶壳帽当碗,撇去水上的浮物,澄清着,备用,此时他极不情愿地喝了一口,冰凉冰凉的,想想地面上正值盛夏酷暑。自己却在这里避暑,饮用如此凉水,不觉又一次哑然失笑了。
这是事故第三天。
四
他简直是一个犯人,陷入黑暗的牢房,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不安地等候着最后的判决。
他尽量不开灯,以节省电能,他理解照明对于处境的重要性。除了间隔敲风管外,不做剧烈运动,不呼叫,以节省体能。他的情绪有点波动,有时觉得自己像误入陷阱的野兽,既愤怒又无奈。水在身边下部,与他无声对峙。昨天他拆了一根笆片当做水文标插在水中,现在他拔起看看,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家贵叹了口气。他习惯地坐起,黑暗中用斧把敲击着管道,发现气力少了许多——斧头变重了。
“梆、梆梆。”除了石家贵本人,没有任何人能听见这焦急的信号。
第四天,家贵当了一次屠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用锋利的斧头,肢解活生生的小动物。雪亮的斧刃上血迹鲜红。这是面对饥饿和死亡威胁的一次重大的决策和行动。家贵关上灯,闭上眼睛,艰难地咀嚼着生鼠肉。一股浓烈的腥味令人窒息,连肉带骨的咀嚼声,家贵自己都觉疹人,一团粘粘的东西从口腔直至胃部。胃痉挛着,对来料进行加工,此时的家贵成了一只地地道道的猫。
然后,他在对面的棚腿中挖了一小坑,埋了鼠皮和内脏。他想再留几个字,纪念这个为自己捐躯的小生命,便去掏窑衣的口袋。他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和一截短粉笔头,他在支架的木腿上用粉笔写下这几个字:
“一个生命葬于此地。”
五
接下去的两天,外边仍无动静,水,依然围困着家贵。一丝丝空气在整个过程中细微流动,它灌溉着家贵的生命之树。家贵尽量减少活动以积蓄能量。敲击风管虽然近乎徒劳,但他没有放弃,只是次数明显减少。焦急和孤独无法排遣。饥饿袭击着他,家贵用心灵与之对抗。渴极了,才去喝帽子中的水。有时,他非常希望自己是条龙,能把面前巷道里水,一口气喝干,然后升腾飞去,但这只是幻想而己。硕鼠一半葬于腹中,一半埋在对面的棚腿下。黑暗中,他知道脚已压上鼠坟。他感到:这个保险峒就是自己的墓地,自己的活坟,他甚至想,万一自己死了,会不会有别的老鼠来为它的同类报仇雪恨。黑暗是压在心灵的巨石。焦急是火,孤独是蛇,水是冰冷的铡刀。
背靠着木质支柱,他回想着许多往事和熟悉的人。心爱的女友,那聪颖的姑娘现在怎样?是否在为我啜泣?夏夜林荫道上漫步。闺房里的喁喁而谈。拥与吻。而今天各一方,遥隔地层,只身一人,被险情围困,无法突围,父母又该如何伤心啊!
家贵在这十一天里很少想到死。虽然他亲眼目睹过多次工伤事故,轻、重伤的,死亡的,血肉支离破碎的,什么样的没见过。死的念头,是一味毒药,是标准的高压电线,他不去碰它、触摸它,他把思绪和感觉置放在灿烂的信心里。他开灯看了一下电子表: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整。
六
二十日的家贵已经相当疲惫了。
敲管子更累了。但他还是敲。仿佛说:我还活着。他的两眼深深陷入眼窝,迟疑的目光投向自设的水文标杆。标杆已向水面倾斜,他也懒得扶正。水,像退了些,又像没有退。他关上灯喘息着。这天的他,神志开始恍惚了。他一会儿觉得小顺和周庆挤在自己身边,一会儿听到师傅在和自己划拳,一会儿看见彩妮的胖丈夫。他艰涩地睁开眼,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深深的地层,窄小的空间,只听见自己微弱的呼吸,真像无边黑夜里的森林,到处潜伏着野兽,想跳出来吞吃他。他蜷缩着,希望能看见一颗星一片月,可哪里有呢?他拧亮灯,估计照明还能持续多久。昏黄的光线落在身边废弃的纸张上,那是包瓜子用的书纸。家贵留着它准备当手纸用,一直没用上。
纸上的文字,在这段特殊的空闲里,家贵已通览过一遍。此时,在昏黄的矿灯前,他又一次费力地重温着: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地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朦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得这么惨。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地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好、更悲壮的了。
这是家贵残剩在大脑中的那段经历的最后一片羽毛——阅读。他联想到自己的处境:一边是水,一边是未燃之火:煤。在他看来,好像那段话就是为自己写的。区别在于:自己还活着,但前景不明。
家贵打这,就完全迷糊了。但对阅读这一细节很清晰。经过这场残酷的煎熬和磨练,家贵得到了很大教益,长进不少。
七
石家贵困难地读完纸片上的文字,拧灭了矿灯,调整好心态,开始长达六天的昏睡,其中,后两天是在矿工医院的特护病床上度过的。
二十四日晚,家贵像一只腊月里的青蛙,开始长长的冬眠。这是他与死神进行悲壮的决战。没有硝烟,兵不血刃。一名矿工憋足最后一股气,与死神顽强抵抗。最终,还是死神溜走了,家贵获胜。三十日上午八时五十三分,他醒来的那个微笑,简直是面光辉灿烂的旗帜!
石家贵被营救出来之后,安全检查人员按常对8.17事故现场做了原始笔录,在家贵腿边的棚腿上认出了一个字。其实这是家贵写给那只鼠的墓志铭。他把前面的两个字和后面的五个字给抹去,只留下一个字:
生。
责任编辑倪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