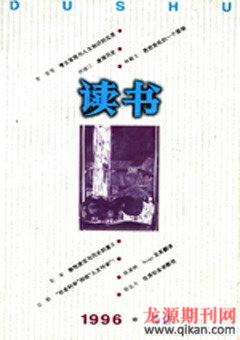族性迷信与历史的意义
东 来
一九八九年苏联退出了与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一九九一年美国仅用七十几个小时便打垮了中东军事强国伊拉克。美国人因此便有一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优越感。病态的欣快(euphoria)开始在美国政治中弥漫。政治家布什总统宣布要“建立世界新秩序”,政治策士福山先生也得出了“历史终结”的轻浮结论。但是,波黑经久不息的战火和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失败悄悄地把“世界新秩序”送进了历史的词语库,洛杉矶的种族骚乱和辛普森的“世纪审判”更使“历史的终结”成为笑柄。胜利与成功的欣快症遂让位于因挫折和失望而产生的新悲观主义(New Perssimism,有关评论见美国第二大国际事务杂志For-eign policy第一百期,一九九五年秋)。短短的三四年间,美国人便完成了一种情感变化的周期。“世界新秩序”尚未建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便开始盛行,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布热津斯基“大混乱”的预测便接踵而来(有关对亨氏和布氏两人理论的评论可参见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李慎之:《二十一世纪的忧思》,《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四期)。真不知是美国人在开历史的玩笑,还是历史在开美国人的玩笑。
值得注意的是,亨氏和布氏这两位国际战略大家对国际事务的悲观见解实际上都是源于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担忧,亨氏的冲突论得益于他对美国国内日益紧张的种族冲突的亲身体验,布氏的混乱观同样也摆脱不了美国社会衰败的影子。不过要从他们的大作当中寻找美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却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毕竟论述的是国际关系而非国内政治。实际上,早在他们两人之前,另一位学界政界两栖名人阿瑟·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已经比较深刻地阐述了美国思想界的混乱,提出了“美国正在失去统一”的惊人之见。他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今美国文化,同时也可以给亨氏和布氏两人的理论作个注释。
小施莱辛格的名字在欧美学术界可谓无人不知。他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与亨廷顿在政治学,布热津斯基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地位相当,都是属一属二的顶尖人物。但就他们对整个知识界曾有过的影响而言,施氏的地位可能更高一些。在七十年代对美国专业人士进行的一次调查中,施氏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美国二十名知识分子之一。他与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有着共同的背景:都曾受教并执教于哈佛,同时也出任过政府顾问的要职。不过,他比后两人年长十岁(施氏生于一九一七,亨氏和布氏分别生于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因此成名也更早。由于受其父、美国城市史研究的奠基者阿瑟·施莱辛格的影响,小施莱辛格从小酷爱历史,二十一岁从哈佛本科毕业,旋即负笈赴剑桥攻读研究生,但一年后就返回美国成为一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投身于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一九四五年出版了处女作《杰克逊时代》(The Age of Jckson)。这本被誉为“二战后最有影响的史学著作”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次年没有博士头衔的施氏破例被哈佛聘为副教授。当时其父也在哈佛执教,因此留下父子同为哈佛历史系教授的佳话。八年后,他晋升为正教授,此时基辛格、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这些七十年代的名流则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施氏一生著作等身,其中《罗斯福时代》(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千天—肯尼迪在白宫》(一九六五)、《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九八五)等著作多次获得普利策、全国图书等图书大奖。与相当一部分哈佛教授一样,施莱辛格并不满足于书斋生活,一直与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一九六一年他与几位哈佛精英一起成为年轻的肯尼迪总统的幕僚,他本人担任总统特别助理这一要职长达四年,为此放弃了自己在哈佛的终身教职。六十年代后期,他曾与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领袖并肩游行。但就是这样一位当年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今天却开始对民权运动在美国文化中造成的结果——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hsm)表示深深的怀疑和忧虑。
在其最新著作《美国正在丧失统一》(TheDisuniting ofAmer-ica,1992)中,施莱辛格一再强调,以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sm)、族性迷信(thecult of ethnicity)和制度化的双语教学(institutionalized bilingualism)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正在侵蚀美国人的立国之本:那镌刻在美国国徽上的合众而一(E Pluribus Unum)的理想。
所谓非洲中心论,是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世界史观。它的基本看法是,人类历史的发祥地在非洲,黑人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书上所写的关于古希腊的辉煌文明,诸如哲学、艺术、科学、政治理想与法律观念,都是古希腊人从黑人那里偷来的。换言之,现行的“欧洲中心”史观是欧洲白人历史学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意编造的一套神话,应当予以推翻,并重建非洲黑人为中心的世界史观。因此,必须用这种新的史观来重修美国大中学校的历史课本,改造原有历史课程的设置。在非洲中心论者看来,这种改造课程的努力是增强美国黑人自信心,提高美国黑人地位的重要举措。正如一位黑人学者所云,“拯救和重建黑人的历史是拯救和振兴黑人人格的不可缺少的部份”。(对非洲中心论的详细评论可参见已故沈宗美教授的论文:“作为一种世界史观的非洲中心论”,《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非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不能说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但是它太情绪化了,缺少起码的史料基础。对此,施莱辛格首先根据专家的考证,指出“非洲中心论”是以极不充分的史料和牵强附会的解说为基础。其次,这种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来曲解历史的方法,根本达不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增强黑人自豪感的目的,因为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从未认同过非洲的文化,也不关心非洲。他通过指出一系列受过西方教育的美国及世界上的黑人领袖人物来说明,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的现代西方人文教育并不妨碍培养出伟大的黑人。同样,犹太裔和亚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出色的表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多学了什么“犹太中心论”或“亚洲中心论”的课程。因此,“非洲中心论”对黑人的成长有害无益。他借用一位黑人专栏作家的话说,“非洲中心论”的教育只会使黑人孩子“在一个他们必须参与竞争的文化中处于劣势”。
在施莱辛格看来,“非洲中心论”只是族性迷信的典型发展,要彻底清算之,就要打破族性神话。族性迷信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只有本族人才能够真正理解和认识本族。因此,大学所开设的族性理论和历史的课程,只有具有同一族裔背景的教授才有资格讲授,推而广之,便有了只有女性才能讲授妇女课程,只有同性恋者才能进行有关同性恋研究的奇谈怪论。族性迷信不仅表现在课程上,而且也波及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对族性的迷信使学生相信,他只有与自己的同胞才可能进行真正的交流。于是,美国大学校园“像贝鲁特那样分裂成各种文化飞地”。曾经在一个半世纪前开美国黑白学生同校上学风气之先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今天成为分裂的典型:亚裔,犹太人,拉美裔和黑人,生活在不同的宿舍,甚至同性恋者也按族裔分成不同的团体,结果,“奥柏林学生的思、学、行、居完全分开”,大学失去了它应有的普遍性。对于这一分裂的图景,施莱辛格痛心疾首。“族性迷信夸大了各族裔之间的差别,加深了不满与对立,加强了各种族和民族之间可恶的鸿沟,结果只会是顾影自怜和自我封闭”。
族性认同的重要标志是语言。多少年来,美国不断用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来向世界各地的移民及其子女普及英语,英语教学成为使移民“美国化”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一些多元文化论者却认为强迫移民孩子学习英语,放弃母语无异于一种“政治压迫”和文化剥夺,为此他们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从未规定过英语是官方语言这一点,借助一九六八年《双语教育法》,开始倡导双语运动(bilingualismmovement),要求公立学校向移民(这里主要指拉美移民)提供用西班牙语讲授的课程。于是,西班牙语几乎成了美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通用语言。在施莱辛格看来,这种作法不仅使移民后代缺乏进入主流社会所需要的语言技能,而且“滋长了自我封闭,并由此滋生了种族对立”。因此,“帮助我们的学生流利地使用主流语言,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与能力而非剥夺”。施氏指出,更重要的是,一种共同的语言是使美国成为一个同质民族所必需的纽带,而制度化的双语运动则是对这一理想的威胁。
由于“非洲中心论”,族性迷信和双语运动是在多元文化主义旗帜下出现的,对它们的批评便可能涉及到“政治正确”(Poolitical Cor-rect,简写为PC)的问题。所谓“政治正确”就是强调一个人的言行不能对他人构成任何公开和潜在的冒犯。这种美国式的“政治挂帅”几乎渗透到美国大学生活的所有方面。在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学生处为了让学生“政治正确”,特公布了一份可能会使别人感到自己受到压迫的忌语。其中有:
异性恋至上(Heterosexism):对那些异性恋以外的性指向(sex-ual orientation)诸如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的压迫;这可能因为没有注意到他们存在而发生。
外貌至上(Lookism):相信外貌是个人价值的一项指标;建立某种魅力或美丽的标准,以及因为某种偏见或概括而断定某人符合或不符合这种标准所造成的伤害。
在施莱辛格看来,这种用“政治挂帅”来控制学生不文明的行为尚说得通,但把它作为控制教师和课程的工具则是对学术的蔑视。在古老的哈佛大学,两位资深的历史学家决定开设一门题为“美国人民的形成”的课程。课程简介刚刊出,有人便在校报上抨击这两位教授“缺少种族敏锐感”,政治上不正确。黑人学生更写了份长达六页的抗议函,指责其中的一位教授依然使用充满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气息的字眼,如谈到东方宗教时用了oriental(东方)这一形容词,谈到北美印第安人时仍然用Indians(印第安人)而不用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s)。这位被抨击的教授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族裔史学的倡导者之一,著名的《哈佛美国族裔集团百科全书》的编辑斯蒂芬·桑斯特姆(Ste-phan Thernstrom)。面对学生的抗议,两位教授只好放弃这一课程。
美国大学校园正在发生的这一切,让施莱辛格万分感叹。他写道,美国是多族裔人民融合而成的统一民族的理想正在被放弃,“融合转向族性,合一变成分裂。族性迷信正在使美国不再是一个有能力改变和同化其所有人民的国家。我们现在难道不是在贬损一致,美化多元吗?中心还将存在吗?抑或熔炉将让位于幻想中的通天塔?”
虽然施莱辛格把“非洲中心论”、族性迷信和双语运动看作是导致美国分裂的三种力量,但实际上,族性迷信是问题的关键。“非洲中心论”和双语运动只是它的衍生物。因此他把这些力量的代表人物统称为族裔空想家(ethnic ideologues)。“他们把自己置于美国悠久的融合理想的对立面。他们要求这个国家不是从个体而是从团体的角度去思考归属感,从而把政治关注的对象由个人权利转向集团的权利。他们在把美国变成一个更为分隔的社会方面已经有了进展。他们竭尽所能把大学生变成反对欧洲与西方传统的一代人。他们把种族中心、非洲中心和双语教学课程加诸于公立学校,旨在把少数族裔子弟排除在美国社会之外。他们告诉来自弱势社会集团(minortygroupsups)的年轻人说,西方的民主传统并不适合于他们。他们鼓励这些弱势集团把自己看作是受难者,让它们生活在各种托辞当中,而不是让它们拥有由于黑人的反抗和白人的负罪两者结合而产生出来的众多机会。他们让忆苦和积怨恶化我们的空气,进而明显地促进了美国生活的分裂化。”
施莱辛格的这番责难可谓慷慨激昂。但另一方面,他却把这场运动称为“一种精英而非民众的运动”。它的倡导者是那些被称为在“大学中取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他们至多是在恐吓白人,但无法吸引自己的民众。因此它注定要失败。
既然如此,施莱辛格又为何要大动肝火,以古稀之年与多元文化主义者较劲呢?这大概与其历史学家特有的职业敏感和责任有关。他深知,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教育,而教育的第一要义就是确定课程和教材。而族裔空想家正是由此发难,直捣美国的立国根基。因此,向美国青年一代灌输何种人文教育,便成为双方论战的焦点。因为学生在学校中所学到的东西最终将影响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我们看待其他美国人的态度,我们观察这个国家目标的方法。对课程规划的辩论就是一场对什么是美国的辩论,问题的要害则是未来美国的塑造”。
对族裔空想家为了现实需要而重构与删改历史的作法,施莱辛格尤为深恶痛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把历史作为武器是对历史的滥用”,而“把历史作为救世良药(therapy)则意味着对历史本身的亵渎”。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任何民族、文化或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曾有过犯罪、暴行和恐怖,“每一种文明在其深处都藏有骷髅,诚实的历史呼唤未经删改的记录”。但是,如果让“族裔自豪与自尊成为历史教学的标准,那么许多事情就无法讲授。因为骷髅必须藏匿起来,以防止它令后人不快”。他颇为意味深长地指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历史(feelgood history)是对这一崇高职业的背叛”。因为“历史的目的不是促进集团的自尊心而是理解世界和过去。只有不带情绪的分析、判断和视角,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与传统,并坚定地保护宽容、民主和人权这些难以分割的思想,才有可能对历史进行自由的探讨”。
我们尽可以不同意施氏这种貌似客观的史观,因为其实质可能是为西方文化与价值辩护,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对历史实用主义的批评的确令人深思。我们对纳粹德国为鼓吹日尔曼人的伟大而编造历史的恶行嗤之以鼻,我们对日本官员和文人修改其历史教科书的丑行义愤填膺,我们对我们自己曾经历过的影射史学深恶痛绝。可是,我们是否想过,这些极端的事例却来自一个许多人都认同的、并不卑劣的观念,历史应该是一个“求用”的工具手段,而不仅仅是“求真”的知识追求。
现在该是重新思考历史的意义的时候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四日于南大—霍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Arthur Schlesinger,Jr.,TheDuniting of Af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rural Society,NewYork:W.W.Norton&Company,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