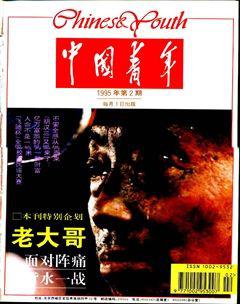橙红色的太阳
梁粱
司玉杰,沈阳人,男,38岁。现为中国广播艺术团男高音歌唱家。
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歌唱演员,我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这就注定了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
小时候,我的老师就是一架破旧的收音机。听完一首歌,我就躲进小屋,亦步亦趋地学唱。父亲听着心烦,训我:“干什么不好,整天价就知道鬼哭神嚎,烦不烦?”10岁那年,我参加全市少儿歌咏比赛,得了奖,并且,收音机里还给播了出来。父亲听了,一脑门子疑惑:“这能是你小子唱的?”我自豪得脸放红光:“那还有假!”“你要真爱唱,就唱吧!”父亲大赦般地恩准了我的爱好。
70年代,我到农村插队,贫困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没有扼止我唱歌的热情。每到休息时,总会有人嚷嚷:“小司,给大伙来一首。”我就扯开嗓子,痛痛快快地唱个够。田间地头,总是聚拢来许多老乡,听我唱。
回城后,我成了一名水暖工人。每天大清早,我就寻一僻静所在,吊嗓子,练声,风雨无阻。
1986年5月,我参加沈阳首届“五月的鲜花”音乐周,获得表演一等奖;6月,参加沈阳市职工歌咏比赛,获得一等奖;7月,获辽宁省军工系统优秀文艺节目调演男声独唱一等奖。随后,我参加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获得优秀歌手奖:在全国民族民间音乐比赛上,我以一首《山歌越唱越亮堂》获二等奖。很快,我又被辽宁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聘为特约歌唱演员……认识我的人都说1986年是我的幸运之年。但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为这“幸运之年”的到来,付出过几多辛劳和汗水。
不久,我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成为一名专业歌唱演员,但我并未停止对歌唱艺术至真至美境界的追求。去贵州山区演出,我登上大山,面对茂密的森林和飞悬直下的瀑布,细细体悟和寻找贵州山歌那纯朴、粗犷的感觉。去陕西演出,我请来当地的民歌王,请他唱“对面沟里流河水,后山上下来些游击队;一杆杆红旗崖上插,快把咱们的游击队带回家”。——我觉得那才是真正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苍凉的歌声里,自有一种朴拙而又直逼人心的悲壮和感动。那以后,我再唱“信天游”,才觉得我真正进入到歌里去了。从台下观众热烈、激奋的掌声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去内蒙古草原演出时,我请当地的服务员小姐唱“长调”,我又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演唱的感觉……
这些年,我多次作为中国歌唱家艺术团成员出访欧、亚各国,我的歌声受到国外音乐界同行和广大华侨的高度赞誉。在这同时,我没有忘记田间地头上喜爱听我演唱的乡亲们,所以,我每年都要到基层和生产第一线演出百余场,我觉得那些乡亲和工人师傅们需要我的歌声,而我更需要为他们演唱,因为他们是我艺术上最权威的评判者。他们亲切地称我“咱们最贴心的歌唱家”时,我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述的。
至今我有个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那就是成为一名战士。唱歌和当兵,曾作为我的两大心愿,照彻过我少年的心空。如今,我已成为一名歌唱演员,而当兵的愿望却只能默默地存留在心里,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所以,每次登台演出,除了唱工人、农民喜欢的歌,我总要唱一首与军队和战士有关的歌。或许,这对于我那未能实现的心愿,也算是个小小的补偿吧!
去年,我自费出了一盘个人演唱专辑,我给这盘带子取了个名字,叫“军旅情怀”,因为专辑中绝大部分歌都与部队和战士有相关,像《水兵想念毛泽东》《一支人马强又壮》《怀念战友》《八角楼的灯光》《西沙,可爱的家乡》等,其中首《可爱的甘巴拉》。1993年6月28日,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签署命令,授予驻藏空军某部甘巴拉雷达站“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光荣称号,当我从报纸、电视上看到那些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山上,在严寒、缺氧、缺水的恶劣环境下忘我奉献的战士们的事迹后,就一心想为甘巴拉的战士们写一首歌。最后,由空军军供部副部长司树杰同志作词、我作曲,共同完成了《可爱的甘巴拉》。我曾在不同场合唱过这首歌,凡是了解甘巴拉情况的指战员,无不流下激动的泪水。
1993年底,我去天安门国旗班,向战士们赠送磁带,应他们的要求,我清唱了《可爱的甘巴拉》,位战士听完后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们国旗班也写一首歌。我当即就答应了。他们护卫国旗的英姿,他们铁一般的意志,钢一般的信念,太值得讴歌和礼赞了。我相信,这首歌一定也会像《可爱的甘巴拉》一样,给人们以深刻的感染和启迪。
作为一名歌唱演员,能够写出、唱出反映时代,讴歌英雄的歌曲,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骄傲和自慰的呢?所以,我是幸福的。曹锐,女,1973年生。白求恩医科大学学生会学习部长,运动健将。吉林省优秀共青团员。
柳青说过:一个人的一生往往只有关键的几步,特别是当他年轻的时候。——这话我信。
我就读的中学是全国13所重点之一的东北师范大学附中。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都是最好的。但高三下学期,祖母病危,我和母亲轮番在医院作全天候护理,加上高考前紧张的复习,我得了神经衰弱。老师知道我的实力,就把唯一的保送名额(哈尔滨工业大学焊接专业)给了我。但这与我的理想相去太远。我放弃了这一机会,坚持参加完高考。成绩令我失望,根据分数线划到我名下的学校更让我沮丧:长春某专科学校。我面临着又一次抉择:上,还是不上?我选择了复读这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路。
复读那一年里的情形,正如我一篇日记里所写的,是“在很深很深的怅惘里,等待命运转折的时刻”。已经进入大学的昔日同学的来信,常常使我烦躁莫名。尤其是大年三十之夜,充耳是四处噼啪炸响的爆竹,满世界都是辞旧迎新的一派喜庆,而我,只能躲进自己的小屋,为半年以后吉凶难料的高考,忐忑不安。那是我记忆里心情最为灰黯的大年三十。
天遂人愿,我终于大功告成,以优异成绩进入白求恩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我欢欣雀跃。医大的师资、设备、学习环境都是全国一流的。我庆幸自己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医生,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若说缘由,自然有的:我这条命就是医生给拣回来的。我小时候心脏有毛病,医学上叫作“动脉导管未闭”,发展下去很危险。医生们成功地为我施行了闭合手术。我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伯伯的脸。“疼吗?”医生伯伯的脸上漾着慈爱、温馨的笑容。我说不疼;他就让我好好躺着,别乱动,他很快会再来看我的。然后,他轻轻地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觉得很踏实,很安全。直到伤口开始隐隐作痛,我也使劲忍着,因为我相信那个医生伯伯很快就会再来看我,只要他一来,就会将疼痛从我身上赶走。
这以后,每次见到当医生,我就打心眼里觉得亲,同时,也近乎固执地认为,他们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他们的双手都是具有非凡魔力的,可以轻易地将一切病痛和不幸从人们身上赶走。一个强烈的愿望便在我心里扎下了根:长大以后,我要当一名医生!
进入医大,我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找到了用武之处。理论课,临床实验课,我孜孜以求,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很快,我便不再满足于教室和实验室的狭小天地,我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施展所学,为身患各种疾患的病人,解除病痛的折磨,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机会来了。医大的白求恩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决定赴吉林双阳,为当地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带着踌躇满志,准备一展身手的冲动和欣悦,我率先报了名。
到双阳后,经过短暂的调查摸底,当地极为恶劣的医疗状况首先便深深地震撼了我们。数千人的村子,只有一名卫校毕业生,这还是好的。但凡村民患病,无论病情轻重,就是打吊瓶。有的人开始时病情并不重,却因为明显的误诊,加上滥用各种忌用或慎用的激素类药品,轻者不能得到正确、及时的治疗,枉受了许多痛苦,重者则加重病情,甚至致残、致死。更严重的是,因为地处偏僻,从未接受过科学的医疗知识,人们的健康观念都是畸形和不健全的,而错误的健康观念又必将导致错误的治疗,最终贻祸自身。有一个38岁的病人,几年前怀疑自己得了胃病,就找来土方,将面烧成灰和着碱喝下去,他这么做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为他作了检查,确诊他原来得的是爆发性胆囊炎,错误的治疗,没有治好他的胆囊炎,他却真的患上了慢性胃炎。说真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一直都处于一种深刻的感动中,为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为至今仍处于病痛折磨中的村民们。但认真想想,这份感动却决不应该是目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感动是很容易引发的。重要的是,感动之后作一些深入的思考,对人生,对社会。
我不知道在半个来月的时间里,看了多少个病人。问听诊,作诊断,开处方,每一道程序和环节我都一丝不苟地去做。遇有疑难病症,我就虚心向随队的专家、教授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再仔细作复诊……看着病人们满意而去,我的心里漾起一股喜悦与自豪。那是一个医者最由衷的自豪。我为我当初的选择而庆幸。
我想,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变故,我将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医生。这是我一直为之追求的理想。我想告诉我的同龄人,认准了一条道,就潜心以求,而不应该让许许多多的诱惑迷住自己的双眼,或者让一些挫折滞住你奔向彼岸的双脚——这一点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