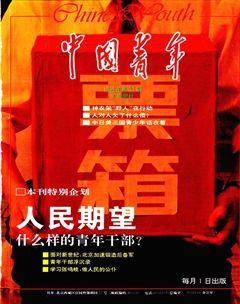神农架:“野人”在行动
刘新平
位于鄂西川东边境、面积3250平方公里的神农架,山高水长,林海苍茫,峰峦交错,脊岭连绵。在海拔3000多米的神农之颠,更是云雾缭绕,常年冰封雪覆,寒冷异常。在这里,百多公里方圆之内,了无人迹,唯有猿声夜啼,狼群长嗥,给这古老、蛮荒的神农顶平添了一份恐怖,一丝肃杀!
然而,就在神农顶的眺望塔里,有一个普通的复员军人曾经生活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些个日子里,他邀山川作伴,与日月共眠,搏风击雨,以一双锐利的目光,警惕着茫茫神农,稍有风吹草动,他便会似矫健的猎豹,作神速出击,消弥火灾于将起之际,制止盗伐于猖獗之时。峰峦无声,山林无语——但灵天秀地的神农架,却在悄然寂静中,记取了他不寻常的功业,也记住了他的名字——袁裕豪。
共和国成立之初,神农架顶峰曾驻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日夜观察山情,护林防火。但由于供给艰难,无法生存,于1956年撤下山去。1985年,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在神农顶建起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现代化眺望塔并准备选派一名哨兵长年驻守。其主要任务是防止森林火灾,树木被盗;观察报告生态情况,保护珍稀野生动物。
但是,这个哨兵谁能胜任?深山密林的荒野之气,虎啸狼嗥的恐怖之音,何况还有流传于世上的诸多关于野人的传说,谁又有胆量置身此间?
袁裕豪站了出来。这位原广州军区某部一个普通的炮手,有着一张坚韧果敢的脸庞和一副筋骨强健的高大身躯。他的出现,使眺望塔迎来了它的第一任哨兵。
在神农架林区,我曾请袁裕豪谈谈他上眺望塔的初衷。他搓搓骨节粗大的手掌,腼腆地笑了:“其实也没得什么好讲。当时那里缺人,就去了。”
“考虑过环境和生活都会是相当艰苦的吗?”
“这一点当然想到了。不过,那么多原始森林和珍稀动植物不去保护是不行的。我上去苦,别人上去也一样苦啊!”
“所以就义无返顾地去了?”
“是这样。”
其实,说起眺望塔的苦,绝非常人可以想像。虽然保护区尽了最大的努力派人运送给养上山,但实在是难以做到充裕、富足。也确有一台风力发电机,但由于风太大,扇叶总是被刮坏。他就只能点松明。每到夜晚,伴一盏孤灯和四周的兽声树语,更加映衬出眺望塔的孤寂、清冷。那条距眺望塔最近的小溪有几千米远,小径曲折难行,山石上布满青苔,挑一挑食用水登上眺望塔是一项绝不轻松的工程。为了省时节力,他就用一只大铁筒接塔顶的雪水。雪水吃得多了,肠胃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又因为山高风寒,塔内阴冷潮湿,时间长了,风湿病也如约而至。有时周身的关节疼起来,他会抽搐不已,直感到再也挺不过去了。到了冬天,山上铺满1米多深的积雪,给养上不来自是小事,巡山成了最大的难题。平时半个时辰就能走完的山道,他至少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那不能称作走,只能叫做连爬带滚,体力的消耗是惊人的。每次巡山回来,他常常是瘫了一般,慢慢地才能挨进眺望塔……这一切他都以顽强的毅力忍受了下来。除了每天往返数十公里的例行巡山,他还得每天十多次登上18米高的塔顶,用望远镜观察百余公里方圆的山林。
5月,是神农架最好的季节。山坡上,竹林裹身,杉叶滴翠,杜鹃摇红,煞是神秀诱人。而背阴处则幽谷深沉,神秘莫测;石林突兀,奇绝天成。无论晴空万里时,或云雾缠绕中,神农架那神奇脱俗的身姿容貌,都会让所有外来者陶醉其中,乐不知返。
但袁裕豪的神经却无法在这天然美景中松驰下来,因为盗伐者随可能窜进出林。“笃笃笃”,他敏锐的听觉捕捉到这令他心颤的伐木声,他象一只发怒的猎豹奔到盗伐者面前。一方坚持要伐,一方坚决制止。盗伐首先发难,三个人同时欺身上前,要揪打袁裕豪。凭着部队里摸爬滚打练就的一套好拳脚,袁裕豪几下就将对方制服。盗伐者们无计可施,怏怏地准备下山。却再次被喝住。袁裕豪令他们坐在地上,宣讲了足有一个小时的《森林保护法》。“你们都明白了吗?”“明白了!”盗伐者诺诺连声。“可以走了!”袁裕豪挥挥了手。“这家伙,真象个老八子(当地土语,意为老虎)”。下山的路上,一名盗伐者对同伙说……
一个秋日的上午,袁裕豪在塔顶发现10公里外的猴子石一带有一股浓烟升起。说是烟,不如说那只是一股似烟似雾的灰褐色云团。神农架多雾,茫茫浓雾左旋右绕,常常将整座山峰掩没掉。袁裕豪对着望远镜,凝视良久,终因见不到火苗而无法确认。突然,他隐约听见炸裂的声音,那是蒿草和干枯的树枝被烧着后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声音。袁裕豪意识到一场可怕的山林火灾已经发生。眺望塔没有通讯设施,最近的报警点在数十公里外的鸭子嘴哨卡。袁裕豪无暇多想,端起冲锋枪,打出了所有子弹,随后,急速下楼,向鸭子嘴方向急奔。他选择的是一条最为快捷的下山路线,但途中的障碍也空前的多。密林、深谷,嶙峋的山石,陡峭的岩壁……他步履矫健,身形如飞。衣服撕烂,面颊刮破,他全然不顾,只知一个劲地拔足狂奔。“火、火、火……”他嘴里念叨着,心里也像着了火。终于,他喘着粗气闯进了鸭子嘴哨卡。听见管理人员用电话通知了保护区,他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算稍稍平静下来。
走出哨卡,他没有回眺望塔,却直奔猴子石。在那里,他与灭火队员一起,奋力扑火。因为报警及时,大火尚未形成气势,两个时辰之内火便被扑灭了。
等袁裕豪摇摇晃晃地推开眺望塔的门,他已是精疲力竭,浑身直如散了架一般。他像一块倾倒的巨石,一头扎在床上……事后,有人统计,那天袁裕豪至少来回奔行了70公里,加上马不停蹄地参加灭火,这对于一个人的体力而言,绝对是超过了极限。就连袁裕豪也对自己身体的承受力大感惊讶。
“意志和信念常常能使一个人的身体极限膨胀出数倍甚至数十倍。”我说。
“好像是这样。”袁裕豪点点头,“当时我真是急了。俗话说,水火无情。原始森林的火更是可怕。那片森林若是被毁,国家的损失该有多大!所以,我实在是顾不了别的,现在,要是让我不歇气地跑个几十公里,我还真做不到。”
如果说山火易扑,袁裕豪巡山时的刚直与严厉在那些盗伐者中引发的满腔怒火却是难以轻易扑灭的。一次,他巡山归来,一进门就傻了眼。屋子里锅碗瓢盆被砸得狼藉一片,缸里的粮食和厨房里的蔬菜也不翼而飞。床上,还被恶毒地撒了一泡尿。好在山上长满野果可以充饥,才让他度过了一段艰难日子。但与不久后发生的事件相比,这种施虐式的报复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一个霪雨霏霏的下午,袁裕豪又抓住了六七个贪婪的盗伐者。本来,他想给他们宣讲《森林保护法》,考虑到下雨,他临时决定将课堂移到眺望塔。领他们回塔途中,一个盗伐者摔了一跤(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一种故意),袁裕豪弯腰准备拉他起来,谁知,一根木棒从他身后猛然袭来,那令人猝不及防的重重一击,使袁裕豪轰然一声,栽倒在地。等他醒来时,已是雨过天晴的中午,阳光透过树木洒下的点点光斑在他眼前晃动。他觉得头晕目眩,摸摸后脑勺,针刺一般的痛。他已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昏迷了多少时间。他强挣着爬起来,找了一根树枝撑着,一步一晃地坚持到了眺望塔。
“现在这头还常常隐隐作痛。”袁裕豪告诉我。
“那帮家伙后来抓住了吗?”我问。
“难呢!不少都是从外地来的,来无踪去无影,不好抓!”他苦笑笑,“不过以后再碰见滥砍滥伐的,我还是得管。得罪小家,有益于国家,自己受点苦遭点罪,值!”
回忆起眺望塔的哨兵生活,袁裕豪说他其实也有着常人难以体验到的快乐。孤寂落寞中,他学会了与过往的金丝猴或苏门羚交朋友。每当有金丝猴或苏门羚从塔前经过,他就吹笛子给它们听。但他慢慢发现,每当笛子里传出尖锐的高音,它们就纷纷走避或作烦躁状。他明白了笛子的高音对它们而言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噪音。它们其实是极喜欢悠扬、舒缓的乐曲的。于是,他将乐器换成一支竹箫,常常他吹累了,它们还不愿意离去。他停止的时候,它们就会作出种种不满的表示。在强烈的抗议面前,他只有屈服,再吹。
有一次,一只年幼的金丝猴受伤离群,袁裕豪将它抱回眺望塔,悉心喂养、疗伤。两个月后,他将痊愈的金丝猴送回猴群。过不几天,他早上刚推门出来,那只他送走的金丝猴早就候在那里,只一跃,便扑进他的怀里。金丝猴如此重情重意,使他的心里涌上一丝温馨的暖意。
在尚未去眺望塔之前,袁裕豪就是一个“野考迷”,是神农架野人研究会会员,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队员。在眺望塔期间,虽说任务繁重,可他还是忙中偷闲,从事他的“野考”工作。
1989年4月20日,袁裕豪的爱人来到眺望塔,夫妻双双去巡山。在神农风景垭以西几公里处,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就在离他们20多米远的地方,一个红毛怪物正躺在积雪之上。“野人!”夫妻俩同时惊呼。袁裕豪冲爱人挥挥手,猫腰向野人靠拢过去。野人的听觉极其敏锐。它站了起来。一身红毛,肥臀丰乳,双臂奇长。袁裕豪慢慢举起枪向野人瞄准。但野人却突然转身,飞也似地向密林遁去。
“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野人和野人留下的奇异脚印。”袁裕豪笑了,很满足很惬意的样子。
1989年底,袁裕豪被调到海拔较低的漳宝河哨卡,在履行哨卡严查严堵的工作职责之余,他总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去巡山。他觉得他与神农架的高山密林已经有了一种须臾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虽然他在离开眺望塔的第二年就因长时间的营养缺乏而突患爆发性急性黄疸肝炎,差点将命丢在了医院。但刚刚出院,他的身影就又出现在山林之中。看他的步履身姿,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刚刚跨出医院大门的肝炎病人。
因为海拔较低,山林的入侵者便也多了起来,割漆的,挖药的,利用各种现代化工具滥捕滥猎的,防不胜防。袁裕豪不由得紧张起来。几乎每次巡山他都有所截获,或捣毁药棚、漆棚,或收缴钢丝套、猎枷、绳网等捕猎工具。他的冷面无私未改,刚直果决愈烈。“袁老八子”威名更甚!
但盛名之下,老八子亦难免败走麦城之窘。1992年春日的一天,袁裕豪与关门山管理所的谭明光所长一齐去巡山,途中发现一帮药贩子正在他们头顶的一处山崖上偷挖药材,而那帮人也几乎同时发现了他们。为了到手的药材不被收缴,那帮人首先发难,向崖下猛扔石块。没有防备的谭明光被击中,头上鲜血直流。他们只好紧贴崖壁,躲闪如雨的石块。袁裕豪急得搓手顿足,却又无计可施。既不是短兵相接,再好的身手也无法施展。看着身边鲜血不断流出的谭明光,袁裕豪咬咬牙,一哈腰从崖下窜出,向前猛跑。他的出现,吸引了药贩子们的注意力,石块纷纷落在他的身前身后。他一边左躲右闪,一边拣起石块向崖上回击。崖下的谭明光趁隙脱离险境,赶回了管理所。
这次经历,使袁裕豪更加坚定了看山护林的决心。他巡山更勤,执法更严。在哨卡,检查起来一丝不苟,那些想偷运木材和药材出山的人,都将经过漳宝河哨卡视作畏途。他们知道要想从袁裕豪眼皮子底下踏出一条道来,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有一件事似乎最能说明问题。一次,一所中学从山里拉了两卡车烧柴,袁裕豪按规定照收了50元钱,而他的儿子就在这所中学读初中。隔不几天,他的儿子就被学校勒令退学。袁裕豪什么也没说,将儿子送到几百公里外的一所学校就读。“我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就将保护区的规定视作儿戏,随意更改。我更不能拿国家的财产去做交易。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和党性决不允许我这样做!”
说实话,虽然早有人向我描绘袁裕豪,说他整个就是半个野人,但第一次见到袁裕豪,我的第一感觉还是大吃一惊。他面容苍老,额上皱纹横生,这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头发枯涩,一如秋后的蒿草;牙齿脱落了近三分之二,这些都是久居山野留给他的严酷的纪念。他语言木讷,口齿不清,唯举手抬足方显出几分敏捷。这与我们熟知的有关野人特性的文字记载,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却给予我越来越强烈的震撼。在我眼里,他成了一条豪侠仗义、祛除邪恶的好汉,一个无私无畏的真君子、伟丈夫。曾经吃了许多苦头,饱尝了许多艰辛,而献身神农的初衷不改。每天,他都把身影留在林区的每一条小道。栉风沐雨,无怨无悔!
大矣哉,“野人”袁裕豪!
——红其拉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