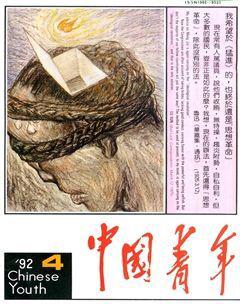今天的太阳与昨天不一样
竺晓政 魏群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上午,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一回。这是他到任后参加的第一个会议:生产经营分析会。公司与基层的大小头目们都来了,只是没有一位党务部门的同志,习以为常了。整整一个上午,烟雾缭绕中人们睡眼惺忪。一会儿推门进来个趿拉着拖鞋的找人,一会儿冒出个穿小裤衩的叫人,这哪里是在开会,简直是赶大集。
他愤怒至极地宣布:暂时休会,告诉各办公室,这里不是集市,也不是澡堂子,穿戴整齐再上班。
下午,他终于又一次忍无可忍。
这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长得要命,俗得要命,烦得要命。眼下天津储运公司是个什么形势?1~7月份,欠利润计划209万,欠利税计划134万,完成全年任务似乎已注定无望,4000名职工1991年一级效益工资长不上,1990年已长的一级也保不住。不仅如此,中国储运总公司是物资部第一家工效挂钩单位,天津公司作为全系统四大支柱之一,与总公司的整体效益息息相关。可是,咋就没看出在座的有哪个着急上火呢?呷巴着已经冲得没了色儿的茶,每个人都重复着说了一百遍一千遍不疼不痒不咸不淡的车轱辘话,什么“疲软”、“滑坡”、“最大的稳定是没出问题”,归了包堆就愣不往那实质性的问题上捅。
“这会打算开多久?”他问。
“两天。”
“两天?扯淡!现在就散会!”他一反新到一地缄默数日的习惯,情不自禁地数落开了。
“听你们这会,哑巴都能气得说出话来,你们侃天说地,自我感觉良好。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在内外严峻的形势面前求稳怕乱,不思进取,怎么带领大家去闯难关?现在我请班子里的同志想三个问题:从去年高速班子后,你们都干了什么?在公司困难时刻,你们都在想什么?你们都适合做什么?上秤约约,对着镜子照照……”
吕晓明,物资部最年轻的部属总经理,中国储运公司的一把手,危难之际主动请战到天津二级公司兼任总经理与党委书记。来者不善,与会者面面相觑。
在吕晓明的办公桌上,放着上送的两摞材料,行政管理方面的约有二寸厚,党务工作方面的足有一尺厚。他翻阅着《中储天津公司宣传工作竞赛半年检查情况小结》,文中内容令他啼笑皆非。思想政治工作、双基教育、通讯报道、黑板报、广播宣传橱窗等均以打分和好中差论处,而基础分名次均在80分以上。且不说人的活生生思想怎么就能通过那没有生命的分数套检出来,让人更难以搞明白的还有一个亏欠上百万元的企业竟然思想政治工作十分出色,这莫不是一种嘲笑、一种讽刺?他忿然,提笔在这份材料上写道:“通篇空洞无物,形式主义东西多了一些,今后这种活动要少搞,给基层减少一些麻烦。这种东西复印多了岂不是浪费?!”党务部门的同志受不了啦:“这不是一手硬一手软吗?”他们也有自己的辙,先送你顶改革者观念新的高帽,然后不软不硬地请示:“天津公司党务工作同时受总公司和地方物资局党委的领导,二者明显有不一致的地方,听地方的还是听总公司的,请明示。”“够水平,先戴帽,后拴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挑拨关系。”吕晓明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们:“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谁也不会提倡脱离本单位实际的形而上学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问题显而易见,工作只有一个中心,企业就靠效益说话,天津公司的上层机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基层生产经营的发展和能量的释放,非改革而别无他路。
其实,用吕晓明的话说,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这是大中型企业难以搞活的带有普遍性的致命伤。中国改革喊了十几年,只是谁也不敢真的给它作大手术,在关键的问题上,多数是想绕道走。宁肯不过河,也不去摸那块石头。
吕晓明不想回避。
他和天津公司的同志们,经过几上几下的讨论,形成了“小管理、大经营”的机构改革框架和机关“拆庙送僧”,基层“建殿请神”的工作展开思路。
——领导班子的调整要一改过去“到届、到龄、出问题才调整”的传统,每个成员都放在效益的筛子上过滤,干事不干事,会不会干事是评价前提。
——公司原有吃管理饭人员245人,机构20个,人事重叠,层次过多,把它精减到7个机构44人足矣。
——效益下降本身就是企业党的工作的失误。要坚持纠正那种不正常的倾向:一强调党的工作就是机构升格、官加一品、编制扩大。调精兵强将,搞党政兼职,从组织机构上为解决党政两张皮提供保证。
——庙没了,僧往何处?富余人员设计4条出路……
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不带硝烟的战斗,虽然无声,却也无情。
宣布机构改革方案出台的前夜,吕晓明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几乎没停。关心他的领导们既为他的设想与魄力而兴奋,同时为他捏一把汗。甭说别的,一封匿名信,就可能遭到身败名裂的下场。“晓明啊,三思而行……”
北京的朋友把他远在北美的妻子搬出来挡驾,她从大洋彼岸打来电话:“晓明,你该懂中国的国情……”如此之大的动作会带来怎样的震荡和后果,吕晓明心中也没有底,他在层里来回踱步,眼睛一直睁到天亮,脑子一直想到天亮,尽管这一夜他吞下了12片安眠药。
他想到,改革就是探索,探索就有风险。自己放着京官高官偏偏到这里来捅“马蜂窝”,就是要为企业改革蹚一条路子,没有风险还轮不上自己来呢。
他想到,机构改革动员会后,上上下下反馈的98条意见表明,群众切盼改革,真心支持他动刀子,这就是民意。他想到,1984年天津公司机关曾为精简一个人而闹得天翻地覆,结果机构越减越大,这种高喊“狼来了”的改革,只会伤害老百姓的改革热情。这次不能重蹈覆辙了。
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没出息。
彻夜深思,吕晓明把个人荣辱抛到九天之外。
1991年9月12日,机构改革方案如期出台。
你是代价,也是收获
想改革,喊改革,盼改革,而今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是做好龙的叶公,还是让改革的车轮从自己身上辗过,面对这道试题,津储人笑不出来了,人们需要蘸着委屈的泪水和难以下咽的苦水来填写这试题的答案。
马金桩,1986年当上公司副总经理,连任三届。据说之所以连任,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不得罪人。这一回,马金桩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手术刀会首先落在自己的头上,他被列入出班子、下基层的行列。他很忿然:生产上不去,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应该集体负责。他很委屈:干了这么些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成绩还有资历啊!
他很想不通:我既没政治问题,也无经济和生活问题,一身洁白,怎么能随便对待干部,我这面子往哪儿搁?
他想的似乎都有道理,在那个四平八稳、一劳永逸的“大锅饭”体制下,无疑他的理由都成立。这么些年,谁不这样想,谁不这样干,谁不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中混得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然而,他错就错在忘了改革就是要打破这旧体制,让人们换个活法。
他去申辩,吕晓明告诉他:这些年你是没什么错误,但也没什么政绩,没有政绩本身就意味着工作失误;老好人其实并不是没有毛病,只是他心思没有完全用于干事上,减少了被人评说的机会;你的面子固然值钱,但4000名职工的面子更值钱。
他也狡黠:“那请让我在出班子之前调走。”吕晓明斩钉截铁:“企业耽误得起人,耽误不起事,给你3天时间……”
他终于没能调走。值得欣喜的是,改革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想的、说的、做的已经完全是带着发自内心的“改革味”了。
那天,他掏着心窝子对记者说,“改革是一个实践过程,实践能证明一切,说明一切,改变一切。要不是亲身实践,能上能下这种事确实难以接受。老说观念转变,不碰上具体事,不把自己摆进去,观念变革就永远是挂在嘴头上的空话。如果你当初来采访我,我不是拒你千里之外就是大发牢骚,现在不同了。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平庸是最大的错误,四平八稳只能窒息企业的活力……”他滔滔不绝。
双向选择,自由组阁,第一天无人问津她,人们楼上楼下搬桌子抬柜子以及冬冬冬的脚步声震得她心发慌,但她还是硬撑着,谁都不找,堂堂的党办主任兼宣传部长,能说会写,怎么能没人要呢?结果,确实没人找她。前所未有的失落,她哭了。
朱广荣,从1966年至今从事党团工作已有27个年头,颇有“牛大姐”那份责任感。面对天津公司的危机,她抓主人翁教育,抓社会主义优越性教育,整材料,写报告,搞评比,开现场会,她为自己高度的党性和勤勉沾沾自喜。可是到头来,没人买这个帐不说,自己还因此被抛弃。究竟是大伙儿错了,还是自己错了?她终于把“手电筒”照向自己。
自省是痛苦的,痛苦却是一服清醒剂。
她找到吕晓明,递上一份要求下基层从头干起的申请书,然后抖落出她夜不能寐的反思。“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没睡好觉。我没有想到多少年来总是我革人家的命,这一回改革却改到我的头上了。仔细想想,20多年,虽然也很努力,但虚的、花架子的东西令人生厌,两股道上使劲,越努力添的乱就越多,自己更谈不上长进。是改革救了我。不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下半辈子搞不好我就是个废人。”
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发自内心地想改变自己,重新塑造自己更宝贵的。本来,对她是准备降职使用,但她的自省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启迪,这是改革所赋予人们的一种内在力量。她没有被降职,到南仓一库任副经理,几个月来,她既熟悉了业务,又发挥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长,有的放矢,她获得了职工的认可和尊重。
赵丽,34岁,女性。人们的评价:是一个能干事,想干事,也能干好事的人。但个性强,性子烈,脾气急,容易遭人嫉妒,被人看不惯。
半年前的今天,她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借调”历史,正式成为天津公司经销部的会计。那天,她把两个月的工资全部买了糖果,分发各科室,“大家替我高兴吧。”她乐得合不拢嘴。部主任拍着她的肩膀说:“赵丽,你是干出来的。”
她是干出来的。只身去南京催回“死帐”,人家留她玩两天她不肯,因为家里有工作等着她;去北京订合同,为赶头班车,她让丈夫把孩子反锁在屋里,骑自行车送她去车站……她从来都对自己充满自信。
然而,半年后的今天,她的自信被粉碎了,组阁没有她,她成了被精简的对象。
赵丽痛不欲生,她要找总经理问个明白。总经理在开会,她就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夜,等了一夜,哭了一夜。伍子胥一夜愁白了头,而她清晨梳头,头发掉了一大缕。
见到总经理,她很冲动:“改革应留住精华,如果一定要我下去,我现在就跳楼。”
“改革不希望死人,但也不怕死人。干企业就是谁掀我的锅,我就砸他的碗。”吕晓明兵来将挡,他懂心理学。
抽泣。痛哭。沉默。
“你说你是精华,你死了,还有什么时间什么机会来证明你自己呢?英才需要社会、实践和时间去承认……”吕晓明循循善诱,激将与开导并用。
抽泣。痛哭。沉默……
“那好,我下去,我是为改革而走的,希望能记住南仓二库有一个不情愿下去的小小的赵丽,怀着满腔的委屈为支持改革留在那里。”
正值月到中秋,别人都回家团圆去了,赵丽含着泪在办公室里整理准备移交的文件,她爱人包了饺子给她送来,说,“十五的月亮是圆的,你不回家,孩子想你啊。”她哽咽着:“就让我干吧,今年十五没有了,明年月亮还会圆,我欠你和儿子的,我一定补上。”
赵丽下去了,她觉得总经理的话有道理。
可是,没几天闲话出来了,连她的爱人也有了猜疑:“改革顾名思义就是卸包袱,你干得这么卖劲,为什么要裁你,肯定是有那方面的问题瞒着我。”
“那方面的问题”,不言而喻,这是一个人“不检点”的专用词。
赵丽有口难辩,她的精神垮了。一个星期不吃不喝,安眠药失灵了。一天半夜,她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急得她爱人嚎啕大哭,把一瓶子速效救心丸塞进她的嘴里。
……
当然,赵丽最后没有死,她在生死搏斗间发现了人生、事业、青春和只属于自己一次的生命是那么值得留恋,没有苦难,没有波澜,没有较量,生就如同于死。生死之别就在于生比死难。改革是使一切得到证明的机会。赵丽挺直腰板向命运挑战,她立下军令状,以全部家产和4000元资金作为风险抵押,向公司承包了多年帐面亏损达3.5万元的集体经营执照,她要成为一个被社会承认的女老板。尽管前途未卜,已经死过一回的赵丽还怕什么呢?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它不完美,不成熟,甚至会错怪好人,伤害无辜,但如大兵压境,你别无选择,不是主动参与就是被改革,唯有顺应改革潮流,你是牺牲者也是受益者,你是代价也是收获。
干杯!津储人
短短20天,津储公司完成上层机构的改革。没有告状信,没有上访者,有的只是不可能成为可能,成为现实。
吃管理饭的人员减到44人后,腾出两层办公楼出租,这笔费用正好承担改革后44人的管理费。年节约管理费达320万,正是改革前被245人吃掉的那笔财富。
交流干部87人,提职33人。从副局级到科级干部,降职使用9人,免职23人。而且真正实现了动态调整,在记者离开天津那天,又有7名干部被降职,其中包括在这次改革中刚刚提拔起来并有过贡献的人,因为他们已不适应新的形势。津储人心里都记着总经理的一句话:改革不是整人,却是折腾人,就是要在动态中把每个人折腾到自己的黄金点上,而干部能上能下不过是寻找黄金点的一种方式。
效益直线上升。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不仅完成了利润利税计划,还弥补了以前月份的亏损。全年实际利润将比头一年增长15.3%。记者来到唐家口仓库,那位曾经为亏损而痛哭失声一筹莫展的经理喜气洋洋地向记者展示两个月来新添的家产:两部“大哥大”、一部传真机,还有微机、自动速印机,还有“奥迪”、“桑塔那”、“夏利”。
记者问,改革带给你们的最深感触是什么?回答: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帮人,咋今天就显得人杰地灵了!
1991年11月18日,中国物资储运天津综合改革现场会召开。物资部长柳随年激动地说:“天津储运公司108天的改革,解决了国营企业普遍想解决而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为搞活大中型企业探了路。”他说他要给李鹏总理、邹家华副总理写信,汇报这里的经验。
11月21日是会议的尾声,也是会议的高潮。长达16个小时的发言,有49名同志争抢话筒,一吐心声。深夜0:30分,吕晓明高高举起一杯白酒,感谢储运人对改革的理解支持,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唰地举起酒杯。
此时,只有吕晓明知道,这酒中埋藏着一个巨大的悲痛:他那弥留之际的慈母与爱子最后诀别的心愿永远地成为遗憾!
自古忠孝两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