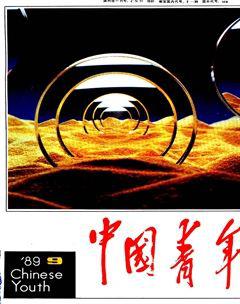一个殡仪工的自述
一提起殡仪工,人们心目中便不由会浮起一个不吉利的字眼:晦气!
我是一个殡仪工。记得有一次我到百货商场去买整容用品,当开发票时,售货员问我是什么单位的,当时我没敢大声说,只小声说了一句:“您就开八宝山殡仪馆整容室吧。”她好像没听见。当我说第二遍的时候,她“啊”地惊叫一声,把笔甩了过来说:“你自己写吧,我不会写。”写完以后,我发现她总斜着眼看我,像躲瘟神似的。我的心一下翻腾开了,那滋味着实让人难受。
然而,人活百岁终有一故。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生命有限,多姿多彩的生活不可能永无止期。生老病死,人总会有蹬脚闭眼、结束人生的时候,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于是,别人也会有求助于我们的时候。
众所周知,我们八宝山殡仪馆是北京最大、举世瞩目的殡仪馆。上至最高层的中央领导,下至所有的平民百姓,死了以后都愿意往我们这儿送。每天送来的尸体少时数十、多时数百,平均每天达七八十人,真可谓门庭若市、从不间断。我所在的整容班,每天接收的整容尸体最少时也有十几个。虽然是见惯不怪,却也有动感情的时候。前年,有一天送来一位被火车轧死的女人,那女人30岁左右,据说是神经错乱自己撞火车致死的。女人已被压成碎片,血肉模糊,四肢残缺不全,尸体是用塑料袋包后送来的。见了面,死者的哥哥扑通一声向我们跪下,声泪俱下地诉说死者是他的亲妹妹,妹妹还留下一小孩,妹妹是他没看管住跑出来的。他恳求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妹妹的碎尸整成完人,让她原原本本地离开人世。眼见此情此景,心头一热,鼻子也酸溜溜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干!我们迅速找来夹板、绑带、针线等等,硬是将碎尸一块块、一片片地缝合、绑扎成一个整体,再将其擦洗、梳理干净,尽量恢复死者生前的原样,死者的哥哥感激不已。还有一次,一个小伙子送来一位死了好些天的老头(老头是他父亲),尸体已经发臭腐烂,蛆虫遍身。可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小伙子扑通地跪倒在我的跟前,苦苦地求我为他父亲换衣服。我明白,他虽是死者的儿子,但也绝不敢为已经死去而且发臭的父亲换衣服的。实际上许多死者的家属都是这样:活着时是亲而又亲的一家人,死了后可就大不一样,活人都怕死人呢!我是殡仪工,开始自然也怕死人,可后来不但不怕,反而觉得人死了有什么可怕?我接触的多数死人大都神情平静,面容安详。他们睡得正酣呢,只不过是长睡而已,有啥可怕的呢?要说可怕,是活人可怕,活人中有狡诈的、阴险的、心狠手辣的、口蜜腹剑的,他们随时想着损人利己、想着谋财害命……死人就不会这样。我是给死人整容的,眼下这小伙子声泪俱下地求我,我哪能无动于衷?人活着时多灾多难,死了后穿件像样点儿的衣服告别人世,完全应该!我二话没说,将小伙子在地上扶起来,接着动手工作:将老头的脏衣服脱下,用手一把一把地把尸体上的蛆虫抓扫干净,给他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给他洗脸、刮胡子、描唇、上油彩等等。这一切,都是与同事一块儿干的。那小伙子,别提对我们有多感激了!
当殡仪工,当然绝对算不上什么好工作。三百六十行,若是让大伙儿自由选择工作,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会来、不敢来。说句实话,要是时间能够倒流、一切从头来,让我从众多的工作中选一份工作,我也不一定选择当殡仪工。可眼下真要有机会让我换个工作,我还真不愿意哩!为啥?也不为啥。顺便说一下,有人见到殡仪工,都觉得很惊奇,很新鲜,进而便问你每月挣多少钱,似乎我们都是为钱而来似的。哼,钱再多,你恐怕也不会来吧?老实说,我们对这种提问,最反感!实际上,就我自己而言,我目前的基本工资只有58元,就算把别的补贴加上,每月也只不过两三百元,可眼下社会上许多行业,随便拉出一个,他们的收入也不比我们低吧?所以,我现在愿意当殡仪工,乐意干这工作,绝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是觉得社会需要,像社会各行各业一样,缺一不可。试想:如果没有殡仪工,不说全国,就是北京,每天那么多尸体往哪儿堆?存家里、放街上?哼,那北京非成地狱不可!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就跟社会上别的工作一样,很平常。虽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但也绝不卑微!要真不服气,你以后就别找咱!(笑)
我当殡仪工,似乎也有点遗传,这一点与我的许多同事有些区别。我爷爷过去专事抬棺,我父亲退休前也在八宝山专事接尸,连我算进去,真是地地道道祖宗三代都干这行当。我1978年高中毕业,两年后参加招工时,本来有一个哥们儿要同我一块儿投考八宝山的(那哥们儿同我住在一个大杂院,他父亲也当过殡仪工),可后来找门儿去了拖拉机公司。我则是铁了心要来的。当然,开始母亲也不同意,说当父亲的已干了一辈子,当儿子的还不换个工作?可父亲说:“殡仪工有什么不好?”就这么一招,把母亲给顶回去了。母亲是老实人,地道的家庭妇女,自然最终还是听父亲的。于是,我一切顺利,最终如愿以偿。
来八宝山后,一开始我被安排去接尸,接着在火化车间干了半年,后来便被安排到整容班,工作可以说一次比一次恶劣、辛苦。
我们整容班实际上只有3个人:吴连增、谢志刚和我,平均年龄30来岁。我们平均每天要整出十几具尸体,他们中也是上至中央领导、国家干部,下至普通老百姓,还有的是海外华侨及外国友人。一般来说,人死了,亲属都愿意为其亲人整出一个安详的面容来,我们就是本着这一要求尽量去满足他们,但这样做工作难度很大。比如说,有的死人生前肥胖,因疾病折磨,死后非常消瘦,而且有的瞪着眼睛,有的则咧着嘴。我们便想办法往死者嘴里填上棉花,让眼睛尽量闭着,然后洗洗脸刮刮胡子;女同志则梳理好头发,化妆上油彩,这样一来基本上就跟生前一样。像这些正常死亡的还好处理一点,要是非正常死亡的如车祸、工伤、烧伤、跳河自杀以及腐烂尸体、传染病致死等等,那可就腻味了!
大伙还记得1986年夏季发生在山西五台山那起惨重的车祸吧?当场就死了31人!其中除两名死者在当地处理外,剩余的29具尸体全部拉到八宝山停尸间。我们一上班,看见整容间里的血水流满地面。天气很热,腐烂的尸体散发着一股股呛人的气味,咸臭咸臭的,一闻直想吐。再瞧那些尸体,满目疮痍!有的胳膊腿已不在原来的位置上,有的头部已经裂开,脑浆奇臭无比。大厅里,家属悲痛的哭叫声和喊声汇成一片。我们在上级领导的指挥下,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了一个临时整容小组。没有一个讲价钱,也没有一个人提要求,穿上工作服大伙就动手干。尸体中有脑袋裂开压扁的,我们就把它冲洗干净然后塞上棉花,再缝合面部伤口;还有胳膊腿断了的,我们就找来夹板用绷带扎好,然后再穿好衣服进行整容化妆,整完一个就让家属与其告别。一连两天,我们加班加点,精神高度紧张,累得都快顶不住了!可大伙儿硬是一丝不苟,坚持认真地把尸体处理完毕。
殡葬是一种工作,更是一项事业。既是事业,就得全身心去干;既是事业,也就要有创新。
由于社会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死者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比如非正常死亡,弄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过去的老做法就是给死者带个墨镜和口罩,把一切都捂住了。但这是另一种面孔,跟整容相去甚远,死者家属感情上也不自然,总会留下遗憾。眼下却是摸索着把死者的伤口一点点地缝起来,而且尽量不让露出线纹,尽量使嘴眼鼻子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为了使死者家属感情上好受些,我自己至今还坚持不戴手套,再脏再臭甚至满身蛆虫的尸体我也是不戴手套地为其整容,整完了我再洗手消毒。于是,家属十分感激。我也并未满足,技术上想精益求精。去年我被派到上海参加为期半年的全国殡仪工学习班,具体学习防腐、化妆等技术。此外,我还准备参加北京的美容班,想从活人美容技术中学些有益的东西,将其应用到死人的化妆上。
也是1986年的事儿:房山县长阳乡有个20多岁的姑娘过几天就要结婚了,可不幸的是她去买东西的路上,突然被拖拉机轧死了。尸体交房山县火化场整容后,家属死活不满意,非要把女儿整出原样来不可。没办法,房山火化场只好打电话向我们求援。当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快要下班,天气又冷。可我们二话不说,立即整理好工具开车直奔房山火化场。家属马上拿出姑娘生前的照片,哀求我们照着照片整。我瞅了一眼照片,对家属说:放心,我们尽力而为。经过一番细致而紧张的擦洗、缝合、修整,一张年轻的面容露出来了。家属看后非常满意。肇事单位也很感动,事后拿出200元钱表示感谢,并说100元算你们的收入,另100元你们就吃顿饭买盒烟抽吧。我们连忙说:“这是我们的份内事。公事公办,我们收100元,算是单位的收入,另100元请你们收回。我们要真为这点钱,还没准不来了!”回到单位,已是晚上9点钟……
由于自己努力工作,1987年以来,我先后获得过“民政部劳动模范”和全国首届共青团“五四奖章”称号,眼下还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委员呢!但说心里话,我个人并不看重外界的评价。我在想: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绝不应该靠这些冠冕堂皇的称号支撑生活,而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和对工作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