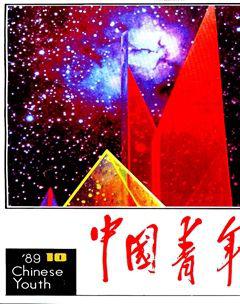谨守初衷
20多年前,上山下乡的大潮席卷了整个锡林郭勒大草原。
如今,大潮已经退去。当年来自北京的四五千名知识青年,今天仍然在这块土地上的,只剩下300人了。陈朋山便是这300人中的一员。
8月是草原上的黄金季节,一个晴空丽日的下午,我找到了她……
“我个人的经历平淡无奇。”这是她接受我采访的第一句话。
“我与共和国同一年出生。父母是外交部的干部。小时候和姥姥住在广州,生活优越,即便三年困难时期也没吃苦。1962年到北京,后考入女四中。在学校里我是学习尖子,初三时入了团。‘文革开始时,也有心参与,但因被别人看成是修正主义黑苗子,只得靠边站了。1968年,和当时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怀着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决心来到了内蒙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阿拉腾郭勒公社巴拉格大队。
“放牧、挤奶、洗羊、打草、挖井、剪羊毛……一干就是8年。夏天,顶着高原的烈日,熬着寂寞一个人放牧十几个小时;冬天,要经受一次次暴风雪的袭击,在零下30度的气温下护理牲畜。我学会了骑马和蒙语,学会了蒙古民歌和一个真正牧民的生活能力。同时,也同这块土地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蒙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76年,我被任命为副旗长(当时还叫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上调到盟委组织部任部长,今年又当选为盟委副书记。
“同大多数知识青年相比,我是个幸运者。坦率地说,我并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除了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我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主要是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支持。每当我做出一点点成绩,人民就给予我很高的荣誉。记得曾经有一位朋友问过我:你在锡盟20年,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如果这20年在北京工作,你的个人价值是否能得到更充分的实现?当时我没有回答,但后来我认真思考了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说这20年中我有所失的话,失去的只是优裕的物质生活和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理想。相反,我所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多。除去党和人民给我名誉、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培养意志品格、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对人民满腔热爱的思想感情。同时,我还在生活实践中学会了用一种辩证的、实际的方法看待我们的社会,指导我的工作。社会是复杂的,中国的现状是不可能通过几句话、十几句话或几本书、十几本书就了解的。而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是群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疾苦和自己的是非善恶标准。只有了解人民心里想什么,才能做好工作,才谈得上为国家作贡献。我觉得,在锡盟20年,这些是我最大的收获。
“‘实现个人价值,对我来说,这是近几年接受的新名词。我上学时没有这种说法,那时只讲奉献。现在对‘实现个人价值可能还有不同解释,但就我的理解,它的含义应该是,适应环境,努力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我不到20岁来到锡林郭勒草原,一晃就是20多个春秋,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我也不可能重新选择这20年的生活。至于假如我在北京生活20年,情形又能怎样,我从未想过,因为这种设定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我现在能说的是,我的乐土在锡林郭勒草原,我的价值也只能在这里实现。由此,我想到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民,他们不是也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吗?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子女中有许多人受教育的程度还达不到城市的水平,能够为改变这种状况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也就是说能为更多的人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工作,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每个人一生中都要面临几次重大选择,20年前,陈朋山选择了到边疆干一辈子,一条路走到底,尽管那时的选择带有几分浪漫与狂热;然而,20年后的今天,她仍然牢牢地抱守着20年前的初衷。
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