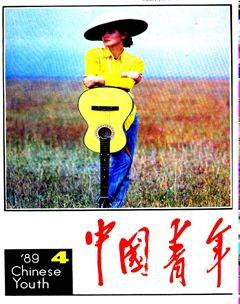立足于事实的大地上(我的经历)
杨百揆,男,湖北沔阳人,1950年10月出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行政学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著有《美国总统及其选举》《西方文官系统》《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等。
我一生的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神幻时期
从小,我性格内向,好沉思,不善言谈,爱读书,爱玩。父亲对我们很严。言谈举止都要有“规矩”。父母每天检查我们的作业,看成绩册,还要求我们把每篇课文都背下来。当时家里的书很多,从线装古籍到量子力学,从王右军的草诀歌到连环画。父亲还不时地给我们买一些科普读物。儿童文学和童话故事则主要从姐姐、哥哥那里借来看。我什么书都爱看,还容易迸入角色,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
二、形而上学时期
上中学以后,大约是1963或1964年,校园中政治气氛开始浓起来。先是学雷锋,做好事,后来是阶级教育忆苦思甜,下乡下厂劳动。我读书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大约是1964年,读完了《矛盾论》《实践论》,并在书内空白处做了笔记。后来又读了许多马恩列斯著作,以及中外各种思想流派的政治、经济、历史、外交、军事、文学著作几百种,并做了数十万字的笔记,还读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和自然科学书籍。读书增长了我的知识,开阔了我的思路。但只有文革、插队、当工人和这时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才使我真正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回想起来,书只起到了参考、借鉴和印证作用。当时我看一些书并不理解,后来发现,是生活使我理解了一些书的内容,否定了另一些书的内容。
大约在1971年前后,我曾一度认为自己一切“弄诵”了,也号称“壮志坚信”,并用理论套生活,不自觉地削足适履。但强有力的生活之足不断地顶破僵硬的理论之履,使我思想逐步发生了转变。
三、实证时期
我思想的转折大约是从插队后期开始的。1977年转变基本完成。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大概是深深体验了当时中国的落后和社会中种种惊人的不合理现象。对此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广泛、深入的思考,从现实生活中理解和评判各种理论和社会基本价值。大概由于知识结构、思想方法不同和某些特殊经历,我逐步形成了一套看来与很多人不大一样的思想。在以后的日子里,生活和世界发生的事情不断验证、强化和丰富了这些思想。这些年我主要考虑如何使之社会化,并不断完善和充实的问题。我想用这样的话概括我的生活经验:
牛顿说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认为这挺危险,还是立足事实的大地上最牢靠。